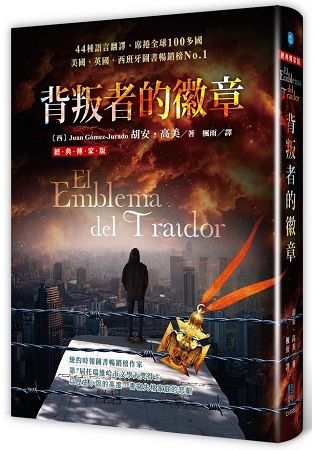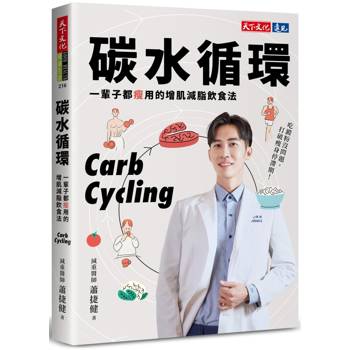紐約時報圖書暢銷榜作家
第七屆托瑞維哈市文學大獎得主
以歷史小說的高度,書寫失格家庭的悲劇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慕尼黑。保羅‧雷納目睹大表哥愛德華因在戰爭中負傷嚴重,被抬回家中等候死亡宣判。從愛德華的口中,十五歲的保羅,毫無防備被推向殘缺而殘忍的成人世界:他意識到德國的戰敗如何扭曲人性,並得知,始終缺席的父親,原來死於一場親戚間的謀殺……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背叛者的徽章(經典傳家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3 |
歐洲現代文學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2 |
西葡語文學 |
$ 282 |
西葡語文學 |
$ 288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背叛者的徽章(經典傳家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胡安‧高美(Juan Gomez-Jurado)
1977年12月生於西班牙馬德里,聖巴勃羅大學新聞學博士,西班牙知名記者,足跡遍及全球,對神秘現象、宗教學有精深的探索和研究,其小說《背叛者的徽章》一經發表就引發巨大轟動,被翻譯成44種文字,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後續作品《與上帝的契約》《上帝的間諜》更榮登歐美各國各大圖書排行榜榜首,胡安本人也因此被譽為西班牙在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暢銷小說作家,以及繼史蒂芬金、丹‧布朗後又一位世界級驚險探秘小說大師。
作者獲獎紀錄
★ 美國《紐約時報》圖書暢銷榜榜首
★ 英國圖書暢銷榜榜首
★ 西班牙圖書暢銷榜榜首
★ 法國《世界報》圖書評論榜榜首
★ 獲「世界拉丁語圖書大獎」
★ 獲美國「最暢銷文化小說」、「最佳冒險小說」金獎
★ 創下西班牙小說於美國出版之最高版稅金額
★ 作品《上帝的契約》已由好萊塢買下電影改編版權
胡安‧高美(Juan Gomez-Jurado)
1977年12月生於西班牙馬德里,聖巴勃羅大學新聞學博士,西班牙知名記者,足跡遍及全球,對神秘現象、宗教學有精深的探索和研究,其小說《背叛者的徽章》一經發表就引發巨大轟動,被翻譯成44種文字,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後續作品《與上帝的契約》《上帝的間諜》更榮登歐美各國各大圖書排行榜榜首,胡安本人也因此被譽為西班牙在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暢銷小說作家,以及繼史蒂芬金、丹‧布朗後又一位世界級驚險探秘小說大師。
作者獲獎紀錄
★ 美國《紐約時報》圖書暢銷榜榜首
★ 英國圖書暢銷榜榜首
★ 西班牙圖書暢銷榜榜首
★ 法國《世界報》圖書評論榜榜首
★ 獲「世界拉丁語圖書大獎」
★ 獲美國「最暢銷文化小說」、「最佳冒險小說」金獎
★ 創下西班牙小說於美國出版之最高版稅金額
★ 作品《上帝的契約》已由好萊塢買下電影改編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