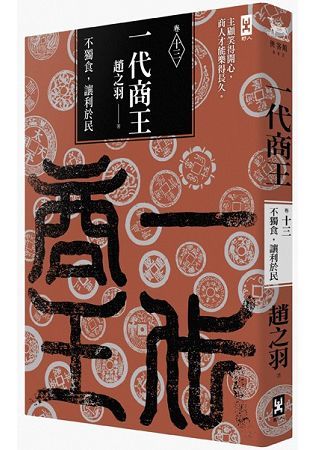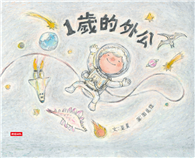商戰╳謀略╳歷史╳愛情
一代商王‧古平原
主顧笑得開心,商人才能樂得長久。
★ 作者趙之羽的先祖為清朝開國大將、滿文創始人,
多年潛心清史研究,堪稱最懂清朝政商關係的小說家。
★ 火熱銷售50萬冊,中國政商小說里程碑之作,
同名改編電視劇正熱烈籌拍中!
古平原vs.李欽——親兄弟的恩怨,就在商場上解決
「生父」之謎真相大白後,無論在古家或李家,都引起軒然大波,
兩淮鹽場成了兄弟間較勁的最佳場所,比實力也比財力,
想從中謀取利益的王天貴和蘇紫軒,各懷鬼胎幫助這對異母兄弟,
而一心想爬更高的喬鶴年,發現官場利益更勝朋友情誼……
面對變了調的兄弟情、朋友義,還有從中萌生的愛慕、眷戀,
這些古平原的「老相識」們,該如何處理彼此的「感情」事?
誰的錢最多,誰就能掌控大局
害怕丈夫會回到古家、兒子比不上異母兄的李太太,
擅自作主將一半鹽場退回官府,逼古平原買回去,
希望就此打垮古家,把他們踩在腳下。
古平原能籌到足夠的錢吃下這些鹽場,反敗為勝嗎?
高價進鹽低價賣,究竟垮台的是誰?
買下一半鹽場的古平原,發現無鹽可賣,
李家於是趁機拉抬鹽價,讓他不得不以高價進鹽貨,
但李家又用計規定了極低的售價,準備打趴古平原。
古李二人的爭鬥,究竟最後垮台的是誰?
兩個勢同水火、想置對方死地的古平原和李欽,得知彼此是異母兄弟後,憤慨不減反增;
而始終擔心丈夫會回到古家的李太太,決定插手干預商場事,徹底擊垮古家。
當兩家明爭暗鬥如火如荼,王天貴、喬鶴年、蘇紫軒……
究竟各有什麼盤算,又會如何橫插一手,將局勢攪得更混亂?
販私得利只是一時之利,洞燭機先方有一世之利。
我希望將天下鹽場的巨利,分而勻之,讓百姓吃鹽不必再錙銖必較。
主顧笑得開心,商人才能樂得長久。──古平原
讀者書評
★歷時五年磅礴著作,天涯、搜狐、榕樹下火爆連載,千萬讀者跳坑熱捧!
★豆瓣讀書網友五顆星狂推:根本停不下來,太好看了!
‧財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中國版的《商道》。──于師傅
‧話說從商要讀胡雪巖,也可讀讀古平原。──越讀悅讀
‧從關外到山西,還原一代晉商的精氣神!──好吃
‧這書真是好看,從故事的精彩角度說,一點不比盜墓差。──林間的猴子
‧劇情緊湊,情節跌宕起伏,最近看的書裡的難得佳作。可惜每卷又剛好停在關鍵˙時刻,為啥不幾部一起出啊。──maranatha
‧文筆很見功力,故事也精彩,好小說!──yehuo
‧太太太精彩了,都不想睡覺了,太好看了! ! ! ! !──我是小書蟲
‧徹夜讀完。──澤板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