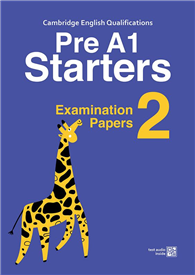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茶花女的圖書 |
 |
茶花女:文學史上三大青春悲戀小說,小仲馬成名代表作【獨家收錄《茶花女》文學沙龍特輯│法文直譯精裝版】 作者:亞歷山大.小仲馬 / 譯者:譯者李玉民 出版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6-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與《羅密歐與茱麗葉》、《少年維特的煩惱》並列文學史上三大青春悲戀
世界文豪小仲馬畢生的自白懺悔
令小仲馬獲得父親大仲馬認同的代表名著
名家法文直譯,絕美風華再現
獨家收錄《茶花女》文學沙龍特輯
她是19世紀巴黎交際圈中芬芳罪惡的山茶,也是小仲馬畢生成就祭壇上的聖女……
一個月裡的二十五天,她佩戴著白茶花,其餘的五天,則戴著紅茶花。她的身上總是帶有迷人的花香,人們都喚她為「茶花女」;全巴黎的人們都知道她的芳名,只因她是個出入上流社會的交際花。
家境貧苦的瑪格麗特,不得已從鄉間到都市謀生,憑藉著她的天生麗質,搖身一變成為巴黎貴族爭相討好的交際花。可是在那浮靡的亮麗背後,蘊藏了一個女孩渴求心靈伴侶的簡單願望。但當她邂逅了富家公子阿爾芒之後,一切有了轉變的契機。為了正式揮別過去的自己,瑪格麗特陷入了經濟困境,奮力抵抗著外界的流言蜚語,只為守護兩人的愛情。然而阿爾芒父親的意外來訪,迫使她面臨到現實的殘酷無情。為了阿爾芒的前途、為了另一位純潔女孩的幸福,她決心作出此生最偉大的舉動……。
《茶花女》是小仲馬僅23歲便寫就的作品,一出版即獲得當時文壇的熱烈迴響。他以哀婉動人的故事情節、緊湊明快的敘事張力,緬懷自己年少時逝去的愛情。書中以寫實主義的筆法,描繪出十九世紀法國上流社會的絢麗,卻也飽含浪漫主義的細膩關懷,具有文學思潮轉向的重要代表性。西元1875年,小仲馬高票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登上法國文壇的頂點,《茶花女》亦成為世界永垂不朽的傳奇之作。
★茶花女文學沙龍特輯:
.小仲馬文學祭壇上的聖女──瑪麗.杜普萊希
.法國文壇最耀眼的雙子星──大小仲馬父子
.流芳至今的茶花女現象
.巴黎茶花女在新文化中國
根據法國伽利瑪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本翻譯而成
一窺19世紀巴黎交際花的美麗與哀愁
本書特色
1.強烈的自傳色彩:小仲馬將愛情回憶獻上文學祭壇,以歷歷在目的寫作筆法,譜寫出舊日時光的甜美與哀痛。
2.感人的情感書寫:鋪陳男女關係裡的迂迴錯落,劇情環環相扣,最終醞釀為真心成全的愛情真諦。
3.堅定的文學地位:既有浪漫主義的感性關懷,亦有寫實主義的具體呈現,擁有文學思潮轉向的重要代表性。
4.不朽的傳世影響:與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並列為三大愛情悲劇,多次改編為電影、歌劇,亦為電影《紅磨坊》靈感來源。
作者簡介 |
小仲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
原名「亞歷山大.仲馬」,法國小說家、劇作家。小仲馬為《基督山恩仇記》、《三劍客》作者大仲馬的私生子。大仲馬拋妻棄子,直到小仲馬七歲才肯承認他的身分,使得小仲馬自幼飽受歧視與譏笑。儘管如此,小仲馬仍然繼承了父親的寫作天賦。
一八四二年,十七歲小仲馬離開了寄宿學校,在巴黎開始接觸上層浮華生活,結識到巴黎當時著名的交際花瑪麗‧迪普萊西。之後,兩人墜入情網,然而瑪麗無法脫離奢華享樂的上流社會,小仲馬因而與她斷絕往來。一八四七年,瑪麗因病過世,在悲痛萬分之下,小仲馬將他的情感回憶寫成小說《茶花女》,一出版便馬上轟動一時。
西元一八五二年,「茶花女」被改編為戲劇在歌劇院初演。小仲馬透過電報告知父親:「第一天上演盛況空前,人們都誤以為是您的作品登台了!」大仲馬則回電:「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茶花女》哀婉動人的故事情節,緊湊明快的敘事張力,使得這部著作成為眾人愛戴的不朽名著。
西元一八七五年,小仲馬以高票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代表,享有當時文壇最高榮譽。他的作品多推崇家庭與婚姻價值,被視為近代由「浪漫主義」轉到「寫實主義」的重要作家。具有生活感的社會背景,亦不失藝術價值。他著名的作品包括《茶花女》、《半上流社會》、《金錢問題》等。
譯者簡介 |
李玉民
一九六三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文學系,曾至法國里昂大學留學兩年,之後擔任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從事文學翻譯將近三十年,譯著超過六十本,總字數超過兩千萬,曾獲得「思源翻譯獎」、「傅雷翻譯出版獎」。在其翻譯的著作中,有半數作品是他首度引薦給華人讀者。主要譯作有雨果的《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大仲馬的《三劍客》、《基督山伯爵》,小仲馬的《茶花女》以及巴爾扎克的《幽谷百合》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