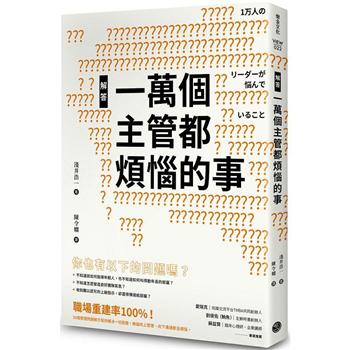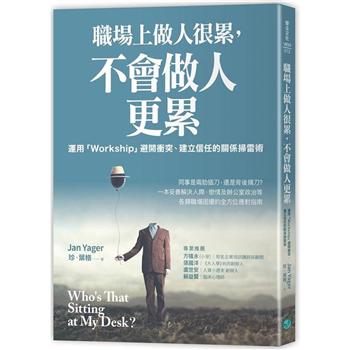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試閱內容1】
快走到店鋪末端的帳房時,他故意加重腳步聲,好讓別人聽見。
帳房的門簾掀開,阿爾努太太就在眼前。
「啊,是您!您在這裡!」
「對。」她回答說,因為情緒激動因而顯得結結巴巴:「我在找……」
他看到她的手帕放在書桌附近,猜想她來店裡是要了解店鋪的帳目,消除她的焦慮。
「您或許是要來買東西的吧?」她問。
「只是微不足道的東西,夫人。」
「這些店員老是不見人影,真不像話!」
他不打算責怪他們。相反地,他慶幸現在這樣的情況。
她用諷刺的目光盯著他:「唔,婚事辦得怎麼樣啦?」
「什麼婚事?」
「您的婚事!」
「我?我此生絕不會結婚!」
她做了一個表情,像是表示不相信這種鬼話。
「您說這種事怎麼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難道您以為,在美好的夢想絕望以後,我會自甘苟活於平庸之中嗎?」
「但您對您的夢想並不是那麼的……認真!」
「妳這話什麼意思?」
「您那天不是帶了一個女人去看賽馬!」
腓德烈克在心裡詛咒羅莎妮,繼而回憶起什麼來。
「不是您自己要求我不時去找她,以了解阿爾努的情況嗎?」
她搖搖頭回答說:「所以您就及時行樂了?」
「老天!讓我們忘掉這些愚蠢的想法吧!」
「您馬上便要結婚了,當然應該忘掉。」她咬著嘴唇,憋住一聲嘆息。
腓德烈克放聲大喊:「我說過了,我沒有要結婚!難道您相信,憑我對知性的需要,以我的生活習慣,我會甘心窩在外省,靠打打牌、管理水泥匠,穿著木屐散步度日嗎?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有人跟您說過,那女孩家裡很有錢,對不對?但我那會在乎那些錢!我長久以來嚮往的,是人間最美、最溫柔、最富有魅力的事物,一個體現於人形的天堂。後來,當我終於找到了這個理想事物,眼裡便再也容納不下其他的一切……」
他雙手捧住她的臉,開始吻她的眼瞼,反覆說道:「我永遠不會結婚!永遠不會!永遠不會!」
她順服地接受他的親吻,心中又驚又喜,完全失去動彈的力量。
樓梯上方突然傳來開門聲。她嚇了一跳,但站著不動,雙手舉在胸前,示意腓德烈克不要作聲。下樓梯的腳步聲愈來愈近,然後有人在門後面問道:「夫人在嗎?」
「進來!」
會計掀起門簾時,阿爾努夫人一條手臂擱在櫃臺上,神情平靜地五根手指轉動著一枝筆。
腓德烈克站立起來,裝成本來正要準備離去的姿態。「夫人,我告辭了。我要的東西不久就會備妥,對不對?」
她沒有回答,但這種無言等於是給了腓德烈克肯定的回答。她的臉燒得通紅。
第二天他又上她家去。為了打鐵趁熱,他一開口便為賽馬場的事提出辯解。他說,上次他會跟那個女人在一起純屬偶然。即便承認她漂亮(其實不算漂亮),但既然他愛的是另一個女人,她又怎麼可能占據他的心思,哪怕一分鐘也不可能?
「您很清楚我的心意如何……我已經表白過了!」
阿爾努太太低著頭。
「我很遺憾您說過那樣的話。」
「為什麼?」
「因為即便依照最平常的禮節來看,我也不應該再見您了!」
他表示抗議,指出自己的愛屬於最純潔無邪的那一種。他過去的舉止足以證明他的未來。他一定會謹守分寸,決不會打擾她的生活,不會唉聲嘆氣地麻煩她。
「我昨天只是情感滿溢了才會那樣。」
「我們不應該再去回想那個時刻,我的朋友!」
然而,兩個人既然同病相憐,又為什麼不可以相濡以沫呢?
「我了解您,知道您並沒有比我更快樂!您渴求感情、忠誠,卻得不到回應。您想要我怎樣我都會聽從。我絕不會冒犯您!我可以發誓!」沉重的心情讓他支持不住,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
「起來。」她說,「我要您快起來!」
她用命令的口氣要他起來,說是如果他不依從,將永遠不再見他。
「啊,我不信妳會那麼狠心!」腓德烈克回說,「我在這個世界又有何所求?其他男人求的是財富、名譽和權力!但這些東西都不是我要的,您是我唯一的執著、全部的財富和生命的中心。沒有了您,我如同沒有了空氣,絕對存活不下去!難道妳感覺不到我的靈魂正在飄向您,感覺不到這兩個靈魂若是不能融合為一,我就會枯竭而死?」
阿爾努太太全身顫抖了起來。
「您走吧,求求您了!」
她臉上絕對的表情讓他停止。然後他上前一步。但她卻退後一步。
「看在老天的份上,求求您離開吧!」
腓德烈克因為是那麼地愛她,不想讓她為難,便離開了。
他對自己非常生氣,罵自己是白癡。不過,二十四小時之後,他又重新登門拜訪。
僕人告訴他太太不在家。他佇立在樓梯間,既憤怒又怨恨,恍恍惚惚地不知所措。但阿爾努卻在此時走出來,告訴他妻子當天早晨已動身前往奧特伊。他們已經把聖克盧的鄉間別墅賣掉,改在奧特伊租了一間小別墅,她會住在那裡一陣子。
「這又是她的突發奇想。既然她覺得這樣稱心,就隨她去吧,我也落得清靜。今晚就一起用餐吧,如何?」
腓德烈克藉故有急事要辦,推辭了邀請,接著即刻趕赴奧特伊。
看到他,阿爾努太太忍不住發出一聲歡樂的驚呼,腓德烈克的全部怨氣為之煙消雲散。
他沒有再傾吐愛意。為了取得她的信任,他甚至表現得過分拘謹。臨走前他問她,能否可以再來?得到這樣的回答:「當然,還用說!」說著,她向他伸出一隻手,但隨即把手縮回來。
自此以後,腓德烈克的拜訪日趨頻繁。為了讓馬車伕快馬加鞭,他答應給額外的小費。但他常常還是受不了馬兒慢吞吞的步伐,乾脆下車,追趕一輛公共馬車,氣喘吁吁地攀上去。打量其他乘客的臉孔時,他心裡會有一種瞧不起的感覺:他們都不是去看她的!
遠遠的他就可以辨認出她的房子。那是一棟瑞士木屋樣式的小別墅,漆成紅色,正面有一個陽臺。花園裡有三棵老栗樹,中央有一個小土丘,插著一根樹幹,樹幹頂有一個用茅草搭建而成的傘蓋。圍牆的披簷上垂掛著一棵葡萄樹的藤蔓,它們歪七扭八的就像是腐爛的纜繩。柵欄門上的拉鈴拉起來很費勁,鈴聲很遲鈍,而且總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有人應門。每當這種時候,他都會因為懸著一顆心而擔驚受怕。
隨後,他會聽見女僕趿著拖鞋快步走過礫石的聲音,有時則是阿爾努太太親自出來。有一天,他到的時候,看見她正彎腰在草坪裡採摘紫羅蘭。
阿爾努太太因為女兒脾氣太壞,不得不把她送到女修道院寄宿。她的兒子每天下午都在學校。阿爾努現在養成習慣,每天都會跟列冉巴,還有他們的朋友貢班一起在王宮廣場吃午餐,一吃就是大半天。所以,腓德烈克和阿爾努太太完全不用擔心有誰會來打擾兩人的獨處時光。
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應該屬於彼此。基於這種默契,使他們不至於招來災禍,也使得彼此更容易傾訴衷情。
她告訴他從前她住在沙爾特時的生活:她直到十二歲還是個虔誠教徒,後來迷上音樂,常常在小房間裡一直唱歌唱到夜幕低垂。從她房間的窗口,可以眺望到城牆。
他則向她傾吐自己念中學時是如何多愁善感,又常會在想像裡看見一張女人的臉從雲霧後面向他發出光芒。正因為這樣,當他後來初次見到她的時候,只覺得非常眼熟。
這些談話遵守著一條規則,那就是只涉及他們彼此認識以來的時光。他常會回憶起關於她的瑣事,比方說某個時期她衣服的顏色、他們倆在某一天遇見過的某個女人,或是她在某個場合說過些什麼話。聽到這些,她都會很驚訝地回答:「對,我記起來了!」
他們有著相同的品味、相同的見解。所以,聽到對方說話時,他們常常會喊說:「我也是這樣。」
然後他們沒完沒了地埋怨上天:
「為什麼老天爺不成人之美,讓我們早點遇見……」
「唉,要是我年輕點就好了。」她感嘆說。
「不,要是我年長些就好。」
他們想像著一種只有愛情的生活,這愛情無比豐盛,可以填滿無邊的孤獨,凌駕於一切的喜悅歡樂之上,睥睨著所有的不幸與痛苦。在這樣的生活裡,戀人無視時光荏苒流逝,只顧不斷地互訴衷情,最終孵育出一種璀璨而光榮的物事,有如天上閃耀的繁星。
兩人常常在陽臺露天樓梯上佇足遠望,凝視連綿到灰白天際的參差樹林,樹梢已隨著秋天的到來逐漸轉黃。要不然就散步到道路盡頭的一間夏天度假屋。屋內唯一的傢俱是一張灰色的帆布躺椅。玻璃窗上沾著許多污漬,牆壁散發一股霉味。他們快快樂樂地坐著聊天,想到什麼便聊什麼。有時,陽光會穿過威尼斯式百葉窗,像一根根琴弦似的從天花板一直延伸至花地磚。塵埃在這些光柱中形成漩渦。出於玩心,她用手把光線遮斷。腓德烈克輕輕抓住這隻手,端詳它的脈管、肌理和手指的形狀。在他的眼中,她的每根手指都不只是手指,而是各自擁有自己的生命。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情感教育(二版)[福婁拜夢幻逸作,超越《包法利夫人》,繁體中文版首度面世]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情感教育(二版)[福婁拜夢幻逸作,超越《包法利夫人》,繁體中文版首度面世]](https://media.taaze.tw/showProdImage.html?sc=11100912105) |
情感教育(二版)[福婁拜夢幻逸作,超越《包法利夫人》,繁體中文版首度面世] 作者:古斯塔夫.福婁拜 /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7-1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情感教育(二版)[福婁拜夢幻逸作,超越《包法利夫人》,繁體中文版首度面世]
超越《包法利夫人》,揭露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的浮華與幻滅
一部令卡夫卡、莫泊桑、普魯斯特、納博可夫,為之著迷的極致名著
最具福婁拜自傳色彩的經典作品
阮若缺 (政治大學歐語系教授)——精采專文導讀
▍洶湧的愛情、澎湃的理想、無畏的革命
這世上的每個人,都期盼以不同的方式成就自我,完成生命的驚嘆!▍
我想要書寫我們這一代人的道德歷史,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書寫他們情感的歷史。這是一本關於愛情、關於激情的書。但僅能容於當世的激情,亦即消極的激情。
──古斯塔夫.福婁拜 自述《情感教育》創作動機
▍那是我們人生的最好時光!▍
寫實主義巨匠福婁拜,以瑰麗細密的文字、客觀冷靜的口吻,編織出一幅十九世紀法國社會浮世繪。從柏拉圖式的單純愛戀、再到情欲糾葛的遊戲,最後淪落到為了現實利益妥協,腓德烈克用他人生理想的幻滅,完成了屬於自我的情感教育。藉由成熟的敘事技巧,福婁拜道出了世代青年從滿腔抱負,到最終一事無成的集體生命困境,緬懷那些似水流逝的徒然激情。直至今日,猶有許多的「腓德烈克」,在混亂奔騰的社會局勢裡,惶惶不可終日。
腓德烈克,一名出身富有家庭的法學院學生,初到巴黎這座自由開放的大都市。在某日返家輪船上,他邂逅了畫商阿爾努的妻子-瑪麗,並且深深為她著迷。然而,她卻始終不敢接受他的情意。置身在風起雲湧的十九世紀,這名青年出入於極致奢華的社交晚宴、迷人感性的高貴沙龍,也見證了法國王朝的一夕傾倒、街頭喋血的暴動場面。革命號角響起,權勢地位轉移。歷經數波動盪,生性浪漫的腓德烈克,除了耽溺在長年的單戀之中,亦先後周旋於家鄉純情少女的愛慕、交際花羅莎妮的胴體、實業家丹布羅斯夫人的財富,久久無法自拔。他的摯友德洛里耶,則是不擇手段地想在混亂的時局裡,尋找一夕翻身的機遇。然而無盡的激情追逐之後,等侍他們的將是……
本書特色
★一部最富有福婁拜個人自傳色彩的小說
★全新中文譯本首度在台上市,滿足經典文學讀者的收藏渴望
★法國文壇巨匠福婁拜,超越名著《包法利夫人》,顛峰代表作!
★描繪法國十九世紀當時社會,反映法國動盪不安的革命時代。出入巴黎上流社會饗宴,目擊群眾攻占王宮時的亢奮瘋狂。
★刻畫人物性格、形貌傳神細膩,用字優美洗練
★影響莫泊桑、左拉、普魯斯特、喬伊斯等卓越名家,小說審美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的重大轉折
名人推薦
▍卡夫卡、納博科夫、莫泊桑、普魯斯特、喬治.桑、努里西埃、阮若缺、房慧真……諸多名家一致傾心推薦 ▍
★卡夫卡 (《審判》、《蛻變》作者)
在寫給女友菲莉斯的情書裡,提到「《情感教育》多年來如同極少的幾個朋友陪伴著我。無論何時,無論何處,翻開這本書,都會令我感到激動不已,完全被它所吸引。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本書作者的精神之子,儘管是愚笨又可憐的那一個。馬上寫信告訴我,妳是否會法文。如果會,我再為妳寄去最新的法文版本。告訴我,妳會法文,即便這或許不是真的。因為本書文字非常之瑰麗。」
★納博科夫 (《蘿莉塔》作者、二十世紀當代小說之王)
我最喜愛的法國文學家是福婁拜與普斯特。……沒有福婁拜就沒有法國的馬塞爾.普魯斯特,也不會有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俄國的契訶夫也就無法成為真正的契訶夫。
★弗朗索瓦.努里西埃 (當代法國作家、龔固爾學院院士)
我無法於《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兩者之間作抉擇。倘若非抉擇不可,那我無疑會選擇《情感教育》。
★房慧真 (《小塵埃》作者)
「他們的青春似錦,生活如畫」,《情感教育》的一開場,從兩個外省出生,一同求學,夢想著即將有著遠大前程的青年寫起。福婁拜筆下總不給任何救贖,只給幻滅與失敗,所呈現的從來都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商品洪流,無止盡對於身分地位的追求,吞沒了包法利夫人,也捲進了這一對曾經純真的青年。
★阮若缺 (政治大學歐語系教授) 精采專文導讀
作者簡介:
古斯塔夫.福婁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一八二一年出生在法國盧昂,父親為當地知名外科醫生。自小接觸醫院的環境提供早慧的福婁拜極佳的觀察素材。中學時期,福婁拜熱中閱讀浪漫主義作品,使得早期作品帶有感性奔放的色彩。在他十五歲時,苦戀一位音樂出版商的妻子愛麗莎,一說此為《情感教育》阿爾努夫人的原型。
之後行遍各地的福婁拜,寫作理念轉向寫實主義。十九世紀五、六○年代,是福婁拜創作的高峰期,先後完成了《包法利夫人》、《薩朗波》、《情感教育》三部代表作。一八五七年出版《包法利夫人》轟動一時,被指控敗壞道德風俗,之後法院判決無罪,福婁拜由此聲明大噪。一八六九年出版《情感教育》,於法國文壇引發討論。不少人認為與《包法利夫人》相比,《情感教育》顯得平板無奇。然而這部著作,卻先後獲得喬治.桑、莫泊桑、左拉、普魯斯特等名家高度讚賞。象徵著小說審美觀由故事情節取勝,轉變為講究反映真實生活的層次,影響後世作家無數。
福婁拜被視為寫實主義代表作家,重視細節刻畫與用字精確,對待作品要求完美。他每天寫作七、八小時,一個月生產二十多頁的稿子,稍有瑕疵便銷毀。一八八○年,福婁拜腦溢血逝世,留下了《包法利夫人》、《蕯朗波》、《情感教育》、《聖安東尼的誘惑》、《三故事》等不朽著作。
譯者簡介:
梁永安
臺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目前為專業翻譯者,完成約近百本譯著,譯有《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老年之書》、《文化與抵抗》等書。
章節試閱
【試閱內容1】
快走到店鋪末端的帳房時,他故意加重腳步聲,好讓別人聽見。
帳房的門簾掀開,阿爾努太太就在眼前。
「啊,是您!您在這裡!」
「對。」她回答說,因為情緒激動因而顯得結結巴巴:「我在找……」
他看到她的手帕放在書桌附近,猜想她來店裡是要了解店鋪的帳目,消除她的焦慮。
「您或許是要來買東西的吧?」她問。
「只是微不足道的東西,夫人。」
「這些店員老是不見人影,真不像話!」
他不打算責怪他們。相反地,他慶幸現在這樣的情況。
她用諷刺的目光盯著他:「唔,婚事辦得怎麼樣...
快走到店鋪末端的帳房時,他故意加重腳步聲,好讓別人聽見。
帳房的門簾掀開,阿爾努太太就在眼前。
「啊,是您!您在這裡!」
「對。」她回答說,因為情緒激動因而顯得結結巴巴:「我在找……」
他看到她的手帕放在書桌附近,猜想她來店裡是要了解店鋪的帳目,消除她的焦慮。
「您或許是要來買東西的吧?」她問。
「只是微不足道的東西,夫人。」
「這些店員老是不見人影,真不像話!」
他不打算責怪他們。相反地,他慶幸現在這樣的情況。
她用諷刺的目光盯著他:「唔,婚事辦得怎麼樣...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前程遠大的學子
第二章 達蒙與皮爾厄斯
第三章 感傷與激情
第四章 難以形容的她!
第五章 「愛情不曉得法律為何物。」
第六章 前途無亮
第七章 命運的逆轉
第八章 腓德烈克的款待
第九章 全家人的朋友
第十章 賽馬場
第十一章 晚宴和決鬥
第十二章 小露薏絲長大了
第十三章 可愛的土耳其女人羅莎妮
第十四章 街壘
第十五章 「能與她倆其中之一在一起將會何等快樂。」
第十六章 羅莎妮帶來的壞消息
第十七章 奇怪的妓院
第十八章 法拍會場
第十九章 悲欣交雜的重逢
第二十...
第二章 達蒙與皮爾厄斯
第三章 感傷與激情
第四章 難以形容的她!
第五章 「愛情不曉得法律為何物。」
第六章 前途無亮
第七章 命運的逆轉
第八章 腓德烈克的款待
第九章 全家人的朋友
第十章 賽馬場
第十一章 晚宴和決鬥
第十二章 小露薏絲長大了
第十三章 可愛的土耳其女人羅莎妮
第十四章 街壘
第十五章 「能與她倆其中之一在一起將會何等快樂。」
第十六章 羅莎妮帶來的壞消息
第十七章 奇怪的妓院
第十八章 法拍會場
第十九章 悲欣交雜的重逢
第二十...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