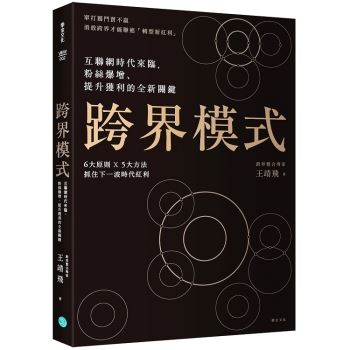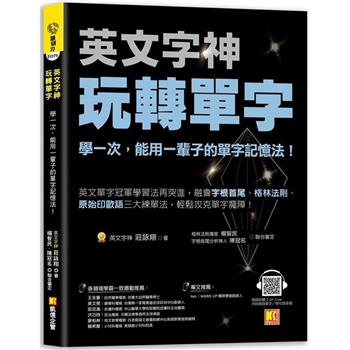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手斧男孩.落難童年求生記的圖書 |
 |
手斧男孩‧落難童年求生記:紐伯瑞文學獎暢銷作家Gary Paulsen自傳小說 作者:蓋瑞.伯森 / 譯者:顏湘如 出版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2-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45 |
兒童文學 |
$ 263 |
Books |
$ 276 |
10-12歲 |
$ 277 |
成長小說 |
$ 277 |
少兒文學 |
$ 277 |
Books |
$ 277 |
Books |
$ 277 |
Books |
$ 277 |
讀書共和國 |
$ 308 |
中文書 |
$ 315 |
親子共讀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紐伯瑞文學獎」作家蓋瑞.伯森自傳小說
※《手斧男孩》荒野求生故事的初心與原點
※ 最真實、最感人的精采童年故事!
※《紐約時報》年度最佳童書(中高年級)
糟糕的大人、善良的大人,以及被迫求生的小男孩。
父母是酒鬼,學校如地獄,
只有森林和圖書館是男孩的安全堡壘……
這一次,蓋瑞.伯森帶來自己親身經歷的精采故事,
不只要在荒野求生,更要在充滿惡意的世界存活下來。
「家」是他沒有的東西,從來沒有過。
二戰末,五歲的男孩獨自搭乘長途火車,離開母親和芝加哥城,來到北方的阿姨家農場。在農場裡,來自都市的男孩第一次撿雞蛋、釣魚、騎馬、划獨木舟、跟鵝群打架,種種大自然初體驗讓他大開眼界,每天都過得刺激又好玩,更在這裡找到了家的溫暖。
某天,母親突然現身農場帶走男孩,搭船前往菲律賓美軍基地與男孩父親團聚。沒想到這竟是一切噩夢的開始──面對成天酒醉的父母,他從此變成了沒有家的孩子。白天,他在廢墟與暗巷間潛行,到森林中自己打獵覓食,在酒吧賺取微薄薪資。夜晚,他窩在地下室裡過夜,與老鼠為伴。
男孩逃學也逃家,一心只想趕快長大。在一個寒冷的冬夜,他遇上一位善良的圖書管理員,她不但帶領男孩打開閱讀的大門,還送給他一份珍貴的禮物,讓他漸漸找到自己真正的天賦……
──徘徊在森林與圖書館之間的童年,苦中作樂、笑中帶淚的動人成長故事──
本書特色
★紐伯瑞文學獎作家蓋瑞.伯森自傳小說
最受青少年喜愛的故事大師蓋瑞.伯森,帶著親身經歷的成長故事回來了!
本書雖是自傳,讀來卻像是小說,揭開創作不輟的故事大師未曾吐露的真實年少故事,是八十歲的蓋瑞.伯森以智慧老人之魂神入當年的小男孩,回看人生關鍵轉捩點的原點之書。
★《手斧男孩》荒野求生故事的初心與原點
沒有這本書裡發生的一切,就沒有《手斧男孩》!如果《手斧男孩》系列六集你還看不過癮,更不能錯過這部堪稱一切冒險起源的真實故事。除了精采有趣的荒野求生,本書更將帶領讀者經歷一個孩子為徬徨心靈尋找到出路的動人成長之旅。
★一個關於勇氣與成長的感動故事
這本成長回憶錄就像《少年小樹之歌》遇上《頑童歷險記》,記錄下男孩在大自然中每個悸動的第一次,也寫下男孩如何以天真的眼睛、幽默的話語看待大人的世界,是讓人看見如何在黑暗中拾起勇氣、努力活過每一天的希望之書。
作者簡介
蓋瑞.伯森(Gary Paulsen, 1939~2021)
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先後當過卡車司機、獵捕人、導演、演員、歌手、水手、工程師、農夫、教師,也曾經淪為酒鬼。年過八十依然創作不輟,是美國聞名而多產的作家,從西部小說到家用維修,各類題材應有盡有,絕大部分取材自他個人的實際經驗。文風精簡樸實,常以人類與大自然的交會為寫作主題,文評家經常拿他與海明威並比。寫作生涯中出版近200本書,共有十多種譯文,在各國都備受青睞,出版總冊數達3500萬。
伯森不僅榮獲美國圖書館協會(ALA)頒贈的瑪格麗特.愛德華終身成就獎(Margaret A. Edwards Award),以表彰他對青少年文學的貢獻,其著作《手斧男孩》﹙Hatchet,系列書皆為野人文化出版﹚、《Dogsong》及《The Winter Room》三書更獲美國知名大獎「紐伯瑞文學獎」肯定。
譯者簡介
顏湘如
自由譯者,譯著包括《終結狩獵的女孩》、《畫鳥的人》、《消失的另一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