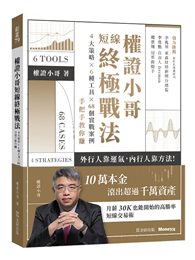Nu yabu o pongso yam, ala abu ku u.
如果沒有這個島嶼,我是不存在的。
真誠‧憂傷‧源自心魂的呼喊
蘭嶼祖島原始情感的承載與追尋
夏曼‧藍波安最新長篇小說《安洛米恩之死》
以獨有的達悟人的海洋文學,向長期對抗惡靈的島魂致敬
請記住我們獵魚家族的名字是卡夫烙,是航海家族
老人家逝去後,你長大成人時
願你如巨岩般的堅強,不自甘墮落
關於地瓜,它是配合魚類的食物
長大成人時,你必須繼續種植我們辛勤開墾的土地
我與你母親要詛咒懶惰的孩子
但願你可以牢記老人家的語言
安洛米恩,航海家族的後裔,繼承達悟人血液裡的海洋脈動,腦袋與靈魂都銘刻著古老的神話與智慧,在水世界裡,他是資質一流的潛水夫。
回到陸地上,安洛米恩被族人視為不正常的「神經病人」、「零元先生」,沒有讀寫漢字的能力,沒有賺錢的工作,獨居於海邊的洞穴、山上的工寮,抓魚,喝酒,撿菸、望海;他痛恨將核廢料帶來島上的政府,瞧不起給酒灑錢充當說客的黨工,嘲諷飛魚季節卻不出海捕魚的「殘障男人」,於是他成為一個無人願意靠近的狂人。
唯一的寄託是部落裡的一個男孩,達卡安。他對安洛米恩說:「Yaji makangai o vatevatek do uwu ko u.」(裝不下那些漢字,在我的頭。)他們是一樣的,達卡安逃開陸上的教室,跟著安洛米恩進入了海底世界,這一對心魂相通的師徒,潛游於流動的活性洋流裡,學習如何與無私的魚類相處相遇。安洛米恩想著,有一天,他要把家族的航海故事告訴達卡安,讓他長大了以後,有傳統知識可以依賴,有海浪有魚類可以過生活……
怎麼辦呢?我們的未來。
潛入海裡,現在,好嗎?
作者簡介:
夏曼‧藍波安
1957年生,蘭嶼達悟族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淡江大學法文系畢業。集文學作家、人類學者於一身,以寫作為職志,現為專職作家,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的負責人。
在他細膩優美、詩意的筆下,海洋、飛魚、傳統達悟人的生活智慧和現代衝擊下的悲喜,皆成了他創作的核心,出版以來獲獎不斷,1992年《八代灣神話》獲中研院史語所母語創作獎,1999年小說《黑色的翅膀》獲吳濁流文學獎、中央日報年度十大本土好書,散文《冷海情深》獲1997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十大好書、《海浪的記憶》獲2002年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漁夫的誕生〉獲2006年九歌年度小說獎,並為同年第23屆吳魯芹散文獎得主,並以《老海人》獲2010年金鼎獎。2012年《天空的眼睛》,獲得該年度中時開卷好書獎。2014年《大海浮夢》,寫下他終於實現童年的航海夢的珍貴旅程,入圍2015年聯合報文學大獎。
章節試閱
安洛米恩從小有耳朵,可以辨別他人的,或是父母親的聲音的時候,在每天的黎明之前,就開始聽父親唱這一首詩歌了。每一天,每個月,每一年,直到他父親去世之前的黎明才落幕。他長大後,這首詩歌也成了他的神話,後來他死後,他也成了島嶼的神話傳奇。
五十多年以前的一九六三年,安洛米恩出生後,他的父親在每一天的凌晨望著黑色的天宇與海洋的時候,開始喜愛哼著這首詩歌,說,這首詩歌是他家族的智慧財產,因為是獨子,他的曾祖父懷念祖先的航海故事;也是台灣政府殖民蘭嶼之後,他家道中落留下的一首航海詩歌,其他家族的男性在公共場合的部落會議是不可以剽竊吟唱的歌。
他的父親也理解,島上不同的家族也都是航海家族的族裔,只是在一八九七年島上來了日本民俗學者、日本武警之後,島嶼與島嶼之間的航海軼事,被日本人戳破了民族航海偉業的傳說故事,認為日本人更為厲害,從北方找到這個孤懸在西太平洋的小島,說,日本人的船不需要使用雙手划就可以遠航,說那是mi kikay(機械船)──以人之島(蘭嶼島)為中心的世界觀被征服了。這個時候,換了不同的殖民者——台灣政府。當他從父親那兒不斷地聽這首詩歌的時候,他很不以為然地認為,說,那是他們那個世代不成文的陋規,說,那個世代的前輩,生活在日本皇民與漢民銜接之間的縫隙裡,喜愛編造厚古薄今的故事,喜愛創作吟詩哼唱作為消磨寂靜黑夜的資本。他不以為然,也是因為他意會不出歌詞的意涵,以及歌詞背後的航海背景,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他父親就是十分自然的喜歡跟他說這一則故事,以及民族的童話故事。
安洛米恩也像是傻子似的耳朵不拒絕,腦袋不思索。他或許不太能夠理解,認為傳說故事只是傳說的功能而已,什麼風雲變色,什麼濤聲震天、海霧豪雨遮天等等的大自然氣象。問題出在於耳朵不拒絕之後數年,傳說的功能在他的腦海紋路自然就鑿出了一道很深的腦紋水圳,就像女人看世界有她們的感官細膩之絮語,深埋在女性看世界的心底。那是安洛米恩的父親仙逝數年後,在他已二十四、五歲的時候,部落裡也出現了跟他一樣喜歡逃學的少年,叫達卡安,他因而開始思索他認為的傳說故事。
這個時候,他的父親的吟詩哼唱也成了他的傳說,他問自己,為何至親親人死後,腦海才浮生出思念呢?那一夜,他在屋外一個人守著原來是望族的家屋,此時的當下守著簡陋的鐵皮屋,家道中落彷彿是惡靈咒語的實現,即使隔壁家的孩子們──他說是品質差的正常人──在這個時候的當下,島嶼現代化後的成就比他好上十倍,家裡所有的電器化設施都十分的齊全,反觀他,自稱是優質家族,就連塑膠椅子也買不起,即便是如此的結果,但他依然承繼他父親的觀念,依然說他們是品質差的正常人。他拱著身子,背靠在立著的石板上望星空,然而,kavavatanen(傳說),那又是什麼呢?天空的眼睛(註1),你可以告訴我嗎?這是他的經典名語。
他開始思索,從他父親死後,他一直解不開這個謎題,構成他極為苦惱的泉源。部落裡的周牧師,曾經跟他說過,說:「來教會吧!跟上帝禱告,祂可以改變你的命格。」這句話聽在他耳裡,不知道已經累積了幾百個星期,但他不為感動,他認為上帝是西方人虛構的,是用來侵略、欺騙非白人世界的弱勢民族的伎倆,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跟天空的眼睛如此對話。但是有了「逃學少年」─—達卡安,跟他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逃學遭遇,步他的後路,他的心海寬慰了許多,他認為,他可以傳授這一則故事給達卡安,雖然是不同的獵魚家族(註2)。想著想著的時候,他笑了起來,說,我有學生了,比自己幻想天空的眼睛有人住實際得多了。
夜色的平靜開啟他心海的思路,他自言自語的說,「逃學」的意義,是從漢人的角度來論斷非漢人拒絕學習漢人的歷史觀、抵抗漢人學制的小孩說的話,在他的父母親的時代,就沒有所謂的「逃學」。而他一九四五年生的大表哥開始上學的時候,也是逃學者,後來是怕被老師鞭打,才不情不願地上學了。
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蘭嶼國校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他認為死人比活人要多,是死人累積的死相,讓活人參考他的活相,認為死是歷史的「時間表」,下一輪,就是他們這個世代的人了,讓活人弔念死者,或者是死相比前人更為難看,就像他父親死的時候,嘴巴還會閉起來,兩個哥哥死相就沒有他父親優雅,死相如世界欠他們似的感覺,幸好是他把他們在台灣的C市火化,在台灣當孤魂,否則他是不願意走進陰森森的傳統墓場的。如果是他死了,自己又沒有小孩,想著自己將留下什麼給下一代的活人呢?他的死相會如何呢?他問自己。
「逃學者」,他不喜歡這個詞,因為這樣,他才被部落的人稱之腦袋有問題的人,但他聽周牧師講《聖經》裡的故事的時候,說,耶穌是因為反抗羅馬人才被釘在十字架,也就是說,就是對抗外來殲滅自己原有文明的侵略者,所以自己是「反抗者」而非「逃學者」。哼哼,他笑了起來,你說,我是不是「反抗者」,天空的眼睛。明媚的星空,寂靜的深夜的環境,多少滿足了他的幻想。
*
達卡安從小學一年級起,就喜歡跟他的外祖父上山砍柴,喜愛上山挖土,種山藥、里芋等根莖植物。喜愛跟著外祖父,看著外祖父沿著礁岸潛水抓章魚、挖五爪貝,他特別喜歡在野外無拘無束地活動,可以不受學校制度的制約,不受上下課的時鐘牽制心魂的自由。達卡安的外祖父逝去那天,是他小學畢業典禮的那一天,換句話說,達卡安跟他相同,島嶼民族被殖民後,學校的第一張畢業證書,他們都沒有領取的,就如他的父親、達卡安的外祖父也都沒有從日本人手中接過畢業證書,「同是天涯淪落人」,想到此,他短暫會心一笑,畢竟「傳說」的意義,他還沒有解開這個他心中的謎題。
安洛米恩也看著達卡安從小就在海邊自己玩耍,戴著他父親的潛水鏡在淺海海溝找貝殼果腹,與潮間帶的小魚兒玩耍長大,這也是完全跟他相似的成長過程,海邊是他們真實的教室,付出真感情、真感覺的地方,累的時候,就在陰涼的礁石縫隙睡午覺。那一天的中午,陽光曬著海面,無影的熱浪像是大自然的蜜糖,吸住安洛米恩胸膛肌膚的毛細孔。安洛米恩手提著他簡易的潛水抓魚的漁具,如魚槍、蛙鞋、蛙鏡等等的,從他的鐵皮屋走向部落船隻進出海的灘頭,在潮間帶遇見了剛失去外祖父的、無法領取小學畢業證書的達卡安。他習慣性地坐在波浪拍打陸地的沙岸,腰部以下泡在海裡,腰部以上給太陽曬著,邊洗蛙鏡,邊抽著手捲菸絲,邊看著移動的海浪,說:
「Tagangan, mu jyangayi do gak-ku?」
(達卡安,你不去學校,為什麼?)
達卡安望著比他大十來歲多的,部落人說是神經病的人安洛米恩。他的直覺感受是,安洛米恩很健壯,對他很友善,好像不是神經病的人,說:
「Yaji makangai o vatevatek do uwu ko.」
(裝不下那些漢字,在我的頭。)
「Yaji makangai o vatevatek do uwu ko.」他重複地說:
(裝不下那些漢字,在我的頭。)
說話的同時,某種被學校制度排擠的自卑顯露在他稚嫩的面龐,是一群孩童學習外來文明的落後者之失落樣,他彷彿很不喜歡這個結局似的,無奈教他寫漢字、背國語注音符號,如是在割裂他肌膚似的痛苦,還好還有海洋可以讓他消磨童年。於是又回道,說:
「Yameingen o uwu ku,nuku mivatevatek.」
(很痛我的頭,當我寫漢字的時候。)
安洛米恩聽在耳裡,思索了一番,而後仰天爆笑,握腹吹淚,露出一張俊俏得意樣的青年面容,他心裡想著,怎麼跟他完全相同,「裝不下那些字,在我的頭」。這一幕,看在達卡安眼裡傻住了,他心裡想著,這個被部落的人稱之「神經病」的人,怎麼不像是神經病的人呢!他繼續爆笑,十步路的時候,達卡安心海十分莫名地問道:
「Ikong mu ikaming?」
(什麼?你笑。)
五步路之後,安洛米恩敞開笑臉說:
「Ta miyangai, yaji makangai o vatevatek do uwu ko u.」
(我們一樣,裝不下那些漢字,在我的頭。)
達卡安淡淡地笑著,十來歲的小孩,剛剛啟程認識這個世界,「裝不下那些漢字」,是他未來在台灣社會生存的基礎,與漢人共事的工具。
「你會寫你的名字嗎?」
「Ku jiya tengi.」
(我不會寫我的名字。)
這是很慘的事,安洛米恩如此想,他最起碼還會寫自己的名字,達卡安又再次地暴露出自己對寫字的無奈,而午間直射他們身體的陽光,並沒有因他們的對話,不適合生存在漢人移民該島之後的歲月而有所憐憫,惟達卡安身體被曬燙的時候,便把頭泡在溫涼的海水裡。
他們在學校共同的感受,某種特質,也是共同被記錄的成績。他知道安洛米恩,算是他部落裡的長輩,也是傳聞中的shumagpan a Ta-u,漢語說是「不太正常的人」。他十分茫然,安洛米恩敞開笑容的臉,似乎沒有部落的人說的那樣不可理喻的,神經兮兮,形容的那種人。他瞬間感受是,他的人很可愛,血脈基因的感覺彷彿可以接納他。
「Macilulu ka jyaken?」
(要來跟我嗎?)
安洛米恩笑道,心中思索著,「希望他成為我的學生」。他想著,若實現即可滿足他當野性海洋老師的願望,吸收跟他相似的遭遇,「腦袋裝不下漢字」的晚輩,對他來說,是真實的畢生願望。
他,一位少男,濃濃的願望如是波波浪花襲上達卡安的心頭,想跟他,看他潛水射魚。想到此,他的心脈開始跳動,願望開始篝火在波浪拍岸的潮間帶,身邊的波浪在晃動,他感覺海水好像沒有睡過。還有外海裡的珊瑚礁岩的原住民生物,許多魚類的曼妙身影,是他極度想要裝在腦海裡的記憶,而且是強力的願望。達卡安站在海裡,看著安洛米恩微笑地清洗潛水鏡,含蓄地回道:
「Apiya a?」
(可以嗎?)
安洛米恩的心魂活絡了起來,心海的喜悅如是他的鐵皮屋點燃著一炷蠟燭,假裝威嚴的點點頭,神情轉為嚴肅,彷彿是學校老師的模樣。小島上使用自製魚槍潛水抓魚的人都知道,他們面對的是野性流動的洋流,要知道洋流的變換,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海洋在不同季節時的詭異變換,以及潮汐與月亮圓缺的直接關係。此刻他思念父親傳授給他的相關於此的經驗、知識,還有他自己的親身驗證。現在雖然是白天,陽光炙熱的午後時段,水世界裡的能見度也很好,潛水的地點,也只不過離陸地礁岸二十公尺以內,帶著十二歲的少男浮升浮沉的游泳兩個小時,在安全上是不會有問題的。然而,安洛米恩的心靈儀式是,招收學生——是他傳授海洋知識,口述傳說故事的對象;再說,他也理解達卡安如部落的人,知道他被形容為神經病的人,是思想不正常的人,雖然他不以為自己是那類型的人,但是他的第六感,似乎可以感悟到達卡安是屬於野性海洋的少男,IQ差,本性質感佳,這一點他認為,他們也是相通的,說自己是屬於優質的人格。所以他嚴肅起來就是要證明自己在達卡安心目中是正常人,是潛水抓魚的好手,想取得達卡安發自心中的尊敬;這個「尊敬」是他極度渴求的,來均衡自己被他人視為非正常人的人格。
「Jika unib syo?」
(你不可以害怕哦!)
「Jyata kamiyan mu maran.」
(有叔叔在,我就不害怕。)
達卡安被學校同學說是頭腦簡單的人,說他父親娶了部落裡最笨的女人,他理解笨的意義就是不聰明,讓他從小不愛母親,愛外祖父;但是愛外祖父,並不會減少他的自卑感,他也不喜愛與人辯證許多事件的是與非,諸如台灣好、念書與不會念書、蘭嶼不好等等的童年話題。但他非常理解,他是所有同學裡喝鹹海水最多,最不畏懼海浪的孩子,同學在教室學習漢人馴化原住民的課程的時候,他逃走,他遠離那位也是達悟人的老師,而後去海邊用身體親近大海,喜愛看海裡的生物,在海邊泡水令他常常忘記肚皮的飢餓,樂不思校。此刻偶遇安洛米恩邀他游泳潛水抓魚,認為這是他學習海洋的脾氣最佳的初始機會,學校不可能安排的,他最愛的課程。他的心魂如是媽媽燃燒柴薪煮地瓜時的金黃火苗,讓柴煙冉冉昇華的狀態。
天空上的太陽如是所有地球上的小島之不滅的燈罩,也是整片的海洋生物永續的能量來源,把淺海處的海底照明得非常清晰。小魚兒嬉戲在陽光直射照明的海底,透過陽光可以讓徒手潛水者理解亞潮帶魚類的原始習性。
此刻,安洛米恩腰部泡在海裡閉目,口中念念他自創的達悟語祝禱詞,內心裡的那股虔誠的精氣,看在達卡安的眼中,勝過他與父親每年參與天主教聖誕節的午夜彌撒,那位瑞士籍神父的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來得更謙卑,當安洛米恩祈禱的時候。
他感覺安洛米恩的禱告比神父精緻,美感,讓少年的他初始感悟達悟人對海神的敬重是民族的固有基因。讓他想起了外祖父跟他說過的話,說:信奉天主教是因為可以獲得麵粉,可領從台灣來的衣服,不是民族原來的宗教。顯然島上的天主教、基督教是後來的宗教,他推測。這一幕,看在他眼裡,喜愛極了,想著,大海偌大,它的變化從他開始逃學起已經看了六年,海浪發情的時候,就是颱風,逼著人類躲進屋裡,安全期就是風平浪靜,邀請男人下海,女人在潮間帶採集貝類,發揮它的人性的時候,就會帶來飛魚群,它是值得敬愛的。
安洛米恩祝禱之後,二話不說地便把胸膛撲向海面,浪沫碎花運行期間,雙腳輕拍蛙鞋。安洛米恩的結實身子便浮在海面緩緩地由淺淺的礁石與鵝卵石築成的小海灣前行移動到外海。他的左手握著魚槍,蛙鏡注視著海底礁壁岩洞,時而憋氣下沉,時而浮升換氣,他如魚兒游姿般的自然,觀察海底的環境。這個時候,達卡安如是水芋田裡的田蛙,用他熟練的蛙式游姿隨後。如此帥氣的潛游,讓達卡安的初始游向外海的心魂羨慕極了。心裡想著,他很正常啊!根本就不是神經病人嘛!難道說,海浪會醫治神經病的人的神經嗎?達卡安邊想著,也邊以最自然的如田蛙似的游法跟隨,他喜歡這種無拘無束的,浮在大海的感覺。
陽光直射海底的光線如安洛米恩長髮披到肩背的幻黃髮絲隨著洋流曲折起舞,也如隔壁家的,他心儀的那位少女的長髮隨風飄逸,讓他第一次感悟到,說,海底的洋流是海裡的風,可以感受到,卻看不見,讓他忘記了他絢麗的頭銜「零分先生」。安洛米恩身子停住,頭殼露出海面透過波浪頻道跟他說:
「Jika unib an!」
(不可以害怕,好嗎?)
「Tuka ngiyan jiyan.jimu miyavasi yaken.」
(你就浮在這兒,游泳時不可以超越我。)
達卡安點點頭,這是他的第一節課。
「游泳時不可以超越我。」這是什麼意思?
達卡安戴著父親的圓形面鏡,讓他觀賞水世界的視野很大,從他的腳下看,他的左右邊,而後延伸外海深處,他的初始感官水世界的顏色,從蛋白,土耳其藍,青藍,綠藍,深藍到墨綠色的,不可知的很遠很深邃的神祕水世界,但是他沒有呼吸管,於是每一次吸了一口長氣,即可憋氣久一點,一次又一次的循環憋氣換氣。嗯,很自然,他想,滿足他飽覽水世界的內太空,對神祕水世界的好奇油然而生,這真是個浩瀚的教室,他心裡默想著。這是晴朗的天氣恩賜給他第一次外海潛泳的良機,給了他最絢麗的海世界,此景讓他下定決心,日後當個優質的潛水人。
他的第二課,就是訓練自己憋氣,憋氣的觀賞安洛米恩潛入海裡的英姿。約莫二十來分鐘之後,一斤以上游移速度很快的一群十餘尾的白毛魚(註3)忽隱忽現在海底裡的海溝,安洛米恩在海面上觀察魚群的性情很久,而後在達卡安眼前不疾不徐地拍動蛙鞋潛下去,首先映入達卡安眼裡的是安洛米恩的大腿肌肉,蛙鞋交替拍動之際,左右邊的大腿肌肉被海水壓力壓得像是豆腐般的軟,這個原理,他還不能理解,第一次見過,他心海如此想。安洛米恩潛到八公尺深的地方,便把身子鑽進溝洞裡,只見到蛙鞋小拍的半個身子,想著,潛水射魚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嗎?他記住在腦海,一分鐘過後,安洛米恩從洞裡浮升,左手握著木槍,此時鑄鐵魚鏢末端穿刺著一尾白毛,緩緩地浮升到海面,此刻他的眼睛又閱讀到安洛米恩的胸肌像是陣風吹動的茅草草原,隨浮升的速度上下移動,肉皮內的肌肉像是水球,扁上去扁下去,一絲結實感也沒有,好奇特,他想。安洛米恩在海面換了一口氣,接著把食指穿進魚鰓,刺死魚兒,紅色的血在海水裡成綠色,他看見了,也學到了,此刻安洛米恩很認真地對他說:
「Pangangapan ko ya, naknakmen mo,jimu mananawuhan do ta-u.」
(這是我射魚的魚庫,請思考在你心裡,日後你不可以跟他人說。)
「Ikongo pangangapan.」
(「魚庫」是什麼意思?)
「那裡有一個洞,是魚兒躲避人類獵殺牠們時,躲藏的洞,就是牠們在海裡的家,稱魚庫。」
「Nuwun.」
(好的。)
「Kama li-hai mo Ngalumirem.」
(安洛米恩,很厲害你。)
安洛米恩浮出愉悅的嘴臉,接著說:
「Jyata nanawuhen ku imo.」
(只要你跟我,我會好好教你。)
註1:達悟語意指天語繁星。
註2:漁團家族。
註3:白毛魚,達悟語稱之ilek,被歸類為女性、孕婦吃的魚,屬於精明的魚類。
安洛米恩從小有耳朵,可以辨別他人的,或是父母親的聲音的時候,在每天的黎明之前,就開始聽父親唱這一首詩歌了。每一天,每個月,每一年,直到他父親去世之前的黎明才落幕。他長大後,這首詩歌也成了他的神話,後來他死後,他也成了島嶼的神話傳奇。
五十多年以前的一九六三年,安洛米恩出生後,他的父親在每一天的凌晨望著黑色的天宇與海洋的時候,開始喜愛哼著這首詩歌,說,這首詩歌是他家族的智慧財產,因為是獨子,他的曾祖父懷念祖先的航海故事;也是台灣政府殖民蘭嶼之後,他家道中落留下的一首航海詩歌,其他家族的男性在公共場...
作者序
後記
※
安洛米恩的哥哥齊格浪,是我與吉吉米特、卡斯瓦勒的小學、國中同學。我們是蘭嶼國中第二屆的學生,島上六個部落的孩子,除去朗島部落外,五個部落的孩子聚集椰油部落念國中,青澀的臉龐,整日在學校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磨蹭,可以說是我們民族近代歷史的一大盛事,同時也是我們這個世代,出生於戰後的一九五〇年代的青少年開始認識新民族、新帝國、學習新殖民者的新語言、新文化,開始了我們夢的迷思的旅行。
我們六個部落說達悟語的口音各有差異,可是卻要學習共通說四音階的華語,以及英語,於是語音的差異發生了許多許多的笑話,譬如,A部落的同學朗讀華語:
「該洩了,該洩了,席校燜狗刮著過起,打價瀨了,同溪瀨了,老師一賴了……」正確的華語念法如下:
「開學了,開學了,學校門口掛著國旗,大家來了,同學來了,老師也來了……」
B部落的同學念:
「該薛辣,該薛辣,席校悶購寡之果器,打家ㄌㄞˇ辣,董希ㄌㄞˇ辣,ㄌㄠˋ師一來辣。」
又如:
「老是,搭說,搭又打勿嗎?」
「老師,她說,她有打我嗎?」
「米油補賴,搭燜朔的。」
「沒有不來,她們說的(她們說,她不要來)。」
諸如其他部落的同學,用達悟語音說華語引來許多的笑話,一到了晚上,宿舍裡的笑話就連篇連夜,連夜震動玻璃窗,夾著相互認識的好奇。達悟語、華語,兩種語言交叉的混音,這個過程最佳的模仿者是由最為頑皮的卡斯瓦勒所發動。
我們這一屆國中同學的出生年約是由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八,我們男同學的宿舍是工藝教室,每一個人一張三尺寬六尺長的合板為床,以桌子為衣櫥,為界線。
我的睡床左邊是齊格浪,右邊是卡斯瓦勒,頭對頭是吉吉米特。齊格浪是個安靜、寡言的同學,面容的皮膚都比我們白而嫩,然而每一個夜晚,我不曾聽過齊格浪跟我說過他未來的夢想,包括他的初戀情人,出社會後來成為情侶。我們國三時,他的大弟也過來念國中,從那時起安洛米恩開始來國中「要飯」與逃學,開始認識了我。他來國中,我們就會偷偷留白飯給他,安洛米恩於是對我有了好印象。
當我高中畢業,出社會的第二年,就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在板橋染整廠工作,遇見三位在土城工業區工作的同學,其中之一,就是齊格浪。見到他,嚇我一跳,他變得很壯,很粗獷,不得志的眼神讓他變得非常喜歡抱怨,很怨天尤人。然而,外來「文明」入侵我們的島嶼之初始,我們這一代的達悟人,又有誰是得志的呢?
時光飛逝,一九八一年齊格浪回蘭嶼家,開始在《蘭嶼雙周刊》發表「小說」,當時蘭恩的創辦人跟我說這個事情,言下之意,我是當時的大學生,他也希望我寫「小說」。雖然我讀的是法文系,讀法國文學,然而,何謂「小說」,我一點概念也沒有,甭說寫「小說」。可惜同學寫的小說,我沒閱讀到。
當我大學畢業,在台北開計程車,搞原住民運動,有一天我接到南港山胞服務中心的電話:
「認不認識齊格浪與他的弟弟。」
「認識。」
原來齊格與他的大弟都住進了北市信義路底的精神病療養院,我當保證人把兄弟倆從醫院領出來。醫院交代我說:「他們不能喝酒。」那是一九八六年的七月,同年的九月,齊格浪跳樓自殺身亡。我當時跟朋友們募款,他的父母親與安洛米恩從蘭嶼來桃園,那一趟是安洛米恩第一次來台灣,他又遇見了我,同時開始跟我要菸抽。
一九八九年我回祖島定居以後,安洛米恩在蘭嶼機場常常遇見我,很自然地要菸抽,開始跟我說他的故事,當他進入他妄想的世界時,他說著達悟語,華語也非常流利,讓我佩服。當時我也開始寫散文,我於是慢慢記憶他的故事與遭遇。
※
我個人從小喜愛遠眺海平線逐夢,追夢。海,給我沒有疆界的無限想像……
國小,我們發現我們自己不是漢人、漢族,不會說華語,於是學校老師給我們稚幼心靈的謎題是:漢人文明,我們野蠻;漢人進步,我們落伍。
何謂文明?何謂進步?這是我個人一直在對抗的問題,也是整個星球人類的問題。筆者從開始說話起就一直生活在喜歡說海浪的故事,造船的故事,夜航獵魚的故事,男人吃的魚,女人吃的魚,燒墾伐木的生活,許多的數不清等等的,都市文明生活律動已遺忘的有機生活,獨占了我成長與求學的旅程。
原來我民族的島嶼生活被學校老師說成野蠻的生活,原來魚類分類的知識被說成是落伍的。時間飛逝,成長的學習是摸索,更是去對抗一元化的價值準繩,如今筆者方意識到,很自信地說,所謂的野蠻!所謂落伍!是我所擁有的,所追求的,是你所沒有的。
在深山裡與父親,叔父,堂叔的伐木經歷,讓我看見了純潔的野蠻美學,讓我身體髮膚深深體悟到原木到雛型到船身到海洋到魚類,那是我民族的環境信仰的核心,就是我們的詩歌文學;與家族裡的男人夜航捕飛魚,夜間潛水捉魚,潛水射魚,男人吃的魚,女人、孕婦吃的魚,海鮮貝類等分類的食的文明,讓我看見了體悟了分享的本質,就是我達悟人的海洋文學,所有的這些都必須經過傳統宗教的儀式。於是我身體髮膚深深體悟到儀式與分類知識是我達悟人的海洋文學,是我們珍愛島嶼環境,海洋生物的具體表現,這些都斧刻在我的身體,以及力行之,學習與環境、海洋相融,這些是你沒有的海洋文學。
※
筆者的寫實小說的真實人物安洛米恩、達卡安、洛馬比克、吉吉米特、卡斯瓦勒,夏本‧巫瑪藍姆、馬洛奴斯,以及筆者本人,都困在現代文明裡的迷題與迷思裡,從現實的島嶼生活來論,我們確實都藉著不同季節的「海洋」不斷地重複療傷,這兒沒有終極結論,只有愈來愈複雜的進行式。
身為書寫海洋律動的情緒的台灣籍的作家,迄今熱愛純文學創作的能量不減,也是我一生唯一的志業,純文學創作是多元而嚴肅的,也絕對是深遠的,你我他的文學作品,其更廣的意涵是,屬於台灣的華語文學,我稱你們是主流文學,我稱安洛米恩、達卡安、洛馬比克、吉吉米特、卡斯瓦勒、夏本‧巫瑪藍姆、巫瑪藍姆、馬洛奴斯等等是移動的「海流文學」。
當安洛米恩來不及把他航海家族的故事說給達卡安的時候,當他的大哥,我的同學齊格浪還來不及書寫的時候,我們的同學吉吉米特已經航海到了英屬法蘭克福群島,南、西太平洋。
這本書深深表達對他們的敬愛,還有我那些把我心魂帶到海上,我家族的海流前輩們,謝謝他們真實的故事。
願野蠻與落伍與我長在
夏曼‧藍波安完稿於新店七張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後記
※
安洛米恩的哥哥齊格浪,是我與吉吉米特、卡斯瓦勒的小學、國中同學。我們是蘭嶼國中第二屆的學生,島上六個部落的孩子,除去朗島部落外,五個部落的孩子聚集椰油部落念國中,青澀的臉龐,整日在學校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磨蹭,可以說是我們民族近代歷史的一大盛事,同時也是我們這個世代,出生於戰後的一九五〇年代的青少年開始認識新民族、新帝國、學習新殖民者的新語言、新文化,開始了我們夢的迷思的旅行。
我們六個部落說達悟語的口音各有差異,可是卻要學習共通說四音階的華語,以及英語,於是語音的差異發生了許多許多的笑...
目錄
安洛米恩之死
一
二
三
四
後記
附錄
這個民族的語言就是詩——陳芳明對談夏曼‧藍波安
海是世界無止盡的追尋 /董恕明
穿過記憶,便是海 /陳芷凡
安洛米恩之死
一
二
三
四
後記
附錄
這個民族的語言就是詩——陳芳明對談夏曼‧藍波安
海是世界無止盡的追尋 /董恕明
穿過記憶,便是海 /陳芷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