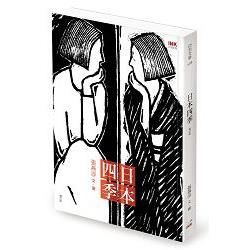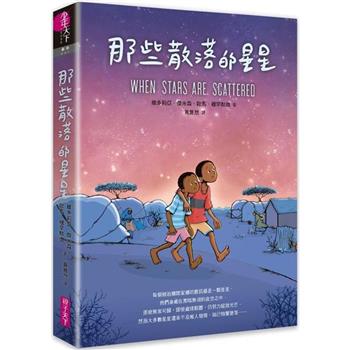新版序
晨間散步,我常習慣性地仰面尋找,找停在四周紅木(sequoia)頂上的鷹鳥,看他們,偶而轉動頭頸,大部時間靜靜棲息,讓人誤認他們是樹頂的枝葉。我想,自他們的高度俯瞰,人們應該都是圓點,你我他沒太大分別。
二〇〇五年夏,我和母親,歡喜坐在一列潔淨的火車中,行向我曾住過的日本小城「茅野」。
火車一路穿山洞樹林,經過蔥綠稻田和果實纍纍的水蜜桃園,農家的紅、藍屋頂由遠處一一來迎⋯⋯明亮的風景,和火車前進的速度律動,讓人心情也有向前衝的亢奮。
我將手中的書,立在椅背小檯上,盯著那黑白封面:這書裡寫的,就是窗外閃逝土地上的事,是十年前我的茅野生活。
如今我帶著才出版的書,帶著初訪茅野的母親,回去看那兒的朋友們—書中故事的真主角。
朋友,大致都見到了。
在田中家,我向牆上老先生的照片行了禮,在醫院,我擁抱了已不能再與我互拜的老太太;在蓋了新樓的幼稚園,我看母親和老修女園長,互相攙扶著爬樓梯;在超市、郵局的櫃檯後,居然還站着兩位熟悉面孔;在小聚會裡,我聽「哈哈」們七嘴八舌講誰誰搬去了福岡、北海道。
小城添了摩登的百貨公司、大賣場、建築新潮的市民館。
我回到舊家門口,看熟悉的窗、門、台階、郵箱。
日本話「もう一度」:再來一次。過去的,不能再來一次。
那些我仍喊得出名字,進進出出我家調皮搗蛋的幼童們,全已上了大學。
二〇一五年春,我的兩個兒子結伴遊日本。
我在家翻舊相簿,找出他們幼時旅行的照片,配合這回將走的行程,一張張傳到他們的手機裡。然後,回訊來了,沒文字,只是照片,兩張一組:一張是我寄去的,另一張則是在同一地點,或與同一些人,二十年後的今天所攝。
照片裡有金閣寺、大阪城、銀座、淺草雷門⋯⋯但寄自茅野的最多,我仔仔細細看了很久。
一張是剛入幼稚園的小兒子,大約正和同伴們搶玩具,滿臉著急,手腳不對稱地歪站著,老修女園長手拿紙摺的飛機,蹲下笑咪咪安撫他。下一張,在陌生的老人院中,患阿玆海默症的老園長笑容天真,我高大的兩個兒子,一左一右蹲在她的輪椅旁。
另一組,頭一張是〈千枚手裏劍〉文中,六歲的「P大」住院時照的。他手腕上纏著紗布,正在打點滴,面對相機,仍擠出一絲疲憊的笑,武井醫生站在床邊,拍著小病童的肩膀。下一張,「P大」醫生摟著已見白髮的武井醫生的肩,親熱感謝幼時的救命恩人。
諏訪、茅野地區有名聞日本,七年才一回的「御柱祭」、我們剛搬到日本時就遇上了,兒子們和對門宮澤家的兩個女兒,穿著慶典童裝的合照太可愛,我寄出了這張。兒子對應寄回的,竟是宮澤家大女兒的結婚照。我驚看小姑娘長成了她媽媽年輕時的模樣,穿著豔紅繡金花的新娘裝「打卦け」,嬌美喜氣。其他家人,祖孫三代,也都鄭重穿著和服,倒是不見老派的拘謹,由新娘領頭全哈哈笑著,看得我也開心極了!
「紅葉狩」時期的佳代子,曾多次邀我們去白樺湖玩雪。我寄出兩家六個孩子穿著花花綠綠滑雪衣,乘雪橇、打雪仗的舊照。兒子則寄來一張佳代子陪他們回幼稚園,坐在教室小桌小椅中微笑的照片。佳代子的兒女都已成家,她的溫和賢淑,現在多用在孫兒身上。
我慢慢讀這些照片,彷佛是以十年、二十年為單位來審視人生。看似你左轉或我右彎的路,其實都仍在同一條大道上。一代接替一代的速度是那麼快,新生或衰老,是如此自然而不可遁逃。
這是十幾年前我寫「日本四季」時還沒有的體會,當時之寫,不哈日不抗日,只是真誠記錄自己在異國的生活經驗,記錄有趣的節慶文化,記錄我遇到的好事好人。
我不曾預想過,記錄下來的四季,正是天地間不斷循環運行的道理,並且那大道理,就藏在平凡小地方。一件圍裙、一樹櫻花、一畝田、一場雨。
二〇一五、八、十五於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