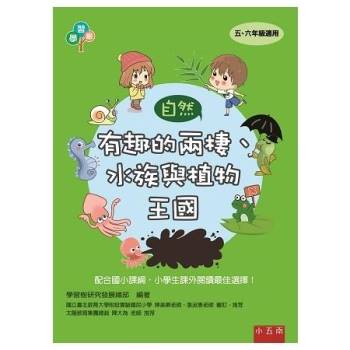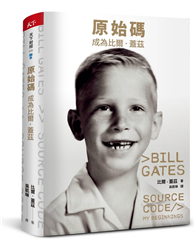後記
陳丹青
二〇一二年底,《文學回憶錄》發排在即,我瞞著讀者,擅自從全書中扣留九講,計兩萬餘字。三年過去了,今天,這部分文字成書面世,總算還原了《文學回憶錄》全貌,但因此與母本上下冊分離,成為單獨的書。
也好。以下我來交代此事的原委——先要告白的實情是:返回八〇年代,這份「課業」並不是聽講世界文學史,而是眾人攛掇木心聊他自己的文章。初讀他的書,誰都感到這個人與我輩熟悉的大陸文學,毫不相似,毫不相干。怎麼回事呢?!我相信初遇木心的人都願知道他的寫作的來歷,以我們的淺陋無學,反倒沒人起念,說:木心,講講世界文學史吧。
大家只是圍著他——有時就像那幅照片的場景,團坐在地板上—聽他談論各種話題。一驚一乍地聽著,間或發問:你怎會想到這樣寫,這樣地遣詞造句呢?
木心略一沉吟,於是講。譬如〈遺狂篇〉的某句古語作何解釋,〈哥倫比亞的倒影〉究竟意指什麼,〈童年隨之而去〉的結尾為什麼那樣地來一下子……幾回聽過,眾人似乎開了竅,同時,更糊塗了。當李全武、金高、章學林、曹立偉幾位懇請老先生以講課的方式定期談論自己的寫作,他卻斷然說道:
那怎麼可以!
總歸是在一九八八年底吧,實在記不清經由怎樣一番商量,翌年初,木心開講了。最近問章學林,他也忘了詳細,但他確認木心說過:「零零碎碎講,沒用的,你們要補課,要補整個文學史,中國的,西方的,各國的文學都要知道。」眾人好興奮,可比得了意外的允諾,更大的禮物。之後,承李、章二位「校長」全程操辦,這夥烏合之眾開始了為時五年的漫長聽課。
一九九三年,文學史講席進入第四個年頭,話題漸入所謂現代文學。其時眾人與老師混得忒熟了,不知怎樣一來,舊話重提,我們又要他談談自己的寫作、自己的文章。三月間,木心終於同意了,擬定前半堂課仍講現代文學,後半堂課,則由大家任選一篇他的作品,聽他夫子自道。查閱筆記,頭一回講述是三月七日,末一回是九月十一日,共九講。之後,木心繼續全時談論現代文學,直到一九九四年元月的最後一課。
二〇一二年,我將五本聽課筆記錄入電腦,一路抄到這部分,不禁自笑了,歷歷想起容光煥發的木心。我與他廝混久,這得意的神采再熟悉不過,但在講席上,他的話語變得略略正式,又如師傅教拳經,蠻樂意講,又不多講,聽來蒼老而平然。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對著人眾,豁出去,滔滔不絕,但以木心的做派,話頭進入所謂「私房話」,他總會找個瀟灑而帶玄機的說法,用關照的語氣,交代下來:
我講自己的書,不是驕傲,不是謙虛。我們兩三知己,可以這樣講講。
麻煩來了—唉,木心扔給我多少麻煩啊——《文學回憶錄》數十萬言,可以說都是他的「私房話」,這九堂課,更是私房話裡的私房話。現在臨到出版,這部分文字也發布,是否合適?
「私房話」一語,固然是木心調皮,可作修辭解,但他有他的理由,且涵義多端,此處僅表其一:通常的文學史著述者未必是作家,而木心是,所以他的話,先已說到:
在學堂、學府,能不能這樣做?
我們才不管那些,巴不得木心毫無顧忌,放開說。麻煩是在下一句:
要看怎麼做。
他怎麼做呢,諸位在本書中看到了。可是三年前擬定出版《文學回憶錄》之際,「要看怎麼做」便成了我的事情——木心生前不同意我的五本筆記對外公開。他去世後,「私房話」語境終告消失,新的,令我茫然失措的狀況出現了:他的大量遺稿,理論上,都是有待面世的文本,那是他的讀者殷切期待的事——哪怕不過數十人、數百人——出版《文學回憶錄》,我能做主,可是夫子自道的這部分,委實令我難煞。難在哪裡呢?
傳出去,木心講自己的書,老王賣瓜,自賞自誇。所以要講清楚——傳出去,也要傳清楚。
是的,他自己當場「講清楚」了,二十多年後,我該怎麼「傳」法?怎樣地才算「傳清楚」?
*
二〇〇六年初,木心作品的大陸版面世了,零零星星的美譽、好意、熱心語,夾著各種酸話、冷話、風涼話,陸陸續續傳過來。我久在泥沼,受之無妨,但那幾年老人尚在世,他開罪了誰嗎?二〇一一年冬,木心死。二〇一二年秋,《文學回憶錄》全部錄入,重讀他以上這些話,我心想:這汙濁的空間,「傳」得「清楚」嗎?而當年的木心居然相信「傳清楚」了,便是善道,便得太平。
老頭子還是太天真。紐約聽的課,北京出的書,世道一變,語境大異,我得「學壞」才行。誠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一橫心,將這部分文字全部剔除了。
然而新的麻煩,須得收拾:全書九十多課抽去兩萬多字,便有九堂課的內容驟然減半(其中,兩堂課全時講述木心的作品)。為了版面的齊整均衡,我還得煞費苦心,將九堂課上半節談論的內容(沙特呀、卡繆呀、新小說派呀)挪移、銜接、拼合,既經壓縮,課目的數序也隨之篡改而減少。諸位明鑒:《文學回憶錄》下冊(繁體版:「二十世紀之卷」,印刻,二〇一三),便是這樣地被我挖去一塊,哪位讀者的法眼,看出來麼?
此即木心留下的麻煩,也是我自找的麻煩——以上交代,亦屬小小的麻煩。
我從木心學到什麼?其一,是他念茲在茲的「耐心」,雖則跟他比,我還是性急。當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談論自己;如今,我靜觀三載這才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頭子知道了,什麼表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機靈,說:「倒也是個辦法。」但這辦法並非「傳清楚」,而是,索性抹掉它、存起來、等著瞧。
我等到什麼、瞧見什麼呢?很簡單:感謝讀者。
迄今我不確知多少人讀過《文學回憶錄》,多少人果真愛讀而受益:這不是我能估測、我該評斷之事。然而風中彷彿自有消息,三年過去了,近時我忽而對自己說:行了。這份私房話的私房話,可以傳出去了。年初編輯第三期木心紀念專號,我摘出聽他講述〈九月初九〉的筆錄,作為開篇,「以饗讀者」,隨即和責編曹凌志君達成共識:過了年,出版這本書。
我的心事放下了。有誰經手過這等個案麼?木心的顧忌、處境,長久影響了我,以至臨事多慮,留一手:這是何苦呢?所幸木心講了他要講的,我傳了我能傳的,此刻想想,還是因為讀者——包括時間。
諸位,我不想誇張《文學回憶錄》的影響。如今的書市與訊息場,一本書、一席話,能改變讀者嗎?難說。而讀者卻能改變作者的。木心的夫子自道,只為一屋子聽課生的再三聒噪;我發布五冊筆錄,乃因追思會上向我懇請的逾百位讀者——雖然,我不是《文學回憶錄》的作者——此刻全文公布這份「補遺」,說來說去,也還是因為顧念讀者。讀者的從無到有、由少而漸多,誰做主呢?時間。我所等候的三年,其實是木心的一輩子,他的遠慮,遠及他的身後。
*
木心終生無聞,暮年始得所謂「泛泛浮名」。一位藝術家,才華的自覺,作品的自覺,說,還是不說,熬住,還是熬不住,這話題,鮮見於通常的文學史,木心卻在講席中反覆言及,雖舉例者俱皆今古名家,但以他自身的際遇,度己及人,深具痛感——眼下這本書,便是此中消息,便是他這個人。
天才而能畢生甘於無聞者,或許有吧;庸才而汲汲於名,則遍地皆是。木心渴望聲譽,但不肯阿世,他的不安與自守,一動一靜,蓋出於此,而生前名、身後名,實在是兩回事。木心自信來世會有驚動,但生前的寂寞,畢竟是一種苦。苦中作樂,是他的老把戲,而作樂之際,他時刻守度。日常與人閒聊,他常坦然自得,眉飛色舞,形諸筆墨之際,則慎之又慎,處處藏著機心、招數,兼以苦衷。一位作家頂有趣而難為的事,恐怕是閃露秘笈、招供自己的寫作,在高明者,更是智性而曠達的遊戲,本身即是創作。
現在回想,如果我們不曾圍攏木心催他開課,年復一年撩撥他,他會有這份機會、場合,慨然自述嗎?我記得那幾堂課中的木心:懇切、平實,比他私下裡更謙抑,然而驚人地坦白——好像在座全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同時,也如他儉省的用筆,點到即止,不使逾度。
木心寫作的快感,也是他長年累月的自處之道,是與自己沒完沒了的對話、論辯、商量、反目,此書所錄,一變為亦莊亦諧、進退裕如的談吐。他的自賞與自嘲好比手心翻轉,他對自己的俯瞰與仲裁,接踵而至。日間校對這九堂課,我仍時時發笑。當他談罷〈S.巴哈的咳嗽曲〉的寫作,這樣說道:
好久不讀這篇。今天讀讀,這小子還可以。
如今「這小子」沒有了。下面的話,好在他當年忍不住:
很委屈的。沒有人來評價注意這一篇。光憑這一篇,短短一篇,就比他們寫得好。五四時候也沒有人這樣寫的。
「他們」,指的誰呢?「五四時候」是也果然沒人這樣寫的:今時好像也沒有。就我所結識者,對木心再是深讀而賞的人,確也從未提及這一篇,而他話鋒一轉:
幸虧那時寫了。現在我是不肯了。何必。
這是真的。我總願木心繼續寫寫那類散文,九〇年代後期,他當真「不肯」了。此是木心的任性而有餘,也是他誠實。一九八五年寫成〈明天不散步了〉,他好開心,馬路上走著,孩子般著急表功:「丹青啊,到目前為止,這是我寫得頂好的一篇散文!」可是八年後課中談起,卻又神色羞慚,涎著臉說道:
不過才氣太華麗,不好意思。現在我來寫,不再這樣招搖了。
當時聽罷,眾人莞爾,此刻再讀,則我憮然有失:老頭子實在沒人可說,而稍起自得,便即自省,因他看待藝術的教養,高於自得。你看他分明當眾講述著,卻會臉色一正,好似針對我們,又如規勸自己,極鄭重地說:
當沒有人理解你時,你自己不要出來講。
什麼叫做「私房話」呢,這就是私房話。全本《文學回憶錄》的真價值,即在「私房」。他談到那麼多古今妙人,倒將自己講了出來,而逐句談論自家的作品,卻是在言說何謂文學、何謂文章、何謂用字與用詞。這可是高難度動作啊,愛書寫的人,哪裡找這等真貨?眼下,隱然而欠雛形的木心研究,似在萌動。此書面世,應是大可尋味的文本,賞鑒木心而有待申說的作者,會留意他所謂「精靈」的自況,所謂「步虛」的自供嗎——承老頭子看得起我們,提前交了底,以世故論,誠哉所言非人:這是文學法庭再嚴厲的拷問也難求得的自白啊。
我知道,以上意思,不該我來說。但我也憋著私房話。那些年常與木心臨窗對坐,聽他笑歎「不懂啊,不懂啊」,我好幾次急了,衝著他叫道:怕什麼啊,你就站出來自己講!
這時,他總會移開視線,啞著喉嚨,喃喃地說:不行的。那怎麼可以。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寫在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