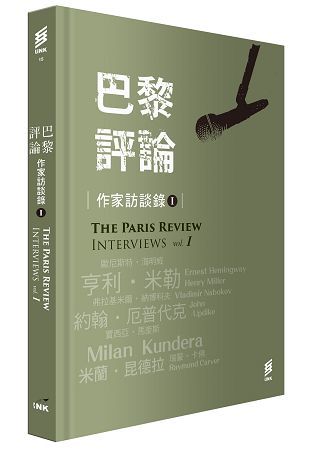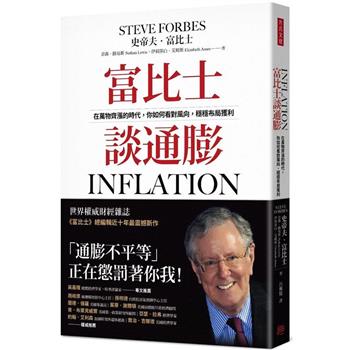附有作家珍貴手稿圖片。
幾乎從我記事起,我就被《巴黎評論》的訪談所深深吸引。把它們匯集在一起,構成了對「文學是怎樣的」這一問題最好的、最現成的探究,從許多方面看,問文學是「怎樣的」比問「為什麼」更有意思。──薩爾曼‧魯西迪
《巴黎評論》的訪談總是從最佳的視角切入大作家的內心和寫作倫理。獨自坐著專心閱讀,就能獲得藝術碩士(MFA)創意寫作課程的訓練。──戴夫‧艾格斯
應該在酒會、朗讀會、婚慶宴會、狂歡派對等各式各樣的熱鬧場合分派《巴黎評論》訪談集。它們也非常適合從高中到藝術碩士課程的各級學校使用,事實上,我曾用這些訪談開設整整一個學期的創意寫作課,別的地方哪裡還能讓我找到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和他們說過的智慧、荒唐、憤怒言論?這些訪談精彩紛呈、令人激動、不可或缺。──科倫‧麥凱恩
海明威:我總是用冰山原則去寫作;冰山露出來讓你看到的部分,是因為有水面下的八分之七。你所瞭解的那些東西儘可刪去,這會加厚你的冰山。
亨利‧米勒:藝術家是什麼?就是那些長著觸角的人,知道如何追逐空氣中宇宙中湧動的電流的人。我們無非只是一種讓空氣裡的某些東西變得有用的媒介。
納博科夫:亨伯特是一個虛榮、殘忍的壞蛋,卻讓自己看上去很「感人」。我自己創作出來的人物,怎麼可能將他「貶低」成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呢?
厄普代克:在寫作的過程中,必須有一種超出意志之外、無法被預定的「幸福感」,它必須歌唱,必須自然順暢。
馬奎斯:寫東西幾乎跟做張桌子一樣難。兩者都是在與現實打交道,素材正如木料一樣堅硬。基本上很少有魔術,倒是包含許多苦工。
瑞蒙‧卡佛:當你把自己的生活寫進小說時,你必須知道你在做什麼,你必須有足夠的膽量、技巧和想像力,並願意把與自己有關的一切都說出來。
米蘭‧昆德拉:第一,徹底去除非必要之物,第二,「小說的對位法」,第三,明確具小說格調的隨筆。
作者簡介:
「作家訪談」是美國文學雜誌《巴黎評論》最持久也最著名的欄目,自1953年創刊號中的E.M.佛斯特訪談至今,從未中斷此當代重要作家的長篇訪談,最初以「小說的藝術」為名,逐漸擴展到「詩歌的藝術」、「評論的藝術」等,迄今已有三百多篇,「作家訪談」成為《巴黎評論》的招牌,也奠定此一特殊文體的典範。
一次訪談從準備到實際進行,往往歷時數月甚至整年,足跡進到作家的書房、工作室、客廳……遍及歐洲、南美、亞洲……全球各地,聽聞作家在熟悉的環境聊著個自的寫作習慣、怪癖、修改方式、困頓時刻、文壇祕辛……真實有趣且極具生活化、現場感,亦為「作者論」的重要文化史料,可謂為「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化對話活動」。
章節試閱
米蘭‧昆德拉
──克利斯蒂安‧薩蒙(Christian Salmon),一九八三年
本次採訪,是一九八三年秋天在巴黎和昆德拉幾次會談的產物。我們在他靠近蒙帕那斯區的頂樓公寓見面,在一間昆德拉當做辦公室的房間裡工作。裡頭的書架上滿是哲學和音樂學的書,有一台老式打字機和一張桌子,看上去更像一間學生宿舍,而不是世界知名作家的書房。其中一面牆上,兩幅照片肩並肩掛著:一張是他父親,鋼琴家;另一張是楊納傑克(Leoš Janáček),他非常喜愛的捷克作曲家。
我們用法語進行了幾次自由而漫長的討論;沒有用磁帶錄音機,而是用了一台打字機,剪刀,還有膠水。漸漸地,去蕪存菁並經數度修改後,這個文本現出其形。
昆德拉的最新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一出版即暢銷,本次採訪就發生在這之後不久。突然而至的名氣讓他很不自在;昆德拉一定同意洛瑞(Malcolm Lowry)的說法,「成功就像一場可怕的災難,比一個人家裡失火還要糟。名聲將靈魂的歸所都吞噬。」一次,當我問及媒體對他小說的某些評價時,他答道:「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
大多數的評論者,傾向於研究作家,還研究作家的個性、政治立場及私人生活,而不是作家的作品。昆德拉不希望談自己,似乎是對這一趨勢的本能反應。「對必須談論自己感到厭煩,使小說天才有別於詩歌天才。」昆德拉對《新觀察家》雜誌如是說。
因此,拒絕談論自己,是將文學的作品與形式放在注意力正中心,聚焦小說本身的一種方式。這次關於創作藝術的討論,正是為此目的。
《巴黎評論》(以下簡稱「評」):你曾說過,在現代文學中,你覺得自己比較接近穆齊爾(Robert Musil)與布洛赫(Hermann Broch)這兩位維也納小說家,更勝於其他任何作家。布洛赫和你一樣,認為心理小說的時代已走到盡頭。相反,他信奉他稱之為的「博學小說」。
米蘭‧昆德拉(以下簡稱「昆」):穆齊爾和布洛赫給小說安上了極大的使命,他們視小說為至高無上的理性綜合,是人類尚可對世界整體表示懷疑的最後一塊寶地。他們深信小說具有巨大的綜合力量,可以是詩歌、幻想、哲學、警句和散文糅合為一個整體。在他的書信當中,布洛赫對此議題有許多頗為深刻的評論。不過在我看來,由於他不當地選擇了「博學小說」這個術語,使得自己的意圖曖昧不明。事實上,布洛赫的同胞斯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一位奧地利散文大家,就寫了本真正博學的小說,即一八五七年出版的《小陽春》(Der Nachsommer)。這部小說很有名:尼采認為它名列四大德國文學作品。時至今日,這書讓人讀不下去,因為裡頭充滿了地質學、生物學、動物學、手工業、繪畫藝術,以及建築學的資料;但這龐大、令人振奮的百科全書,實際上卻漏掉了人類及人類自己的處境。正因為它是如此博學,《小陽春》完全缺乏讓小說變得特殊的東西。布洛赫不是這樣。相反地!他力求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布洛赫喜歡稱之為「小說學問」的具體對象,就是存在。在我看來,「博學」這個詞必須被精確地界定為「使知識的每一種手段和每一種形式匯聚到一起,為了解釋存在。」是的,我確實對這樣的方式有一種親近感。
評:你在《新觀察家》雜誌發表的一篇長文,讓法國人再次發現了布洛赫。你高度稱讚他,可你同時也是語帶批判。在文章結尾,你寫道:「所有偉大的作品(正因為它們是偉大的)都部分地不完整。」
昆:布洛赫對我們有所啟發,不僅因為他已有的成就,還因為那些他打算實現卻無法達到的一切。正是他作品的不完整,助我們了解到需要有新的藝術形式,包括:第一,徹底去除非必要之物(為了掌握現代世界的複雜性又不喪失結構上的清晰);第二,「小說的對位法」(為了將哲學、敘事、理想譜進同一支曲);第三,明確具小說格調的隨筆(換言之,保持其為假想、戲謔或反諷,而不宣稱是要傳達什麼絕對真實的訊息)。
評:這三點似乎表明你的整個藝術規劃。
昆:要將小說變為一個對於存在的博學觀照,必須掌握省略的技巧、濃縮的藝術,不然就掉進了深不見底的陷阱。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是我最愛的少數幾本小說。但別指望我會喜歡它巨大的未完成部分!想想看,有座城堡大到一眼看不盡;想想看,一曲絃樂四重奏長達九個小時。人類有其極限(人的尺度),比如記憶的極限,不應違犯。當你讀完,應仍能記得開頭;如若不然,小說便失去了它的形,它「結構上的清晰」就模糊難辨了。
評:《笑忘書》由七個部分組成。如果你處理它們時用的不是這麼省略的方式,可能會寫成不同的七部完整小說。
昆:可如果寫了七部獨立的小說,我會失去最重要的東西:我將無法在一本單獨的書裡,表現出「現代世界中人類存在的複雜性」。省略的藝術絕對必不可少。它要求一個人總是直接指向事物的核心。在這一點上,我總想起一位我自童年起就極其熱愛的捷克作曲家,楊納傑克。他算得上是現代音樂最傑出的大師,他將音樂剝得只剩下本質的決心,可說是前所未有。當然,每一部音樂作品牽涉到大量的技巧:主題的展露、發展、變化、複調效果(通常很機械),填入配器,過渡,等等。如今,人們可以用電腦作曲,但作曲家的腦中本就有部電腦──如果有必要,他們能夠在毫無原創想法的情況下寫出一部奏鳴曲,只要依著作曲的規則「自動機械化」擴展開來即可。楊納傑克的目的是摧毀這台電腦!野蠻的交錯,而不是過渡;重複,而不是變化──並且總是直接指向事物的核心:只有那些有重要話可說的音符,才有資格存在。小說幾乎也一樣,它也受到了拖累,來自「技巧」,來自作者完成作品的規矩:介紹一個角色,描述一場環境,將行動帶入其歷史背景之中,將角色的一生填滿無用的片段。每換一次景要求一次新的展露、描述、解釋。我的目的和楊納傑克一樣:摒棄小說技巧的無意識、自動化特性,摒棄冗長誇張的小說文字。
評:你提到的第二種藝術形式是「小說的對位法」。
昆:認為小說是一種知識大綜合的想法,幾乎自動產生了「複調」這一難題。這個難題仍要解決。比如布洛赫《夢遊者》(The Sleepwalkers)的第三部,是由五個各異其趣的要素組成:第一,建立在三位主角基礎上的「小說體」敘述──帕斯拿、艾什、于哥諾;第二,漢娜‧溫德林軼事;第三,軍醫院生活的真實描述;第四,一個救世軍女孩的敘述(部分用韻文寫成);第五,有關價值觀墮落的一篇哲學散文(用科學語言寫成)。每一部分都優美。儘管,事實上是以持續不斷的交替(換言之,用一種複調的方式)同步處理,但五種要素依然是分離的──也就是說,它們並不構成一種真正的複調。
評:你用了複調的隱喻並把它運用到文學上,是否事實上向小說提出了它無法完成的要求呢?
昆:小說能夠以兩種方式吸收外界要素。堂吉訶德在他旅行的過程中,遇到不同的人向他敘述他們自己的故事。如此一來,獨立的故事,插入整體之中,與小說框架融為一體。這種寫作在十七、十八世紀小說中常能找到。可布洛赫,沒有把漢娜‧溫德林的故事放入艾什和于哥諾的主線故事中,而是讓它們同時地展開。沙特(在《延緩》﹝The Reprieve﹞中),以及他之前的帕索斯(Dos Passos),也用了這種同時的技巧。不過,他們的目的是將不同的小說故事融合,換句話說,是同質要素,而非像布洛赫那樣的異質要素。此外,他們對這種技巧的使用,給我的印象是太機械且缺乏詩意。我想不到有比「複調」或「對位法」更好的術語,能描述這種形式的寫作,而且,音樂上的類比是有用的。比如,《夢遊者》第三部分首先讓我感到麻煩的是,五個要素並不均等。而所有聲部均等,在音樂的對位法當中是基本的程式規則,是必要條件。在布洛赫的作品中,第一要素(艾什和于哥諾的小說敘述)比其他要素占了更大篇幅,更重要的是,它與小說的前兩部分相關聯,享有一定的特權,因此承擔了統一小說的任務。所以它吸引了更多注意,將其他要素變為純粹的裝飾。第二個讓我感到麻煩的是,儘管巴哈的賦格一個聲部也不能少,漢娜‧溫德林的故事或有關價值觀墮落的散文,卻完全能作為傑出的獨立作品,單獨地看,其意義或品質都分毫未減。
在我看來,小說對位的基要條件是:第一,不同要素的平等;第二,整體的不可分割。記得完成《笑忘書》第三章〈天使們〉的那一天,我極為自豪。我肯定自己找到了一種整合敘事的新方式。文本由下列要素組成:第一,兩個女學生的一段趣事及她們的昇華;第二,一段自傳體敘述;第三,對一本女性主義書籍的批評文章;第四,一則有關天使和魔鬼的寓言;第五,一段關於保羅‧艾呂雅飛過布拉格的夢境敘事。這些要素中沒有一個脫離了其他依然可以存在,每一個都解釋說明了其他,就好像它們都在探索同一個主題,問同一個問題:「天使是什麼?」
第六章,同樣叫〈天使們〉:第一,有關泰咪娜死亡的夢境敘事;第二,有關我父親過世的自傳體敘述;第三,音樂學上的思考;第四,有關在布拉格廣泛流行的健忘症的思考。我父親與泰咪娜被孩子們拷問之間的聯繫是什麼?借用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著名的意象,它是「一架縫紉機和一把雨傘」在同一主題的解剖台上「偶然相遇」。小說的複調更多的是詩意,而不是技巧。我在文學中找不到其他的例子有如此複調的詩意,但雷奈(Alain Resnais)最新的電影讓我大受震驚,他所用的對位技法令人驚歎。
評:《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書中,對位沒有這麼明顯。
昆:那是我的目標。那兒,我想要夢、敘述和思考以一條看不見、完全自然的水流匯聚成河。但小說複調的特點在第六部分很明顯:史達林兒子的故事、神學的思考、亞洲的一起政治事件、弗蘭茲在曼谷的死、湯瑪斯在波西米亞的葬禮,都通過同一個永恆的問題聯繫起來──「媚俗是什麼?」這個複調的段落是支撐整個小說結構的支柱,是解開小說結構之祕密的關鍵。
評:你要求必須有「一篇明確具小說格調的隨筆」,對《夢遊者》中所出現的那篇有關價值觀墮落的散文其實是多有保留。
昆:那是一篇非常漂亮的散文!
評:你對它成為小說一部分的這種方式有過懷疑。布洛赫沒放棄他任何的科學語言,他以一種直白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藏在他的某個角色之後──像曼(Thomas Mann)或穆齊爾會做的那樣。那不正是布洛赫真正的貢獻、他的新挑戰嗎?
昆:確實如此,他對自己的膽識很瞭解。但也有一個風險:他的散文會被看成、被理解成小說意識形態的關鍵,理解成它的「真理」,那會將小說的剩餘部分變成僅在闡述一種思想。那麼小說的平衡會被打亂;散文的真理變得過於沉重,小說微妙的結構便有被摧毀的危險。一部沒有意圖要闡釋一套哲學論題的小說(布洛赫憎恨那一類的小說!)可能最後會被以這樣的方式解讀。如何將一篇散文併入小說裡?重要的是心中要有一條基本原則:一旦被囊括進到小說裡頭,思考的本質就會起變化。小說之外,到處都是肯定性的斷言:每個人都是哲學家、政治家、監護者,都確信自己的言論。可在小說這塊地盤,人們並不堅持己見;這是個屬於扮演與假想的國度。小說中的論點,本質上就是假設性的。
評:但為什麼一個小說家會在他的小說中,想要剝奪自己公然、獨斷表達哲學觀的權利?
昆:因為他根本沒有什麼哲學觀!人們經常會說到契訶夫的哲學,或卡夫卡的,或穆齊爾的;但你倒是找找看,他們的作品中到底有沒有一套連貫的哲學!就算是他們在筆記中表達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容或發展成智力練習,耍弄各種悖論,或即興創作,而不會成為某種哲學的斷言。寫小說的哲學家,不過是用小說的形式來闡明自己觀點的偽小說家。伏爾泰和卡繆都未曾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我只知道一個例外: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這是怎樣的一個奇蹟!越過小說的邊界線,嚴肅的哲學家變成了一個戲謔的思想家。小說中沒一句嚴肅的話──書裡的一切是鬧著玩的。這本書在法國評價過低,到了駭人的地步,正是這個原因。事實上,法國失去並拒絕重新找回的一切,都包括在《宿命論者雅克》裡了。在法國,更注重觀念而不是作品。《宿命論者雅克》無法轉換為觀念的語言,因此無法在觀念的原鄉為人們理解。
評:在《玩笑》中,是雅羅斯拉夫想出一套音樂學的理論,因此,明顯可知他的思考是假設性的。但《笑忘書》中的音樂理論思考是作者的,是你的。那麼我該認為它們是假定的還是肯定的?
昆:這都由語調而定。從最早的文字開始,我就打算讓這些思考帶有一種戲謔、諷刺、挑釁、實驗或懷疑的語調。《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整個第六部(〈偉大的進軍〉)是一篇關於媚俗的散文,闡述一個主要的論題:媚俗就是堅決否定大糞(shit)存在。關於媚俗的此種思考,對我來說至關重要。它建立在大量思想、實踐、研究,甚至激情的基礎上。但語調從不嚴肅;它是挑釁的。這篇散文在小說之外是不可想像的,它是一種純小說的思考。
評:你小說的複調還包含了另一種元素,即夢境敘事。它占了《生活在他方》的整個第二部,它是《笑忘書》第六部的基礎,又通過特瑞莎的夢貫穿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昆:這些離題之處也是最容易被誤解的段落,因為人們試圖從中找到一些象徵性的寓意。特瑞莎的夢沒什麼可破譯的。它們是關於死亡的詩。它們的意義在於它們的美,這美讓特瑞莎著迷。順道一提,你曉不曉得人們不知如何讀卡夫卡,正是因為他們想要破譯他?他們不讓自己順著卡夫卡無與倫比的想像走,反而尋找著寓言,最後只得出一堆陳詞濫調:生命是荒誕的(或生命不是荒誕的),上帝是不可觸及(或可觸及),等等。如果你不懂想像本身就有其價值,根本無法理解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諾瓦利斯(Novalis)讚賞夢時,就知道這一點。「夢讓我們遠離生活的無味」,他說,「用它們遊戲的欣喜,將我們從嚴肅中解放出來。」他第一個認識到,夢以及夢一般的想像可在小說中扮演什麼角色。他計畫將他《海因里希‧馮‧奧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的第二卷寫成這樣的敘述:夢和現實如此纏結,難以區分。不幸的是,第二卷只留下若干筆記,諾瓦利斯在其中描寫了他的美學意圖。一百年後,他的抱負由卡夫卡實現。卡夫卡的小說是一種夢和現實的融合;也就是說,既不是夢也不是現實。最重要的是,卡夫卡引起了一場美學的變革,一種美學的奇觀。當然,沒人能重複他做過的事。但我和他、和諾瓦利斯,都有相同渴望,欲將夢及夢境中的想像帶進小說。我的處理方式是複調的對峙,並非將夢和現實融合。夢境敘事是對位法的要素之一。
米蘭‧昆德拉
──克利斯蒂安‧薩蒙(Christian Salmon),一九八三年
本次採訪,是一九八三年秋天在巴黎和昆德拉幾次會談的產物。我們在他靠近蒙帕那斯區的頂樓公寓見面,在一間昆德拉當做辦公室的房間裡工作。裡頭的書架上滿是哲學和音樂學的書,有一台老式打字機和一張桌子,看上去更像一間學生宿舍,而不是世界知名作家的書房。其中一面牆上,兩幅照片肩並肩掛著:一張是他父親,鋼琴家;另一張是楊納傑克(Leoš Janáček),他非常喜愛的捷克作曲家。
我們用法語進行了幾次自由而漫長的討論;沒有用磁帶錄音機,而是用了一台打字機,...
目錄
歐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歐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
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