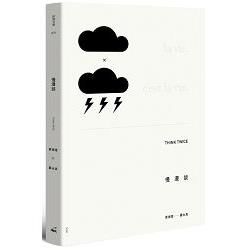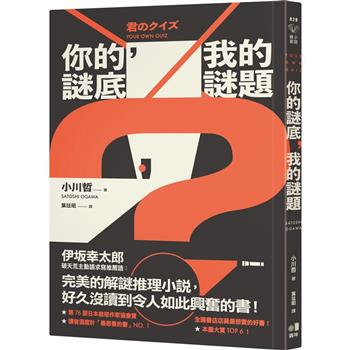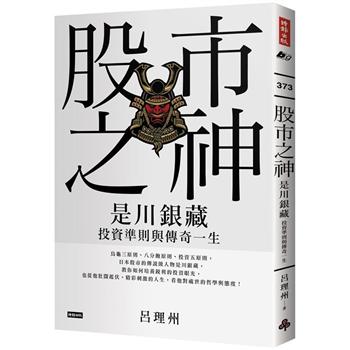黃俊隆與聶永真的真心話大冒險
晃過記憶的轉角,檢視個人與城市的暗巷
厚待彼此,留予一段緩慢的時光
——探索關於街頭、記號、陰影與失去的當代生活課題
晃過記憶的轉角,檢視個人與城市的暗巷
厚待彼此,留予一段緩慢的時光
——探索關於街頭、記號、陰影與失去的當代生活課題
放逐——感覺是捧著一杯茶或咖啡悠悠看著窗外講出來的假掰字。
被萬物綁架——在早已拍/翻版定案的人生待了太久而產生的碎念。
街頭——每個人走出自己待的小世界,聚集交會在一起的地方。
失去——所有失去當下的無法釋懷,都是來自「不甘心」。
過期——每個流行都會因為被過剩的複製而淘汰。
身體——從出生到生命結束,盛載著靈魂的有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