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毀家、原鄉金門的李錫奇,從教師、畫家、策展人、巨匠,到奔走兩岸的和平使者,走過台灣社會與文化藝術發展風風火火的時代,堅持本位,求新求變,以充滿青春激情的探索對待藝術與生命,以他的創作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現代性發展,其親歷性、延續性,為台灣現代藝術史展露具體而微的縮影。
從李錫奇在金門的原生家庭談起,作者娓娓道出時代的烽火如何嚴重影響他的親人與故鄉,及至台北求學,社會氛圍與同儕交流學習的過程,怎樣改變了他的人生路途與畫作表現,接著獲選出國、得獎,開始在國際畫壇嶄露頭角,並增加國際視野,發展他傳統與現代融會的創作思想,作者仔細地將李錫奇的個人藝術史嵌入社會國族世界的大歷史中,讓我們清楚看見時勢的湧動與個人的成長軌跡如何牽連,也縝密分析了李錫奇的藝術創作哲學與精彩特出之處。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色焰的盛宴:李錫奇的藝術和人生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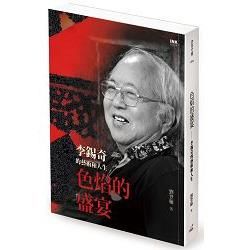 |
色焰的盛宴: 李錫奇的藝術和人生 作者:劉登翰 出版社: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4-2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4 |
美術 |
$ 306 |
藝術設計 |
$ 316 |
中文書 |
$ 317 |
藝術家 |
$ 324 |
藝術家傳記 |
$ 324 |
畫家/畫冊 |
$ 324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色焰的盛宴:李錫奇的藝術和人生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劉登翰
福建廈門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等多種社會職務,已退休。現為廈門大學兩岸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家委員、福建師範大學海峽兩岸文化發展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新詩、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和兩岸文化、閩南文化研究,兼及藝術評論,出版學術專著和文學創作集三十餘種;晚近鍾情書法,視為一種快樂的遊戲,偶有展覽和出版。
劉登翰
福建廈門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福建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等多種社會職務,已退休。現為廈門大學兩岸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家委員、福建師範大學海峽兩岸文化發展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新詩、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和兩岸文化、閩南文化研究,兼及藝術評論,出版學術專著和文學創作集三十餘種;晚近鍾情書法,視為一種快樂的遊戲,偶有展覽和出版。
目錄
序 色焰的燭心──劉登翰的詩學史筆
第一章 自槍管的煙硝裏∕飛撲著一隻折翼的斑爛蝴蝶
第二章 在只有線條的風景裏∕窺視你粗獷的步履
第三章 花開的時候也是這樣吧,像趕赴一場色熖的盛宴
第四章 彼端 朝陽在笑∕且攜手 向恆愛的國度偕行
第五章 那個恣意在紙上繪風繪雨的人∕竟在雲上畫夢
第六章 循看歲月的年輪∕有一片閃閃的曙光亮起
第七章 在祠下的社鼔聲中∕仍昂然地舞著一則九歌
第八章 他以生為金門人為榮∕金門亦將以他為榮
附 錄:
一、傳統本位的現代變奏
──兼論金門歷史文化對李錫奇現代繪畫的影響
二、向時間的歷史深度延伸
──談李錫奇《遠古的記憶》新作
三、藝術創新的《通》與《變》
──記李錫奇新作《記憶的傳說》系列
第一章 自槍管的煙硝裏∕飛撲著一隻折翼的斑爛蝴蝶
第二章 在只有線條的風景裏∕窺視你粗獷的步履
第三章 花開的時候也是這樣吧,像趕赴一場色熖的盛宴
第四章 彼端 朝陽在笑∕且攜手 向恆愛的國度偕行
第五章 那個恣意在紙上繪風繪雨的人∕竟在雲上畫夢
第六章 循看歲月的年輪∕有一片閃閃的曙光亮起
第七章 在祠下的社鼔聲中∕仍昂然地舞著一則九歌
第八章 他以生為金門人為榮∕金門亦將以他為榮
附 錄:
一、傳統本位的現代變奏
──兼論金門歷史文化對李錫奇現代繪畫的影響
二、向時間的歷史深度延伸
──談李錫奇《遠古的記憶》新作
三、藝術創新的《通》與《變》
──記李錫奇新作《記憶的傳說》系列
序
序
色焰的燭心──劉登翰的詩學史筆
蕭瓊瑞
發韌於一九五○年代末期、在一九六○年代中期達於高峰的台灣現代藝術運動,是一場由「現代詩」與「現代繪畫」交響合奏的美麗樂章;作為這場運動最重要參與者之一,且迄今仍保持生猛活力的「畫壇變調鳥」李錫奇,他的傳記,由曾經撰著《台灣文學史》與《彼岸的繆斯──台灣詩歌論》等專書,本身也是詩人、書畫家的劉登翰教授執筆,可說是再恰當不過的人選。
劉登翰教授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因「海外關係」,而分配至閩西北山區二十年,後在福建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並兼任所長;而李錫奇則是福建金門人,福建人來寫福建人,即使曾經分屬不同政權,但改革開放後的兩岸交流,尤其是屬於小三通的金、廈航線,促使這兩位同屬藝術國度的文化人,有著較之一般人更為深切、親密的相知情誼。李錫奇的故事,尤其是金門故鄉的少年記憶與文風民情,在劉登翰的筆下,更讓人有親切、真情的感受。
劉教授對李錫奇作品的詮釋,早有〈向時間的歷史深度延伸──序李錫奇九一系列《遠古的記憶》〉(一九九一)、〈藝術創新的「通」與「變」──序李錫奇九二新作《記憶的傳說》〉(一九九二),及〈傳統本位的現代變奏──兼論金門的歷史文化對李錫奇現代繪畫創作的影響〉(二○○一)等鴻文,今再以他閩台文化研究專家的背景,加上史詩般的筆法,將李錫奇這樣一位生長在戰火洗練下的藝術家,剖析、條理出藝術生命成型的內外理路及因緣,是一部兼具個人傳記與時代歷史的傑出偉構。
在劉教授條理出的每一篇章之前,都有詩人古月的一首小詩:「自槍管的煙硝裏/飛撲著一隻折翼的斑斕蝴蝶」(第一章)、「在只有線條的風景裏/窺視你粗獷的步履」(第二章)、「花開的時候也是這樣吧/像趕赴一場色焰的盛宴」(第三章)……。古月正是畫家的妻子,李錫奇和古月的結褵,也正是一九六○年代台灣詩畫結合最圓滿的一顆果實。畫家八十年的生命,有詩人的陪伴,益顯粗獷中的美麗與細緻。
「他的傳記是歷史的一部分」,是羅曼羅蘭對貝多芬的至高讚美,同樣的讚美似乎也可以用來讚美李錫奇,他的生命,已然成為台灣現代藝術發展重要的一部分,劉登翰教授的大作正為我們揭示了這個事實,也為這個時代作了忠實的見證。
色焰的燭心──劉登翰的詩學史筆
蕭瓊瑞
發韌於一九五○年代末期、在一九六○年代中期達於高峰的台灣現代藝術運動,是一場由「現代詩」與「現代繪畫」交響合奏的美麗樂章;作為這場運動最重要參與者之一,且迄今仍保持生猛活力的「畫壇變調鳥」李錫奇,他的傳記,由曾經撰著《台灣文學史》與《彼岸的繆斯──台灣詩歌論》等專書,本身也是詩人、書畫家的劉登翰教授執筆,可說是再恰當不過的人選。
劉登翰教授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因「海外關係」,而分配至閩西北山區二十年,後在福建社會科學研究院文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並兼任所長;而李錫奇則是福建金門人,福建人來寫福建人,即使曾經分屬不同政權,但改革開放後的兩岸交流,尤其是屬於小三通的金、廈航線,促使這兩位同屬藝術國度的文化人,有著較之一般人更為深切、親密的相知情誼。李錫奇的故事,尤其是金門故鄉的少年記憶與文風民情,在劉登翰的筆下,更讓人有親切、真情的感受。
劉教授對李錫奇作品的詮釋,早有〈向時間的歷史深度延伸──序李錫奇九一系列《遠古的記憶》〉(一九九一)、〈藝術創新的「通」與「變」──序李錫奇九二新作《記憶的傳說》〉(一九九二),及〈傳統本位的現代變奏──兼論金門的歷史文化對李錫奇現代繪畫創作的影響〉(二○○一)等鴻文,今再以他閩台文化研究專家的背景,加上史詩般的筆法,將李錫奇這樣一位生長在戰火洗練下的藝術家,剖析、條理出藝術生命成型的內外理路及因緣,是一部兼具個人傳記與時代歷史的傑出偉構。
在劉教授條理出的每一篇章之前,都有詩人古月的一首小詩:「自槍管的煙硝裏/飛撲著一隻折翼的斑斕蝴蝶」(第一章)、「在只有線條的風景裏/窺視你粗獷的步履」(第二章)、「花開的時候也是這樣吧/像趕赴一場色焰的盛宴」(第三章)……。古月正是畫家的妻子,李錫奇和古月的結褵,也正是一九六○年代台灣詩畫結合最圓滿的一顆果實。畫家八十年的生命,有詩人的陪伴,益顯粗獷中的美麗與細緻。
「他的傳記是歷史的一部分」,是羅曼羅蘭對貝多芬的至高讚美,同樣的讚美似乎也可以用來讚美李錫奇,他的生命,已然成為台灣現代藝術發展重要的一部分,劉登翰教授的大作正為我們揭示了這個事實,也為這個時代作了忠實的見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