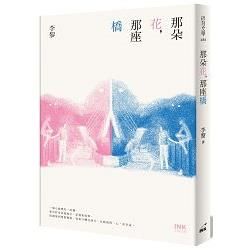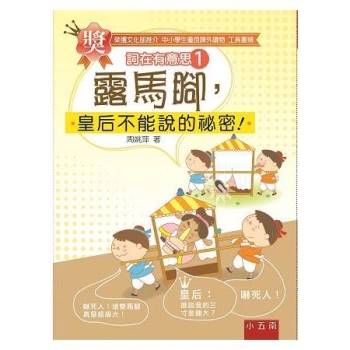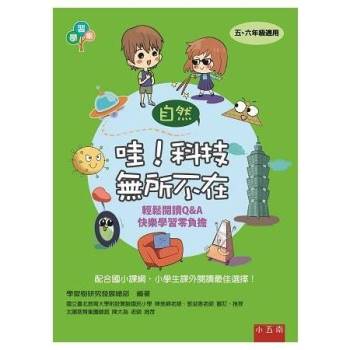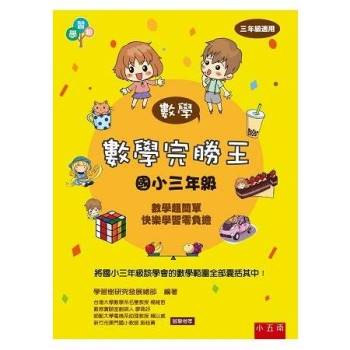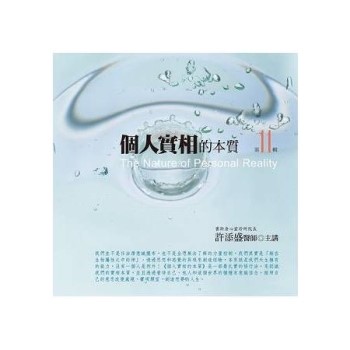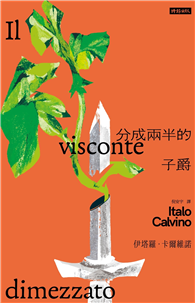平山郁夫與大唐西域壁畫
收藏在奈良藥師寺玄奘三藏院裡,日本畫家平山郁夫的「大唐西域壁畫」系列,每一幅畫右下角的題款日期都是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年畫家正是七十高齡,歷時三十載、前後數十趟追隨玄奘法師腳步的西域之行,積累了幾百本寫生簿;畫家終於完成了這系列壁畫,獻給新的千禧年,也為他漫長的絲路行旅寫下完美的最後一筆。
壁畫系列一共有十三幅,整座專為這些畫而設的「畫殿」,展示的也就只有這十三幅永久收藏作品。如從正門進入,次序是右手邊開始第一幅,然後右壁兩幅,正中七幅,左壁兩幅,左手邊最後一幅。可是正門平時並不開啟,一般參觀者都是從右側門進,按順序看完後從左側門出。
壁畫分成七個主題,順序是跟隨玄奘西行的路線。第一幅是大唐長安城, 現今猶聳立在西安城裡的大雁塔沐浴在金色的日光之中——公元六二九年一個晴朗的秋天,年輕的唐僧從這裡出發,開始了他漫長的取經之旅。接著兩幅是嘉峪關,大唐國土的邊陲,駱駝商旅隊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中竟顯得如此渺小。從此之後三藏法師便踏上了荒漠異域,而他矢志「不東」——取經不成絕不東歸的決心也自此開始。
第四和第五幅畫的是高昌故城遺址。嘉裕關外一千里處,今日新疆吐魯番附近,就是當年繁華昌盛的高昌國都,而今還存在著壯觀的廢墟。玄奘法師在高昌受到優渥的接待,之後就要走上最艱苦的險途:翻越天山山脈、帕米爾高原、喜馬拉雅山。畫家在親身攀登喜馬拉雅山作素描時,決定將這些群山畫成象徵西方淨土的「須彌山」:三幅氣派恢弘的大山,峰頂皚皚的白雪襯著寂淨的碧空,靜穆而莊嚴的聳立在畫殿主壁的正中央。
之後兩幅是阿富汗,主題是「巴米揚石室」,畫裡的巴米揚大佛依然完整而壯麗,正是當年玄奘見到時的模樣;也是畫家在一九六○年代,旅行到尚未被戰火洗劫的阿富汗時所見。巖洞山壁前的大地上,畫家添上了生機盎然的綠地 - 這是過去,也是未來,是畫家對文明破壞之後和平再生的希望。
終於,到達印度了。兩幅印度德干高原,土褐色的風景,荒涼的大地,卻是孕育了古老的哲學、宗教與藝術的地方。最後一幅,是玄奘法師萬里行旅的目的地、藏有數百萬卷經典的佛法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在那幅題名為「那爛陀的月光」畫幅裡,月光下,遺址前的路徑上,仔細看會發現一個小小的、模糊的白衣身形。畫家說:那,就是玄奘,也是畫家自身,以及所有尋求救贖的人的身影。
這些畫乍看是寫實的,再看卻有一種超越寫實的空靈意境。更由於畫面的巨大,人站在畫前會覺得似乎可以走進那烈日黃沙或月光廢墟裡去。之前我在網上看過他的作品,也看了日本NHK電視台拍攝的紀錄片《平山郁夫三藏祈願之旅》,追蹤細述他作畫的過程;但親眼直觀色彩筆觸,親身體會四壁十三幅畫的壯觀,現場的經驗還是無可取代的。
看完一遍,捨不得離去又回頭再看,想到這樣的大畫對六七十歲的畫家是體力的挑戰;尤其動人的是:除了以誠謹和慈悲心作畫,平山郁夫還致力於保護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亞和東亞的文化遺產的工作。早在七○年代,他就捐贈了兩億日圓,成立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
親身經歷了廣島原爆的無情毀滅,畫家卻以他倖存的餘生,尋得了有情的重建之路,並且決心與玄奘法師一樣,走上他的祈願之旅——畫家用他的畫筆,為這多難的世間重建美,以及希望。
倖存者的救贖
一個日本中學生,十五歲那年的夏天,世上第一顆原子彈在他居住的城市裡爆炸。他親眼目睹了火海中人間地獄的慘狀。奇蹟似的,這個少年竟然活了下來,旋即離開了滿目瘡痍幾成廢墟的廣島,進了東京美術學校學習繪畫。後來他成了一位著名的畫家。
他的名字是平山郁夫。去年年底他以七十九之齡逝世,不算特別長壽,但作為一個原爆倖存者,他覺得十五歲之後的人生都是額外的。如何活這額外的人生呢?他選擇了藝術,而且是和平與慈悲的藝術。作為一個倖存者,他在藝術和佛學中尋得了精神的安慰,苦難的昇華,和心靈的救贖。
一切開始在四十年前,他二十九歲那年。原爆後遺症核輻射致使他患上白血球過少的病,那年減少到常人一半以下,他以為時日無多,希望在死亡來臨之前畫出一幅真正動人的好畫。忽然之間,中國唐代玄奘法師的行跡出現在他腦海,那份為追求真理和眾生救贖的不屈不撓的意志給了他啟示,於是畫出「佛教傳來」——兩名僧侶,騎在一白一黑兩匹馬上,遙指前方,美麗的林間有白鳥飛翔,畫中充滿聖潔的詩意。這幅畫讓他成了大名,更是他從此與玄奘結下不解緣的開始。
玄奘法師求道取經的事跡感動了畫家,此後大半生的歲月裡,平山郁夫僕僕風塵於絲路上,追隨那位偉大的先行者的足跡;從中國的西安,敦煌,新疆,翻過帕米爾高原,到中亞,然後印度⋯⋯不辭辛苦的走了幾十趟,畫下不計其數的寫生素描,回到家中畫室重新再畫,最後成就的大作品是十三幅「大唐西域壁畫」,永久收藏在奈良藥師寺,玄奘三藏院的畫殿裡。
這一系列獻給新世紀的壁畫完成於二○○○年底,十年來展出的時間有限,對於難得去一趟京都的旅人湊巧遇上是要憑機緣的。卻是由於今年奈良在慶祝「平城遷都一三○○年」,壁畫全年每天開放,而我今秋正好有機會去京都,有幸得以到奈良親眼看到了。
奈良藥師寺是唐代寺院建築風格,而兩層塔形的玄奘三藏院的匾額上,藍底金字,竟是「不東」兩字——正是,當年法師矢志往西土取經,誓言使命不成絕不東歸。仰望這簡單的兩個字,方有幾分明白畫家所說:年輕時在備受原爆記憶和後遺症折磨的時日裡,玄奘法師的事跡給了他啟發——為了求取解除戰亂中人們悲苦的救贖之道,年輕的法師歷經千辛萬苦, 以十幾年的歲月行走在異域旅途,九死一生,並以餘生之年翻譯帶回的經卷。畫家的腦海浮現一千多年前這個身影,決心追隨,從此走上一條溫柔慈悲的求道之路——絲綢之路。
在交通發達的今日循著玄奘的足跡西行,當然不再有當年的艱險;然而大自然的滄桑和人為的破壞,也為這條漫漫長路改變了面貌。當年唐僧目睹的繁華國度,而今多處不是被層層黃沙深深掩埋,就是只剩黃土上的廢墟遺址。像新疆的高昌故國,一大片壯觀的斷壁殘垣,其中竟還有佛寺的遺跡。又如阿富汗的巴米揚大佛像,玄奘法師與平山畫家都曾親眼目睹過——雖然畫家三十多年前看到的大佛面部已被削去了一半;而今大佛更是被塔立班的砲火炸燬,僅剩空空的洞穴了。
這些,畫家都親眼目睹了,也都提筆畫下了。他不僅畫出絲路當下的美,也畫出想像中原貌的美;他畫美的流逝與綿延,因為世事皆無常,也因為人們依然在為彼此製造戰亂、破壞與傷害。他畫出了完整的巴米揚大佛像,並且在那片飽受戰火蹂躪的荒瘠土地上畫了一片綠地——對這個殘酷的世界,他依然抱著希望。
二○一○年
在奈良抄寫心經
一個秋日,在奈良藥師寺欣賞完平山郁夫的「大唐西域壁畫」出來,同行的日本女友惠子看見畫殿近旁有一間寫經道場:捐獻日幣兩千圓,可以抄寫一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惠子雖是基督徒卻極力慫恿我去寫經,甚至自願擔任書僮替我磨墨。
廳裡燃著香,靜坐抄經的人還不少呢。取了紙筆墨硯和臨摹用的經文,上面是整齊端麗的漢字,我收斂心神開始動筆。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法師翻譯的無比優美的經句,在我恭謹的一筆一劃下逐字緩緩出現了。書寫中的心情漸趨寧靜愉悅;旅途的奔波勞頓和一整天尋訪名刹古寺的興奮焦灼,在寫下這些字句時皆如水流逝,如冰消融。
在佛寺裡抄經,這是我前所未有過的經驗;而這第一次,竟然不是在中國,不是在西域,不是在印度,而是在奈良。
這次在奈良,格外感受到唐代中華的藝術人文宗教,流傳至今影響依然鮮明。更奇妙的是竟把遙遠的絲路和眼前的京都連在一起了——從前去絲路,無論是陝甘的河西走廊或者新疆的天山南北,感受到的都是面朝西方的交流展望,也是西方東來的交匯與終點站;而每次到京都,則是沈浸在日本精緻優雅的禪意美學裡,從來未曾對這兩處截然不同的地方有過聯想。然而色彩繽紛的廣漠西域,與纖細溫婉的京都奈良,在這安靜的寫經堂裡,在我書寫玄奘法師翻譯的心經時,兩種意象竟如裊裊的爐香,悠然結合在一道了。
奈良不僅有紀念玄奘法師和保存展示「大唐西域壁畫」的藥師寺玄奘三藏院,附近還有來自中國的鑑真法師建立的唐招提寺——這位唐代高僧應日本留學僧的邀請東渡傳法,經過五次失敗,到後來連眼睛都瞎了,還是矢志東行,最後抵達奈良都城時已經六十七歲了。鑑真法師不但為日本帶來佛學經綸典籍,隨行弟子中還有精通技藝的,也將佛教工藝美術一併傳來了。
唐招提寺的「講堂」部份是鑑真法師在世時建造的,在那裡我注意到彌勒如來坐像右側有一尊小小的「增長天立像」,豐滿生動,比起其他塑像更給人一種活潑愉悅的感覺;細看解說,竟然就是隨鑑真和尚東來的唐朝佛工的作品。而寺裡那尊右手臂已斷落的藥師如來佛的立像,是被公認具有西域壁畫的特徵,這在當時的日本佛像是看不到的,因而也有猜測是出自隨行的來自西土的「胡僧」之作。
記得在敦煌莫高窟裡,面對那些精美瑰麗的壁畫,我目眩神迷之際的感動簡直要用「震撼」來形容。到了奈良的法隆寺——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築,我驚訝的發現寺裡的伽藍壁畫,那唐代風格跟敦煌莫高窟裡的竟然如此相像!我甚至聯想到上次去絲路,在新疆和田——玄奘時代稱為于闐的古絲路南北道樞紐,看到荒漠中被流沙掩埋了千餘年,二○○三年才被偶然發現的世上最小的佛寺,四壁上那殘缺但依然精美的唐風壁畫,也是一脈相承的。啜飲奈良的一掬清泉,卻發現源頭遠在千里之外。
橫亙在中華大地上,有兩道至今猶存的歷史遺跡:萬里長城和絲綢之路。那高聳的石砌長城的意象是防禦、阻擋、排斥和抗拒;而絲路卻是善意友好的延伸、探索、交流與接納。一千多年來,這條漫長而柔美的絲路,跨越時空,超越了無數人為的障礙與破壞,不僅朝西綿延,也往東舒展。
千餘年後的我,一個渺小的旅人,在絲路的這一端,只能以虔敬的心書寫經文一葉,獻給那些走出這條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道路的行者們。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那朵花,那座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9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38 |
小說/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現代散文 |
$ 252 |
現代散文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那朵花,那座橋
一個小城裡的一座橋,牽出許多其他地方、記憶和故事,
從建築到電影藝術,從東方轉往西方,在敘說時,心,安在這。
世事變幻無常,亦有不變的事物。
同樣的路線,同樣的地名,看起來似乎有不變的東西,然而,物非全是,而人已全非。變化無常才是永恆的常態。
來了,看見了,記住了,沒有留下什麼也不用帶走什麼。
〈花與橋〉裡,訴說到奈良抄寫心經的感觸,小津安二郎電影幕後。實際走訪莒哈絲筆下的情人的家,了解水與火並存的越南。而〈魔毯與萬花筒〉,一窺文明起源,震懾於其藝術的鬼斧神工。科技當前,〈袋鼠與朱鹮〉描述從舊金山和聖荷西之崛起的矽谷,成就了多少傳奇!〈詩與光影〉回顧書中故事,尋找快樂、追憶人生,……不論旅遊、藝術或電影等影像紀錄,還是科技、虛擬社交新世界,透過作者的雙眼與筆力,處處蘊藏驚奇,篇篇生動有情。
作者簡介:
李黎
本名鮑利黎,高雄女中、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出國赴美就讀普度(Purdue)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曾任編輯與教職,現居美國加州從事文學創作。曾獲《聯合報》短、中篇小說獎。著有小說《最後夜車》、《天堂鳥花》、《傾城》、《浮世》、《袋鼠男人》、《浮世書簡》、《樂園不下雨》等;散文《別後》、《天地一遊人》、《世界的回聲》、《晴天筆記》、《尋找紅氣球》、《玫瑰蕾的名字》、《海枯石》、《威尼斯畫記》、《浮花飛絮張愛玲》、《悲懷書簡》、《加利福尼亞旅店》、《昨日之河》、《半生書緣》等;譯作有《美麗新世界》。
TOP
章節試閱
平山郁夫與大唐西域壁畫
收藏在奈良藥師寺玄奘三藏院裡,日本畫家平山郁夫的「大唐西域壁畫」系列,每一幅畫右下角的題款日期都是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年畫家正是七十高齡,歷時三十載、前後數十趟追隨玄奘法師腳步的西域之行,積累了幾百本寫生簿;畫家終於完成了這系列壁畫,獻給新的千禧年,也為他漫長的絲路行旅寫下完美的最後一筆。
壁畫系列一共有十三幅,整座專為這些畫而設的「畫殿」,展示的也就只有這十三幅永久收藏作品。如從正門進入,次序是右手邊開始第一幅,然後右壁兩幅,正中七幅,左壁兩幅,左手邊最後...
收藏在奈良藥師寺玄奘三藏院裡,日本畫家平山郁夫的「大唐西域壁畫」系列,每一幅畫右下角的題款日期都是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年畫家正是七十高齡,歷時三十載、前後數十趟追隨玄奘法師腳步的西域之行,積累了幾百本寫生簿;畫家終於完成了這系列壁畫,獻給新的千禧年,也為他漫長的絲路行旅寫下完美的最後一筆。
壁畫系列一共有十三幅,整座專為這些畫而設的「畫殿」,展示的也就只有這十三幅永久收藏作品。如從正門進入,次序是右手邊開始第一幅,然後右壁兩幅,正中七幅,左壁兩幅,左手邊最後...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從這朵花、這座橋開始……
花,是始終不知名的花;橋,是特地陪兒子去走一趟的橋。但這本書並不僅只是花與橋的故事。
一個小城裡的一座橋,牽出許許多多其他的地方和文字。從那座日本的橋,到日本的懷舊老電影、黑澤明和小津、小津的故居墓園;到奈良的大唐絲路壁畫,跟隨玄奘的絲路走啊走一路走到了滿天神佛色彩繽紛的印度,鬼斧神工的山崖洞窟裡,竟有依稀似希臘風的天女壁畫,隨著她一路飛到天方夜譚的北非沙漠、飛到歐洲,倫敦的書店巴黎的河;塞納河上的密哈波橋有詩也有小說,那個在越南出生長大的莒哈絲,可曾在橋上看著流...
花,是始終不知名的花;橋,是特地陪兒子去走一趟的橋。但這本書並不僅只是花與橋的故事。
一個小城裡的一座橋,牽出許許多多其他的地方和文字。從那座日本的橋,到日本的懷舊老電影、黑澤明和小津、小津的故居墓園;到奈良的大唐絲路壁畫,跟隨玄奘的絲路走啊走一路走到了滿天神佛色彩繽紛的印度,鬼斧神工的山崖洞窟裡,竟有依稀似希臘風的天女壁畫,隨著她一路飛到天方夜譚的北非沙漠、飛到歐洲,倫敦的書店巴黎的河;塞納河上的密哈波橋有詩也有小說,那個在越南出生長大的莒哈絲,可曾在橋上看著流...
»看全部
TOP
目錄
(自序)
從這朵花、這座橋開始……
第一部 花與橋:現在和過去
青山綠水,幾度興亡
平山郁夫與大唐西域壁畫
在奈良抄寫心經
無字小津
兩個東京故事
紅色的富士山
那朵花,那座橋
情人的家
早安越南
第二部 袋鼠與朱鹮:真實和虛擬
兩個城市兩首歌
虛擬社交與非死不可
眾人尋他千百度
袋鼠物語
假如男人是袋鼠
朱鹮送子的故事
巴別塔下的笑話
盈盈的婚禮
回首未來
第三部 魔毯與萬花筒:在地圖之外
新版心願地圖
天方夜譚摩洛哥
軌道上的風景
更高,或是更遠
海上的慈悲女神
丁丁和七寶鎮
洞...
從這朵花、這座橋開始……
第一部 花與橋:現在和過去
青山綠水,幾度興亡
平山郁夫與大唐西域壁畫
在奈良抄寫心經
無字小津
兩個東京故事
紅色的富士山
那朵花,那座橋
情人的家
早安越南
第二部 袋鼠與朱鹮:真實和虛擬
兩個城市兩首歌
虛擬社交與非死不可
眾人尋他千百度
袋鼠物語
假如男人是袋鼠
朱鹮送子的故事
巴別塔下的笑話
盈盈的婚禮
回首未來
第三部 魔毯與萬花筒:在地圖之外
新版心願地圖
天方夜譚摩洛哥
軌道上的風景
更高,或是更遠
海上的慈悲女神
丁丁和七寶鎮
洞...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黎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5-13 ISBN/ISSN:978986387096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開數:14.8*21 1.7 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