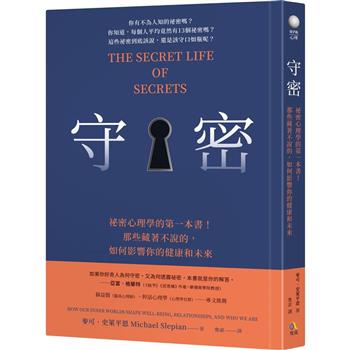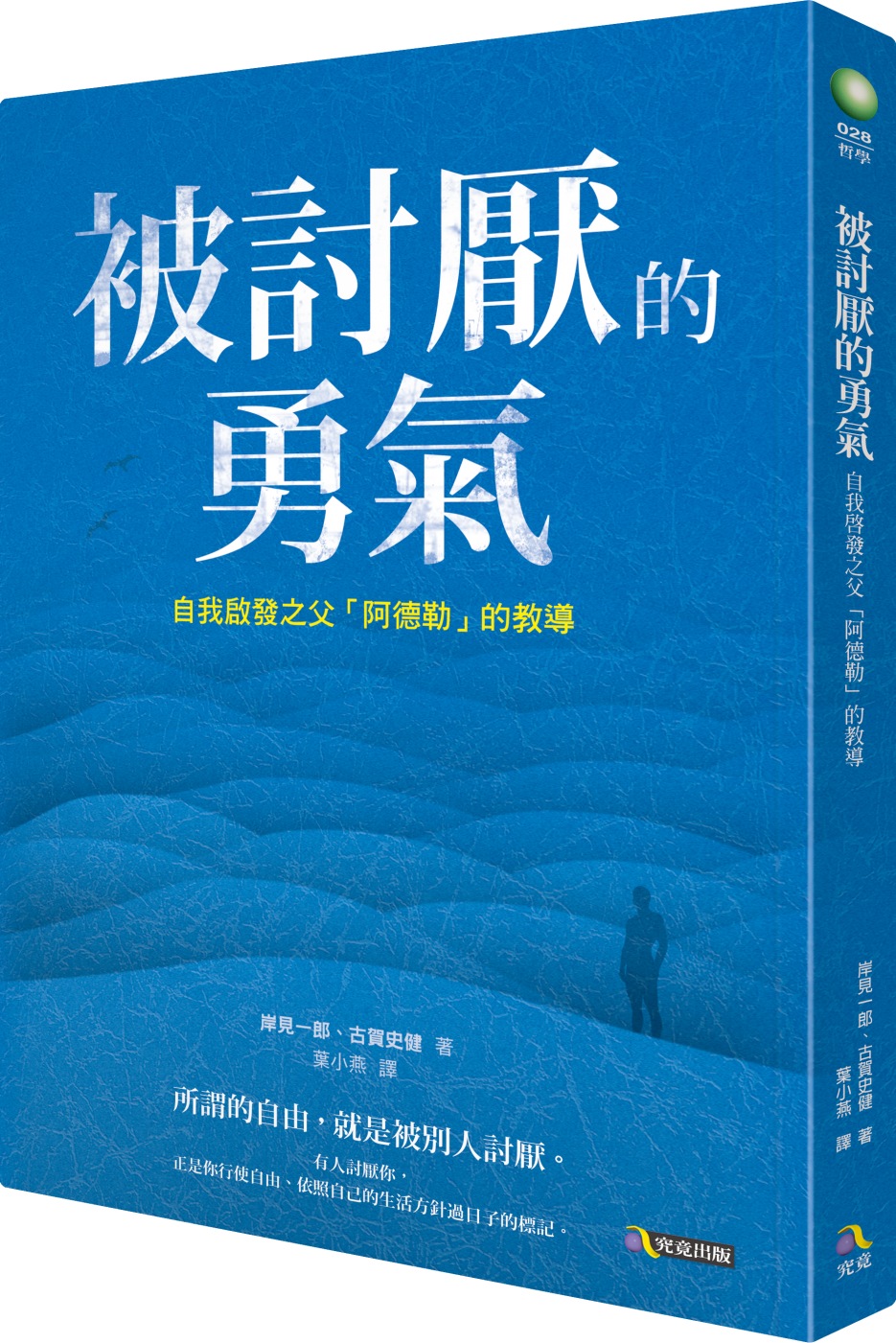從大時代歷史,至個人生命中任何一件可能不會被在乎的事物,都有其詩意的蘊藏,詩人以自身為界,寫下的字句不僅僅是個人的獨特生命展演,也關乎人於現實的超脫以及對真實的追索。而那些流進生命深處的詩句,總是會在面對狂喜狂悲,或是不予人言的痛心苦楚時,讓人們有更寬廣的詩意想像和可能性,甚至是找到超乎原本想像的出路。
楊照從周夢蝶、洛夫、商禽、瘂弦、楊牧五位詩人開始,從詩人歷處的時代背景和各別流離的生命景觀,切入談論台灣現代詩在五○到六○年代的這「黃金十年」,這五位極具代表性的詩人,也就在這十年期間進入詩生命的巔峰。從孤獨國主周夢蝶、洛夫最艱澀難懂的經典之作、超現實主義商禽、最美好的歌者瘂弦、楊牧的抒情詩傳統,他們各自憑著自身的詩藝,在台灣現代詩領域裡走出豐富精彩的路途,也替當時台灣現代詩留下極為精純的質地。
而五位風格殊異的詩人,從人而詩再進一步含括整個年代,在楊照的析解中,凸顯他們在台灣詩壇的特殊與代表性。楊照引領著讀者一遍遍重讀幾位經典詩人,穿透層層肌理解讀,讓讀者在原本的認知和感受之外,又再次發現可能存在著更多的未被辨認出來的意蘊,或是遺漏在歷史或時代中的詩意甚至是幽微的悲傷,還有詩句之外,隱於字句間的伏流,那些被詩人斷開、藏白的不說。在楊照的梳理之下,詩人身影如同一道道穩固的定錨,在詩隨著時代與人心際遇的流動中,標示著不使人迷途的航標。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一九六三年生,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主持Bravo91.3「閱讀音樂」及九八新聞台「楊照音樂廳」廣播節目。長期於「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開設人文經典選讀課程。著作等身,橫跨小說、散文、評論、經典導讀等領域。近期出版有《打造新世界:費城會議與美國憲法》、《別讓孩子繼續錯過生命這堂課:台灣教育缺與盲》、《誰說青春留不住》、《我想遇見妳的人生:給女兒愛的書寫》、《遊樂之心:打開耳朵聽音樂》、《世界就像一隻小風車:李維史陀與憂鬱的熱帶》、《烈焰:閱讀札記I》、《地熱:閱讀札記II》等書。
章節試閱
孤獨的特權——周夢蝶
現代詩的「黃金年代」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現代詩,成就極高。放入華文文學的範圍中比較討論,乃至於拿來放入龐大的二十世紀西方現代詩傳統,應該都是最能夠發光發亮的表現。到目前為止,包括中國大陸在內,沒有任何一個華人社會,在現代詩的整體成就上,能和台灣平起平坐的,這是我自己當然不免帶有高度偏見,卻絕對誠實的評價信念。
從中文的運用,從運用中文所能表達、承載的訊息多樣性、以及發抒的複雜內在情感,各個不同標準來衡量,台灣的現代詩人都遠遠超越中國大陸、香港、馬華或北美的華人寫作者。我們看不到這些地方有如此密集的詩人與詩作,其平均水準如此之高,而且在時代改變了之後,仍然經得起不同世代讀者的探索與挖掘。
而在台灣現代詩史上,我另外有一個更強烈的偏見,我尤其看中、尤其高度肯定五○、六○年代的台灣現代詩,也就是那批一度在七○年代被批判為抄襲西方、脫離現實、嚴重缺乏本土社會性的作品。
我所受的學術專業,是歷史、史學,以至於使我在閱讀文學時,不可能擺脫一種自然、自主的歷史的態度,也就是不將作品割離、獨立看待,總是要將它們按照時間排比成文學史,將它們放回文學史的脈絡下來閱讀、來評價。從這樣的角度看,我認定台灣現代詩的「黃金年代」,是大約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這十年的時間。這十年,無論在質與量上,台灣現代詩的成就高度,無與倫比,令人驚訝。
蒐集了愈多文學史的資料,就愈感覺到這十年的特殊之處。許多詩人在這十年間,寫出了他們至今不朽的經典作品。最戲劇性的,是瘂弦,他今天傳世的所有詩作,幾乎都集中在這十年間寫完,然後,突然地,他就停止了詩的創作,再也沒有其他的作品了。一九六五年之後,他就幾乎沒有了任何詩作,而且一停筆就停了五十年。但光是那十年的表現,就讓我們今天要談台灣現代詩,無論如何不能漏掉他,不能繞過他輝煌的成績。
其實幾乎同等戲劇性的,是鄭愁予。幾十年過去了,至少讀者和批評者、研究者的反應顯現得很清楚,鄭愁予最好的作品,是他最早出版的《鄭愁予詩集》,一代代讀者熱情擁抱、衷心誦讀,一代代批評者、研究者拿來解讀詮釋的鄭愁予詩作,幾乎都來自於《鄭愁予詩集》。〈錯誤〉、〈情婦〉、〈邊界酒店〉……這些詩,都是鄭愁予二十歲上下就完成的作品。出版了《鄭愁予詩集》之後,也就是過了那段「黃金年代」之後,鄭愁予其實和瘂弦一樣,一度也停止了詩的創作,要等了將近十年,他才又重新提筆,創作了《燕人行》及其後的作品。因為這樣,我們沒有那麼強烈感覺到鄭愁予和那十年之間的緊密關係,以為他一直在寫詩,往往也就誤以為他的詩作是貫串時代、散布在不同年歲間的。鄭愁予是有較長的創作生涯,但無可否認的,他被公認最傑出的詩、最為膾炙人口的詩,其實都落在那十年間。
那十年間,洛夫將所有的詩的創作心力,耗費在〈石室之死亡〉上,寫出了台灣現代詩史上最詭奇的一頁。十年結束,洛夫也就離開了〈石室之死亡〉,轉變風格寫別的詩了。他仍然是個創作不懈的詩人,但他自我轉型,成了另一個和那十年、和〈石室之死亡〉很不一樣的詩人了。
另外,還有一些今天被忽略、被遺忘了的詩人,例如方莘、方思、方旗,這不可思議的「三方」,或黃用,也都活躍在那十年間,十年過後,留下了精彩的篇章,倏然消失。
停歇與繼起
「黃金十年」過去後,瘂弦停筆不寫詩了,事實上,鄭愁予也停筆不寫詩了。洛夫離開了〈石室之死亡〉,改變了原本琢磨出的風格。
還有周夢蝶。周夢蝶的兩本經典詩作──《孤獨國》和《還魂草》,都寫成於這「黃金十年」間。他的第二本詩作,《還魂草》出版於一九六五年。然後,要等三十七年之後,我們才再度看到周夢蝶的下一本詩集。那三十七年中,周夢蝶實質上沒有甚麼新作,他在詩壇的活動,幾乎都是環繞著原來的兩本詩集,新的版本、新的翻譯,或是選集中選進了哪幾首詩。
查看由曾進豐悉心整理的周夢蝶創作年表就能看得出來,一九六五年之後,周夢蝶的詩作,大幅減產。周夢蝶寫過文章表述,一九六○年前後,是他最瘋狂寫詩、也最多產的時候。那個時候,周夢蝶一年可以寫二十首、二十五首詩。以他的個性,以他創作詩的「苦行」方式,那真的是多產了。但過了一九六五年,周夢蝶雖然沒有真正停筆,但詩的產量也就快速跌落到只剩下一年兩首、三首的枯水程度,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多年沒有辦法再出版新的詩集的根本緣故。
「黃金十年」結束後,許多事情都改變了,台灣現代詩也就走入了一個很不一樣的階段。例如,余光中就是在「黃金時代」倏然告終產生的空檔、空白中崛起的。雖然他和洛夫同樣出生於一九二八年,比鄭愁予、瘂弦都還年長,但在詩的創作上,余光中卻是相對晚熟的。「黃金十年」間,當這些人迸發出難以逼視的創造力,寫出主要以「超現實主義」為依歸的新鮮詩作時,余光中在寫《天國的夜市》、《舟子的悲歌》,承襲一九四九年之前大陸的詩風,笨拙的押韻、陳舊的比擬與意象,實在讓人難以肯定稱道。紀弦、覃子豪、洛夫、瘂弦、商禽、鄭愁予……這些人意興風發、叱吒詩壇時,余光中的詩作相對看起來落伍、格格不入。像是「遺物」,搞不清楚人家已經在寫很不一樣的東西,他的美學與技法卻沒跟上,還留在前一個時代徘徊著。從詩的角度看,他像是還活在三○年代的大陸,詩的營造與語彙的運用、詩所要傳遞的意念與情感,都沉陷在三○年代的風格中。
晚熟的余光中要等到一九六五年之後,當「黃金十年」結束,輝煌的詩的集結變得鬆散時,余光中找到了他的天地。去到美國愛荷華,遭遇了美國風起雲湧的青年反抗運動,接觸了Bob Dylan、Joan Baez等人的反戰民歌,余光中徹底重造了自己的詩的聲音與節奏,寫了原創性驚人的《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他又在愛情的感染、召喚下,回頭整理中國古典的意象與韻律,發明了「現代詞」,寫成了獨一無二,讓人無法模仿、難以襲取的《蓮的聯想》。
也是在「黃金十年」乍然散落之時,原來的小老弟,當時叫葉珊,後來改了筆名為楊牧的詩人,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自己的風格、自己獨特的位置。葉珊從十五歲,還在花蓮中學念書時,就開始寫詩、開始發表詩作,進而來到台北,和許多詩人熟識。他是一九四○年出生的,比洛夫整整小一輪,和瘂弦、鄭愁予也有將近十歲的差距,雖然他早熟早慧又出道得早,但在「黃金十年」間,他畢竟太年輕,混在一群都比他年紀大的詩人之間,來不及建立自我,更無法對其他人的創作產生影響。
更重要的,葉珊的出生、成長背景,沒有經歷過戰亂、逃亡、流離失所、惶惶不可終日的痛苦與恐懼,他實在進不了這批詩人的內在詩心,也寫不出他們所擅長的那種「超現實主義」作品來。
不過,葉珊-楊牧擁有驚人的詩的直覺,對於聲音與意象的掌握極具天分,一九六五年之後,「超現實主義」暫時退潮,葉珊-楊牧很快就在原來的潮流之外,成功地另闢蹊徑,創造出一種獨特的抒情美感,不只自成一格,進而開啟了台灣現代詩很不一樣的一個抒情傳統。
寫完了最神祕、也最「超現實」的實驗之作──長篇散文詩《年輪》,原來的葉珊化身成為楊牧,告別了自己前一個階段的詩壇身分(poetic persona),昂然且自信地迎向一個詩的新天新地。
葉珊是「黃金十年」中摸索著的少年,游移於自我抒情的衝動,與其他詩人的超現實曲扭心境之間;楊牧則告別了那樣的游移,明確地走向冶東西方不同抒情表達於一爐的新風格。
為什麼是詩?
用甚麼樣的標準判斷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所出現的詩是好詩,以至於可以將這十年稱為台灣現代詩的「黃金十年」?除了主觀的喜愛、年少時產生的私人情感之外,有其他的理由嗎?
有,我真切地相信有,而且可以明白地說清楚。
一個重要的理由是:這十年間的台灣現代詩作品,對於為什麼寫詩、詩之所以存在的道理,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說明與示範。Why poetry?讀詩的人,寫詩的人,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嗎?對於這個問題有甚麼樣可以說服自己、讓自己安心的答案嗎?
為什麼讀詩?為什麼寫詩?人類的社會與文明中,為什麼會產生詩,而且還長期存留在歷史中,沒有消逝、沒有毀滅?這個世界上,尤其在台灣,大部分的人都不讀詩,生活中從來不需要詩,也都還活得好好的,甚至自認比庸人自擾讀詩、寫詩的人都活得更好嗎?這不就足夠向我們證明詩沒有存在的必要性,更沒有存在的必然性嗎?
當我談詩時,我從來不用「新詩」,而是堅持說「現代詩」,儘管有不少人認為「新詩」和「現代詩」是同一回事。這不是單純語言習慣的問題,我的堅持來自於一份信念:詩的關鍵差異,不在「新」、「舊」──產生的時代比較接近我們的叫「新詩」,時代比較久遠的相對就叫「舊詩」。不,詩不是這樣分類的,真正的差異在「現代」與「傳統」。說「現代詩」,指涉的這種詩之所以產生、之所以有那樣的內容與面貌,是和「現代性」密切相關的。「現代詩」和「傳統詩」不一樣,不是源於一個比較「新」,另一個比較「舊」,而是因為它們面對的人類情感、人類處境很不一樣,中間經過了「現代性」的中介與衝擊。台灣的現代詩,是全世界現代詩巨大潮流中的一個分支。在精神上、在目的上、在表達方式上,台灣現代詩和西方現代詩之間的關聯,遠緊密於和中國傳統詩間的連結。儘管受到了那麼多攻擊、批判,回到作品本身來看,我們還是必須承認、必須尊重當年紀弦所提出來的「現代派的信條」:
1、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的一群。
2、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
這些現代詩人主觀上要寫的,客觀上寫成的,的的確確是和中國傳統詩截然迥異的詩,他們認同的對象,不只是西方,而且不是西方的傳統,是「自波特萊爾以降」的西方現代。
「現代詩」來自「現代人」、「現代主義」與「現代性」。簡化地說,「現代」與「傳統」──不管東西方的哪個「傳統」──最大的差別,就在「個人性」與「獨特性」。
傳統詩有很大一部分屬於工匠式的技藝與訓練,有著清楚明白的規範,要寫傳統詩,就得先習得一套符合規範的本事。中國傳統詩,尤其是近體詩,規範嚴格,近乎嚴苛,講究聲韻、講究平仄、講究對仗,更重要也更根本的,其形式本身,五言、七言,四句、八句,就是一個絕對的、不容動搖的限制。西方傳統詩,也有同樣的限制,音節、音步、步韻,分段詩行的多寡,在在都有規定。一般被譯為「十四行詩」的sonnet,其實「十四行」只是其中最簡單的一個形式規範而已,並不是將詩寫成十四行一首,就完成了sonnet,還要符合分段、步韻、主題變化模式,才能被認可為「商籟體」。
先得掌握了形式規範,並能夠自信自豪地展現對於形式規範的運用,才能寫傳統詩。受限於這種集體的、嚴格的工匠技藝要求,無可避免的,傳統詩能寫的、能表達的就必然有著強烈的集體性。百分之八十的內容,是為了符合那大家都同樣遵守的形式規範而來的,頂多只有百分之二十是詩人個別的風格或感受或思想。
傳統詩的趣味、傳統詩的評價方式,和這套形式規範緊密扣連。像是看胡迪尼的終極魔術一樣,傳統詩的根本欣賞角度,在於理解了規範規律之後,驚訝、佩服地看到詩人如何在被手銬腳鐐綁住時,脫身獲得我們自己無法想像、無法在這限制中找到的自由。就像胡迪尼讓自己被繩索牢牢捆住,外面在加上一圈上了鎖的鐵鍊,進入一個木箱,再將木箱投入大水缸裡,在大家屏息以待的氣氛中,他竟然能在溺斃水中之前,神奇地擺脫所有牽扯,自由浮出水面。我們的掌聲與興奮,源自於他先將自己用這種方式綑綁起來,而不在於他創造出什麼東西。
現代詩不是如此。現代詩排除了傳統詩的種種格律限制,回到一個創作上的自由前提假定上──你愛寫甚麼就寫甚麼、愛怎麼寫就怎麼寫,沒有人綁著你,因而你也不可能藉著掌握並善用形式限制來聲稱成就。這種態度源自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到二十世紀間,西方現代藝術愈來愈突顯了個人性與獨特性。工業化、都市化的發展,將人置入於空前同質性的環境裡。工廠的機器統一流程取代了工匠的個別作業,都市的集體無名生活取代過鄉鎮的親族鄰里互動關係。如此人的個人、自我不斷遭到銷蝕,也就讓人心中、生活裡產生了高度的不安。我是誰?我為什麼是我?我憑甚麼是我?我和周遭的人有甚麼不一樣?我只是眾多工廠工人、眾多都市居民中的一個,和其他人別無區別,可以被單一數字代換的存在嗎?我要接受、我能安於這樣的非個人處境,抹殺自我,融入眾人,單純作為眾人的一份子?
波特萊爾的歷史地位,就在於他用他的詩、用他的生活,在巴黎快速同質化的關鍵時刻,彰顯了一個傲然不馴的態度。他活在巴黎,卻絕對不對巴黎的都市環境讓步、讓渡他的自我獨特性。他拒絕被化約為一個同樣的、沒有可辨識面孔的巴黎居民。他看到的、他書寫的巴黎,始終來自一種不懈地、反抗地努力保存自我獨特性的尖銳眼光。
波特萊爾詩集《惡之華》其中很有名的一首是〈天鵝〉,藉由看到從「巡迴動物園」中逃離出來的一隻天鵝,波特萊爾在詩中建構了層層複雜的懷想、哀嘆時間,表達了他的中心意念:每一個活在都市裡的人,都像這隻天鵝般,懷想著、追尋著自己曾經擁有過的那一片池塘,自在生活的基本環境,然而在都市裡,你永遠找不回那片池塘,只能在一層層堆疊、迴旋的時間中,一直無奈地哀嘆。
波特萊爾詩中傳遞了重要的訊息:正因為活在一個必然矮化、進而取消自我個別性的環境中,我們更不能認輸、放棄。你知道你會輸,但你可以、你必須透過藝術、透過詩,來表現你的抗拒,維持你的個人個別性尊嚴。
「從波特萊爾以降」,詩,現代詩是一個無奈、無望、絕望,卻充滿了超越性追求活力的姿態。
這是我對現代詩來歷的認識,也是對於為什麼會產生和傳統詩截然不同的現代詩的解釋。
孤獨的特權——周夢蝶
現代詩的「黃金年代」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現代詩,成就極高。放入華文文學的範圍中比較討論,乃至於拿來放入龐大的二十世紀西方現代詩傳統,應該都是最能夠發光發亮的表現。到目前為止,包括中國大陸在內,沒有任何一個華人社會,在現代詩的整體成就上,能和台灣平起平坐的,這是我自己當然不免帶有高度偏見,卻絕對誠實的評價信念。
從中文的運用,從運用中文所能表達、承載的訊息多樣性、以及發抒的複雜內在情感,各個不同標準來衡量,台灣的現代詩人都遠遠超越中國大陸、香港、馬華或北美的華人寫作者。我們...
作者序
關於這本書,請容我先抄兩段自己過去寫過的文字來說明:
Grucho Marx的名言:「在我開始講話之前,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說。」本來因為有重要、非說不可的事,所以才開口的,然而一旦開口了、一旦講了,卻變得不是那樣,這是Grucho Marx這句話內涵的意義。
或許是講了就覺得不重要了。因為講出來就發現自己講的話沒什麼了不起的,別人已經都講過千百次了,怎麼還會重要呢?或許是無論怎麼講,都無法精確、恰當地傳達原本在內心念頭裡的那份切急重要性,我們明白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意念多麼重要,但卻怎麼也沒辦法表現出來、傳遞出去。
明瞭這樣的困境,我們會懂得一項弔詭的真理:能把我心裡的感受、肉體的經驗講得最準確、表達得最淋漓盡致的,往往不是我們自己的話、自己的語言。我們需要依賴別人、尤其是依賴詩人,來講我們心中那些在語言之前的重要的事。
你問我:詩和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明明那麼喜歡詩、那麼喜歡講與詩有關的事,卻又強調地否認自己是個詩人?為什麼又不贊成喜歡詩的人都去作詩人呢?這中間不是很矛盾嗎?
不矛盾的。我讀詩、我喜歡詩,因為詩,那些對事物或對語言格外敏感的詩人的作品,替我說出心中最重要的事。我只有透過讀自己無論如何寫不出來的詩,只有透過引用既成的詩句,才能真正明瞭、定型自己的心意。詩人的詩,比我自己的語言,更貼近我。
……讀詩就是在讓自己感動的句子前留下印記,以一種神祕的方式據為己有。你不必成為詩人就可以擁有詩;或者說,正因為不是詩人,你可以擁有更多更多不是自己寫,卻與你如此密切呼應的詩。
這是第一段。還有一段:
應該是米瓦許(Czeslaw Milosz)說過的吧,詩人是語言的煉金師。詩人和煉金師一樣,擁有強大驚人的意志力,不接受別人都自然接受的日常平庸、廉價、而且具備高度獨裁性格的語言系統,他們要靠日常語言的材料,創造出原本不屬於日常生活裡所可以擁有的黃金,某種情緒與意義的黃金。
小說比較接近魔術,詩則必定是煉金。因為小說可以靠著虛構的特權,製造讓人看得眼花撩亂的煙霧迷障,變魔術般地操弄現實,贏得掌聲。小說家欺騙、迷惑的,和魔術師一樣,是他的讀者、觀眾們。小說家和魔術師一樣,自己是清醒冷靜的。但詩人卻要面對自己,要說服自己,或者可以說:欺騙自己。他得要找到自己信其為黃金的東西,沒有可以唬弄的,也沒有意義去唬弄。
硬要把不是黃金的東西轉變為黃金,這是煉金師和詩人,同樣值得敬佩的強大意志力。我們驀然理解:煉金術的沒落,與現代詩的興起,在西方幾乎是一起發生的,這或許不是偶然。我們也驀然理解:存在於西方現代詩內部的那股強韌力量,在東西方傳統詩裡都找不到的,也許就是煉金術的借屍還魂。
不過詩,現代詩,顯然比煉金術幸運且成功。因為詩人們不只留下來夢想與努力的紀錄,還留下了大量的,和黃金一樣質純美好,在太陽底下閃閃發光的詩作。真正在平庸、廉價、無聊的日常語言裡,變造出來的無價之寶。
早在十多年前,這兩段話就寫好了,就存在了,也就預言般地解釋了十多年後為什麼我會寫這本書,這本書又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書名。
二○一四年,配合文學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發表、放映,我和楊澤有了一場談瘂弦和洛夫的對話,接著我到誠品書店說了我對洛夫其人其作的一些看法。二○一五年,又有在「齊東詩舍」的四場講座,我自己規劃的總題是「我所鍾愛的台灣現代詩」。因緣際會,迸發出了我多年來對於台灣現代詩的熱切關心,得到了機會讓我得以再度藉由這些詩來說我自己心底最重要的話。
對我來說,這些從年少時便魅惑我的作品,是詩人從平凡經驗中不可思議煉造出來的黃金,是屬於台灣、屬於這個社會,卻總是默默埋藏著的寶藏。絕大部分的台灣人 不知道也不在意這份寶藏。我知道、而且我在意。因為這些詩的金質中,包含了我的夢想、我的痛苦、我的超越、我的領悟,幾乎是所有在我有限人生經驗中值得被稱為「智慧」的東西。也因為這些詩,是我燃著台灣本位認同立場時,經常覺得最有自信的驕傲。
這是黃金,一個歷史偶然因素意外創造出的黃金時代產物,卻像是被記進了黃金帳戶中,先是變形為一個幾錢幾兩的數字,不再閃閃發光、眩人眼目,然後這數字這帳戶逐漸被遺忘了,成了我們不知道自己原來擁有過的貴重財產。
我試圖要做的,是找出遺落在抽屜深處的存摺,將一些黃金提領出來,從抽象無聊的數字,還原為陽光下閃爍耀眼的現象。提醒大家,這些寶藏原來一直在,而且這些寶藏比真實的黃金還更有價值,因為它們可以無限制地豐厚每個人的人生錢包,只要你願意打開你的感官,讓詩人與詩幫你煉金,擦亮你原本灰樸黯淡的平凡日子。
關於這本書,請容我先抄兩段自己過去寫過的文字來說明:
Grucho Marx的名言:「在我開始講話之前,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說。」本來因為有重要、非說不可的事,所以才開口的,然而一旦開口了、一旦講了,卻變得不是那樣,這是Grucho Marx這句話內涵的意義。
或許是講了就覺得不重要了。因為講出來就發現自己講的話沒什麼了不起的,別人已經都講過千百次了,怎麼還會重要呢?或許是無論怎麼講,都無法精確、恰當地傳達原本在內心念頭裡的那份切急重要性,我們明白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意念多麼重要,但卻怎麼也沒辦法表現出來、傳遞出去。
明瞭這...
目錄
自序
孤獨的特權──周夢蝶
最艱澀詭奇的經典──洛夫
超現實主義風景──商禽
如歌的流離──瘂弦
一個抒情傳統的誕生──楊牧
自序
孤獨的特權──周夢蝶
最艱澀詭奇的經典──洛夫
超現實主義風景──商禽
如歌的流離──瘂弦
一個抒情傳統的誕生──楊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