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書寫親情離别,叩問生死的沉靜之作。
我們面對逝者,有如坐在海灘上守望退潮,沒有必要急急轉身而去。
夾在小說裡的書腰、預定要看的電影、仍然掙扎求生的盆栽、未能實現的旅行……種種和母親共同生活卻未完成的細節,在母親離開之後,銘記著遺憾,卻也依舊吐露著舊日的幸福光輝。
經過多年沉澱,止庵以細膩、溫緩而不流於感傷的筆觸,拈起母親尚在時那些看似微小,實則牽引著深刻懷念的日常點滴。全書分六部分,從母親的離逝開始回溯,《惜別》透過母親的日記、書信,以及作者自身的回憶與夢,交織出人子雋永、綿長的孺慕之思。同時由此反覆叩問,死亡之於往者與生者所彰顯的不同意義。
當至親通過死亡進入了永恆,離別就成為永遠的進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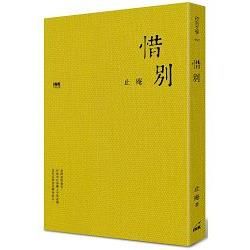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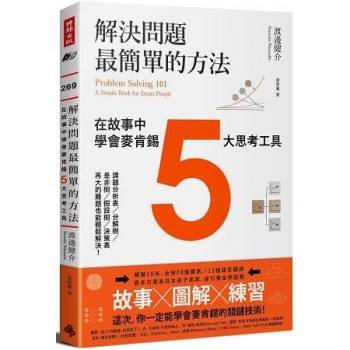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速成+歷年試題](不動產經紀人)](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