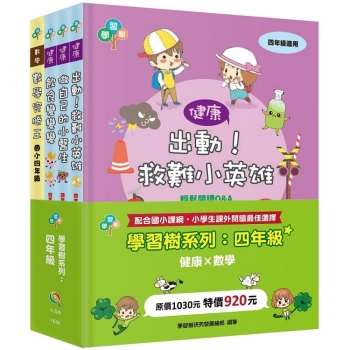她用天地五行,摹寫世間微塵眾生。在河一般浩蕩的歷史之流裡,他們的存在如塵,如沙。時代張揚行過,餘下隱隱震顫的,是他們曾經生存的痕跡。
自2001年以〈水顫〉拿下第六屆花蹤文學獎馬華小說首獎後,如拼圖一般,梁靖芬陸續以土、火、木、金為題拼湊庶民面貌,並且透過小說之筆收攝隱伏在現代生活裡的躁動與不安。《水顫》中的八個短篇各自聚焦不同族群,看似極其普通的日常切片,但卻喧嚷著多元的聲腔和言語,終而匯聚成一幅壯闊又微縮的時代即景。
陳雪、楊澤、駱以軍 齊聲推薦
凝練的文字宜古宜今,筆下的時空無論是追尋先祖的叢林、重逢舊人的舞台前後、或現代夫妻的荒謬家庭劇場,作者的聲腔變化自然,使讀者很快進入她所構造的故事、歷史、或夢境裡。這本小說集展現了「短篇小說」這文類的優異,精準、抒情、節制與冰山底下的的豐富深沉。
──陳 雪
不知道有誰解釋過「後鄉土小說」這詞,我讀梁靖芬小說,常浮現的畫面是:一群活在可輕易辨認的現代時空環境裡的「現代人」,身上還沾有泥巴,帶有土味,因為,稍早雖曾被連根拔起,卻留了幾根帶土的根鬚若隱若現……
馬來西亞和台灣同是海外華人移民社會出身,如果你同意中文是我們共同的精神故鄉,我會向你推薦梁靖芬的新小說集,尤其「刻木」一篇,以淡為師,韻味悠長!
──楊 澤
梁靖芬的小說,有一種沈從文,汪曾祺的閒淡知命,明淨溫暖,一種人心在時間之牆的凹窟與苔蘚,溫柔的用手指撫摸著。一種長鏡頭下,翻動這些歷史之外,南方之南的人物,他們不為人知的祕密。她的故事擧重若輕,讓人低迴,惘然,餘緒久久不能平息。
──駱以軍
〈按摩〉
Melakukan perkara yang mencurigakan,這句話裡的最後一個詞尤其讓人難堪。巧薇第一次放長耳朵偷聽到,還回家認認真真翻了馬來語字典。Mencurigakan,令人懷疑的、可疑的,字典裡這樣析疑。巧薇托著下巴想:這字眼真神奇,什麼都能裝。
〈走索女〉
走索女不怎麼願意提起這一段,是因為後來更早曉得了羞澀。然而那一段在空中飛的個人成長史裡,卻以值得炫耀的光環戳了一個亮眼的印,是第一個靠自己能力贏下的功勳。
〈瑪喬恩的火〉
現在,床頭邊的菸灰缸倒是空的。房裡仍然不缺陽光。黃金葛青綠而沒有頹氣。瑪喬恩強把視線從床上凹槽處移開──不知躺了多久才形成的,面積又因體型的日漸瘦小而節節敗退,在屁股和背脊的地方陷得最深。
〈黃金格鬥之室〉
雖極之不願回想,可又實在忘不掉那段與外人共同方便的荒謬與不便的經歷。於是偶爾也抖出來談談。當一場笑話或苦盡甘來什麼似地,和人談談。你很難想像那是怎麼一回事,我說。事實上我也不甚了解。只知道從我被告誡不能再隨處大小便開始,那廁所的身世就已經那樣。
〈水顫〉
那是久遠的記憶了。久得我背上沸水烙的斑印早不再蹙筋皺絡,航線般漫開去。以前,阿姆像路旁的落地生根,模糊得只有葉形而不見葉脈。自我意外灼傷,阿姆就似飛機草,不只葉脈,連葉邊的鋸齒也鮮明得厲害。
〈土遁〉
一支公、一條狗、一間屋,還有一塊爛芭地,這就是阿爸留給阿峇的全部。阿峇幾乎一有時間就抽著菸想,有時也會看著南嵐的背影想:為什麼呢?為什麼我要帶回一個烏仔讓伊跟住我。為什麼呢?為什麼我給伊吃給伊住,伊還同我不很親。
〈刻木〉
如果,我們的話題繼續在「為什麼」或「為什麼不」上面兜轉,事情將沒完沒了。老師老了,也沒有這種耐性,與啟蒙的必要。我們只是需要久別重逢後的一些舊話題,以勾起回憶,啟動沉寂了近二十年的情誼。
〈顛簸〉
我和阿穆一樣,覺得現在大家都應該重新定義虛擬與實境。至少,再也不能說網路是虛,網外一定就是實。有時我甚至想,胖子阿穆之所以如此依賴網路,多半是因為他在網上化名,成為另一個新生的,自己賜予自己生命的人,而不是神。
作者簡介:
梁靖芬
出生於馬來西亞中部小鎮。大學時主修化學,畢業後進入媒體,任學生刊物編輯三年辭職往北京大學修讀中文碩士,主修現代文學。修讀化學讓她能體會「特例」的珍貴,修讀中文讓她安於用自己的速度去完成想做的事。目前為馬來西亞報章副刊編輯。
〈水顫〉曾獲第六屆(2001)花蹤文學獎馬華小說首獎、〈土遁〉與〈瑪喬恩的火〉分別獲得第七屆(2002)、第九屆(2004)花蹤小說佳作獎。2010年以散文集《夢寐以北》獲第一屆花蹤馬華文學大獎。2013年以〈按摩〉獲馬來西亞海鷗文學獎小說評審獎,同年亦獲第三十五屆台灣聯合報文學獎散文評審奬。
著有散文集《夢寐以北》,短篇小說集《朗島唱本》、《五行顛簸》等。
章節試閱
水顫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
我祖上的船一下海,就是浩浩蕩蕩的二萬人。要把二萬人全裝在一艘船上,那船準大得駭人。我祖上不笨,但也造不出如此大船。所以我相信,我祖上南來時必然似候鳥群飛,分乘大小寶船二百餘艘,大鵬般翩然而至。
大海是倒過來的蒼穹,我祖上的大鵬船隊緊貼著蔚藍航行。雲帆高張,晝夜星馳,船隊路經處所激起的浪花,足把海面拔高幾尺。鵬首是戰船組成的前哨,逐漸收窄的喙精銳得能戳穿鋼板,把礁石趕離。糧船從前哨起,左右二行疊成大鵬體側。拓張的雙翼和尾部是另兩隊戰船,人字撇捺開去。稍一展翎,就是一番硝煙彈雨。我祖上的帥船穩踞鵬腹,另有各式坐船、馬船按功能分守,扮演交通銜接、拖拽之用。
我祖上這一走,就走了二十餘年、三十餘國。我的祖上,明朝七下西洋正使總兵太監,鄭和。若這是電影畫面,必當亮出我祖上面頰豐滿、目光如電的臉孔,身後船桅成柵旌旗幡揚。配樂是緊湊昂揚的鼓聲咚咚,預示歷史上一場偉大的遠航。
自我決定寫下我祖上的故事,阿姆已經半癡呆。阿姆的記憶時醒時壞。我祖上的寶船採用蜂房船體結構製造。最大的功用在於當船底被擊穿,它能將湧入的海水限制在局部船艙,防止全船沉沒。偶爾我懷疑,阿姆腦中必有與蜂房船體相似的結構,像竹筒裡的間隔。阿姆腦中倖存的記憶,當是收在最內層,免被遺忘淹沒。而那恰好是我祖上的故事。
相對於祖上暢通無阻的海路,我不禁埋怨腳下這水窪泥濘,水蛭似攀附鞋底因而寸步難行。霪雨剛止,混濁水窪仍意猶未盡泛著圈,阿姆就催逐大夥進山。只有進山,阿姆的癡呆會暫時痊癒。山路逶迤,前幾段還有鋤頭鑿出的泥階,越往前泥階越無影,彷若扛鋤頭的人越發慵懶無力,抑或鋤頭崩斷終棄之而去。一路上盤根錯雜,阿姆卻堅信那是唯一通往海邊的路。阿姆沒上過學,但若讓她深信某事,她會如愛因斯坦的擁躉,對相對論力捍到底。
哞。
一隻被驚動的雨蛙突然鳴聲抗議。阿姆一驚腳下一滑,即似舯舡靠岸失準,砰一聲撞上岸邊橋墩。我來不及挽扶,阿姆已迅速爬起。
哎喲,夭壽。
阿姆怎樣?
無事,阿弟。別弄髒祭品,等陣到大樹頭,要大力打,大力打。
打大樹頭是進山的規矩。往海邊走,大樹頭長在泥徑右邊,老態龍鍾了,板根卻很爭氣。這樹易認,半人高呈三角翼狀的板根恰好長成四瓣,東西南北支撐著樹。幾撮羊齒與紋身藤蟠虯一身,每片葉子都似乞丐手裡的缽競相爭奪陽光施捨。偶有漏網的光,也零碎篩落一地聚不成個氣候。東面板根中心損去表皮一塊,我提起一旁人臂粗樹幹,擊鼓似朝靶心撞去。
阿姆,打三下?
是。大力打。天阿公山阿公借過借過。弟子進山求拜有怪莫怪……
阿姆雙手合十念咒,噗噗噗三聲結結實實轟天動地。與其說是請山神樹精放行,不如說是向魑魅魍魎示警。去,去,別阻咱去路,否則咱祖上不放過你。
我祖上的二萬人當年踏過這土地。一次漲潮讓他們宛如天兵神將掩至,讓靠海的原住民如驚弓之鳥。幾番觥籌交錯,又隨一次退潮隱身而去。只留下阿姆晚年必來還願的金身。我祖上鄭和,如今披一身錦袍安坐三保佛公壇裡。
鎮上的沒這個靈呵。
阿姆年紀老了。老得當年總跟在身後的表哥早已成家,老得昔日豐碩的臀部塌成兩坨肉瘤下墜,老得神志像隨季節變更的樹葉,落葉時癡呆,葳蕤時清醒。而祖上的召喚,是阿姆現在唯一的養料,每年農曆六月狠狠施一回,滿樹繁花。跟在阿姆後跟走,發覺阿姆的步又比去年碎許多。下墜的臀一路折騰顛簸得夠了,才埋在膝蓋窩與小腿上,朝拜我香火鼎盛的先祖。
我祖上一雙如曳明目半垂,氣定神閒高坐龕中,審視艦下無數水蠆。公元一四○五年蘇州瀏家港口,鄭字旌旗隨風獵獵作響。港上萬頭攢動金鼓齊鳴。大鵬船隊在祝福與歡呼中徐徐駛出江心,駛向大海。此後七次駛離中國至東南亞和非洲東岸,遍歷兩大洋六大海、四瓣海灣三大海峽,造訪當時世界五十五座港口城市。我於是相信,岸邊三保佛公壇前的腳印,未必是我祖上唯一的印跡。長十六寸,寬五寸,入石三分。
阿姆,三保公的腳安大?
是。小孩子別亂說話。拜拜,快拜拜。
阿姆,三保公跌倒嗎?
哎喲,閉嘴。
相傳那是我祖上當年上岸,左手及眉遠眺無邊海域,一時失神舉腳往石上一踩,就此留下的凹槽。雨後槽裡積水,能養一尾藍劍。倘若那真是我祖上一腳踩下的印跡,我祖上必是個高個子。難怪站在艦上,他永遠最受矚目。
我祖上的腳印是這單殿式廟宇香火鼎盛的原因。阿姆把供品擺好,囑我同身下跪。我祖上從人變神的過程,我全然不知曉。神龕兩邊的字聯倒被我及表哥無數次念錯。那是我們互炫的戰場。
椰雨蕉風迎福德,銀壽碧海助宣威。
笨。是銀濤,海濤的濤。
噓。你們出去!
阿姆的喉頭如蜥蜴吞嚥唾液,嗓音氣得沙啞顫抖。
阿姆,你說真有三保公嗎?
當然,阿弟。你曉得咱幹嘛不吃舢板魚?我阿姆說起這故事總眉飛色舞,恍若她正是當年大鵬一員,即使當根船桅也無怨。那時你三保公寶船穿窿,海水不斷流落來,忽然跳進一條舢板魚塞著窿。
像阿姆水缸的木塞?
唔。等船安全靠岸,三保公才把魚拈出拋回海裡。
不信,不信你去捉條舢板魚,看看牠背上的指紋。那是證據。當時年幼,也無力質疑阿姆話裡的荒謬。然而我祖上確實因此而航入心底。待年紀稍長,祖上的偉跡甚至在我炎陽烘照的心底無限制擴大。
我祖上長期蟄伏海上,已練就一副如履平地的步伐。每一分浪頭擊來,都要在祖上面前俯身退去。我祖上登上船樓高台瞭望,眼神是嗖嗖魚鏢兩道,直射下一座海港。我祖上的聲音必然如洪鐘鏗鏘有致。手握的航海圖標明數十航道,每一道都水到渠成。在漫長的航行中,祖上偶感寂寞。他最遺憾的,必然是無人與他齊案匹比。窗外是一片浪聲嘩嘩,祖上耳裡一片澄明,二萬餘人的耳語全在他耳輪邊打躬、放行。它們自動拼貼成各種故事供我祖上消閒解悶。
其中有一則我祖上始終津津樂道。那是我祖上與一位西方同行的對話。當然我祖上不可能認識哥倫布。可是誰會在意呢?如果我祖上可以留下石上腳印,讓我祖上與哥倫布對話只不過更能增加祖上的威睿神武。那是我祖上百年後的邈思又竄入海民腦中。
哥倫布遇到我祖上鄭和,是值得記錄的場面。一個晚上,大鵬飛入非洲東岸。我祖上托額於案,一舟明月半窗星影。哥倫布誤入我祖上帳前。他剛平定船隊上一場權力鬥爭的譁變,僅兩個月的航行即盡綻倦容。我祖上背著手,英姿勃發。也許他身高不及哥倫布,所以微微昂頭,反倒長了氣勢先開口。
你往哪?
橫跨大西洋。
那有啥陸地?
不知道。但那是我先發現的土地。
陸上沒人?
有。
那當然不是你先發現的。
我祖上在哥倫布的錯愣中走下甲板,繼續航向下一個港灣。
瑪喬恩的火
安在客廳與大家一起緬懷金妮最後的時光時,瑪喬恩借故走開,上樓右拐入金妮睡房,一看那床頭邊的菸灰缸就惱火。雖然那是安的。或許正因為,那是安的。
扎實的大床,四腿抓地,床沿有淺藍色碎花床單斜斜落下。床褥不怎麼平坦,上面只有一人份的凹印,像失鮮的肌肉久久無法回彈。
「要說幾次,」瑪喬恩幾乎惱羞成怒──金妮正在死去的某個下午,兩人多年不見後的首次重逢,瑪喬恩曾那樣提醒,卻用一種刻意漫不經心的語氣:「那樣子吸菸無疑存心找死。」罵的正是安。
某個見面的下午,金妮專注地扭動水龍頭,水嘩啦沖去瓷杯上的肥皂泡。水流急了,偶爾濺些出來,她敏捷地縮肚閃開,動作與表情豐富,似乎還呶嘴吹了個小調。眼前飛過一隻蒼蠅,被她用抹布「叭」一下就壓扁了。瑪喬恩在後頭想罵那蒼蠅,「找死」二字卻順水漏入下水口,連個吭氣的片刻也沒有。
其實是瑪喬恩自己心虛,提到死字便英雄氣短,愈漸聲細。
那時金妮還能自理生活。瑪喬恩在一旁切開一粒蘋果,瞥見金妮腰後垂下的圍裙繫帶有點油漬。前方近裙襬處也有。一些還是重疊上去的,顏色深淺不同,邋遢的樣子讓她差點沒切傷了手。菸灰缸在各個地方,在冰箱上,在餐桌,在窗沿,甚至在洗碗盆旁,且都插滿菸屁股。
現在,床頭邊的菸灰缸倒是空的。房裡仍然不缺陽光。黃金葛青綠而沒有頹氣。瑪喬恩強把視線從床上凹槽處移開──不知躺了多久才形成的,面積又因體型的日漸瘦小而節節敗退,在屁股和背脊的地方陷得最深。
瑪喬恩彎腰,捉起枕頭拍了拍,以手撫順枕套讓枕餡出落均勻。摸一摸就知道是人造棉,睡起來不怎麼舒適。「怎麼不換個好一點的?」
金妮沒有應答。那時候,以她那樣的體力,似乎也無需對什麼話都要有反應。瑪喬恩繼續絮叨別的,不像往常獨自一人時能從容面對沉寂。
其實那時金妮的精神還好。臉色比坐巴士來探望她的瑪喬恩還紅潤。瑪喬恩在路口的小車站下車時,臉被路途顛得發白褪色,腋下汗濕了一圈,悄悄低頭嗅嗅,慶幸今早抹了點除汗劑,復順勢將腋下手袋夾緊。淺黃色仿真皮手袋裡的瑣碎物件五花八門,甚至有一支食指長的鐵哨子勾在拉環的地方。防狼,或更可能的,防攫奪匪用。像她這樣上了年紀的女人,獨身、微胖而顯得腳小,似初來貴境、精神恍惚,最容易被劫匪盯上。儘管她已不算第一次來到這裡。
瑪喬恩下了車,順勢在小車站的欄杆上歇歇。半座臀山先是甩到欄上擱著,久悶的熱氣這才穿過短裙每個線孔,嘶呼噴出如集體放屁。車站背後的告示牌上都是廣告。廣告空白處有些塗鴉,瑪喬恩垂頭看了一會,大部分和上個月來時看過的一樣,無非是罵人去吃屎、下地獄、我屌你媽。生殖器官畫得真不好,比例全錯。或者XX愛YY再加個一箭穿心。三大語種都有。最意外的要屬這句:白天不懂夜的黑。雖然句子太老,比器官圖還虛假,但老舊而含蓄的總能戳中瑪喬恩的胃。她知道那是首歌,大熱天卻仍打了個顫。哎,肉麻。
是安給瑪喬恩打的電話,說金妮的情況也許不太好了,你來看看吧。
不太好?這事他們是討論過的,自然是趁金妮不在場的時候。比如說金妮最
後的那刻到來時,誰要做那一個決定:讓她維持生命,還是讓她盡快死去。還有後事,葬哪、落土的方式,甚至靈堂上要放哪個名字:金妮,還是丁秀燕。極少提到金妮的女兒維安。
女兒維安剛才還從客廳走過,先天的黃髮似營養不良,毛毛躁躁地束成腦後一尾,耳輪散落一些鬆的,反倒顯得比實際年齡幼嫩。大概也因為沒和歲月耍過什麼心機,腦中沒用過的處女地要比已開發的部分多。金妮剛從醫院裡運回來,擺放在前廳正中,頭與牆之間隔著一個魚缸。電視機連架子被移開了。家小,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沒人理會說不在家裡過世的大體不能擺入室內的習俗。安不懂。女兒維安自然更不懂。還好有瑪喬恩。
魚缸正被黏上白色麻將紙。紙是從前金妮烘蛋糕時鋪盤子用的,不知存放了多久,邊沿有些發黃。瑪喬恩讓金妮的女兒維安去負責那事。瑪喬恩曾懷疑,維安不知認不認得全麻將上的字。後來又想舉千字圖、三字經之類的比喻,終究還是算了。金妮大概根本沒打算讓維安懂得那一些。
糊紙這樣的事明明白白,不用一再言語溝通,維安很順從。瑪喬恩雖沒奢望維安點個頭或有點反應,但看她轉身摸索工具,看她精瘦的背影,一時也只能靜靜看著。說不上是否真有期待。
女兒維安先從魚缸左邊開始糊起,用手鋪平,沒忘記在玻璃轉角的地方壓一壓,隨著魚缸邊沿把紙拉過去。幾次把紙拆下又重新調整,直到遮掉所有反光表面為止。維安一絲不苟地完成,魚缸裡的裸色雌孔雀則悠哉自在,浮近水面吐了粒泡,復往下沉。維安見牠沉下,隨手拿起飼料瓶撒了幾粒魚食,瓶內即無聲再響。只有這樣多。她伸食指碰觸水面,孔雀知無別物爭食,上來靠了靠後閉嘴彈開。不久再回來,等魚食浸軟發胖。一點都不似平常魚類愛狼吞的習性。維安乾脆把下巴擱在魚缸口上一起等。木無表情,或只有一種表情。金妮生前也不怎麼打理,說是死剩的種,任牠自滅。安則對一切都不上心。
靈堂照片已經送來。是金妮剛生下維安不久後照的,翻拍重洗。燙過的髮有點生硬,劉海呈波浪狀傾斜豎立,像額頭砸了塊盤子,已是那年代最前衛的心思。眉毛修得細長,六分臉繃緊,顴骨收得很好,下巴還沒有下垂。就眼睛瞪得有點不老實,老費勁張望。
客廳中除了金妮照片上的玻璃極微弱地反著光,其他的鏡子或掛畫早已讓白
紙糊住。這樣,如果金妮回來想照照鏡子,就只有靈堂前的照片可供選擇了。當然啦,即使她那樣做,看的也是最光鮮的自己而已,瑪喬恩這樣替金妮著想。
照片是安選的,瑪喬恩知道。金妮和安在一起的那些年其實也沒照什麼相。倒是瑪喬恩房裡的存檔要多些。畢竟是曾經同生共死過的,每個階段都想向時間討回些分量。
「同生共死。」金妮,不,丁秀燕某日說的,整個粉臉朝枕頭這端撲來。說完即因也感覺太粵語殘片而笑得渾身亂顫,床架吱呀作響。那時睡外側的瑪喬恩也笑,頭有意無意往床外沿躲。冷不防床頭板另一面被人「碰」地踢了一腳,不耐煩地喊了聲吵:「不就掉了錢包說吃的玩的都由她馬美蓮付嗎。」
畢業旅行留宿的廉價旅店,一間房要擠好幾個人,是同學受不了兩人不肯睡覺的細語而發飆。瑪喬恩吐舌,當下就靜了。金妮掄起拳頭不客氣地敲床頭回敬。同學不忿,馬上回擊一腳。於是你來我往半嬉鬧半認真,大半夜後玩累,也就一一睡去。四周逐漸靜了下來,瑪喬恩倒比玩鬧前更清醒,百般心思卻不敢翻身。偏著頭見身邊金妮不似假眠,垂著眼抖著眼皮看了一會金妮平穩起伏的胸,不知不覺,也互靠著頭睡了。
還有更同生共死的,是出國念大學。兩人幾乎互相攙扶著一起出去,一路跌跌撞撞。飛機掙脫地心昂然翹首那刻,紛紛緊抵著椅背喊了口驚。金妮的家人沒到機場送行,似她抗爭勝利後的必然結果。
金妮或許還懵懂,瑪喬恩倒是真感到悲壯,她的行李幾乎超重,有一種風蕭水寒的準備。瑪喬恩知那時誰也不看好那國度,不論你上得了多好的學校,回來那文憑終究是廢的。兩國剛正式建交,學生簽證這樣的安全感還不普遍,要去,只能當普通訪遊,可那也是互相暗防著的。繳了費且身家清白的,說讀便讀,只是得半年出入一次做一回安分國民,若不照做便當逾期逗留查辦,千里萬里遣你回來,以後別想再走。況且還是兩個少女。這事讓瑪喬恩警惕不已,每半年的某些天日,是要當末世審判日來反覆提醒背誦的。提醒者大多是瑪喬恩,拉著金妮到境外打個轉,在護照上蓋章,三兩天便又若無其事入境舊地。
還有一次在大學上電影史,課堂裡放老電影《大路》,因為是默片,對白都是字,僅戲裡眾人合唱歌舞時有音。於是大半個課室全罩在一個無聲洞底,偶有衣角摩挲,全都一清二楚。明明是張口要喊的戲,戲裡主角張口一呼,畫面霎時換了塊文字板,像極聾子啞巴對戲,看得很壓抑。瑪喬恩和金妮坐在一起,原就不感興趣而心不在焉,見是無聲,更悶。金妮直打呵欠,很小心了,仍免不了上下顎猛地咬合時發出的細微聲音,惹得右側同學頻頻白眼。瑪喬恩坐她左側,偷偷幫著用筆尖戳、用手指擰著讓她清醒,自己卻也沒信心挺不挺得過去。
直到有幕戲裡二位女角因事高興歡呼,較強壯的女二號轉身把女一號攔腰一抱,居然將人家整個抱起就地打轉,勇猛形象震得課室眾人「哇」聲四起。最後跌坐椅上,將女一號身體打橫放斜,整一個姊妹情深。兩女還在興奮對著話,冷不防女二號一掌拍落女一號胸前,如翠樹擒波,看得課室裡男女一下就炸了鍋。驚嘆藏著賊笑連連。爾後老教授分析,三、四○年代默片性別意識模糊,直到後來那部《黃土地》出土,接連下去的電影才有了具體的女性與男身。這事瑪喬恩亦記得清楚。在金妮和著眾人鬼笑時,自己也笑,卻有意無意躲過了畫面的光。電影接下來再沒有那類的接觸,金妮繼續走神。瑪喬恩鬆了口氣,卻想到同生共死。
水顫
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
我祖上的船一下海,就是浩浩蕩蕩的二萬人。要把二萬人全裝在一艘船上,那船準大得駭人。我祖上不笨,但也造不出如此大船。所以我相信,我祖上南來時必然似候鳥群飛,分乘大小寶船二百餘艘,大鵬般翩然而至。
大海是倒過來的蒼穹,我祖上的大鵬船隊緊貼著蔚藍航行。雲帆高張,晝夜星馳,船隊路經處所激起的浪花,足把海面拔高幾尺。鵬首是戰船組成的前哨,逐漸收窄的喙精銳得能戳穿鋼板,把礁石趕離。糧船從前哨起,左右二行疊成大鵬體側。拓張的雙翼和...
作者序
序 有時就是會這樣
這幾年,不寫字的時候,我打鼓。每天定量,每天,盡可能準時坐在架子鼓前,讓肌肉熟悉抖動的節奏。
不打鼓的時候,我偶爾會想起課堂上一對一教學的鼓手老師。他的年紀不小了,養著一大坨肚腩,早早消除了我以為打鼓是一種瘦身運動的幻想。想起老師,我就會想起所謂「狀態」這回事。
以前,我是不怎麼確信「狀態」的存在的。哦,我當然知道狀態的意思,知道萬物不可能永遠保持在一個平衡點上,知道日常裡有高低起伏,身體有疲憊與舒服的時刻。我僅僅不太確定「狀態」的形狀,不太確定,它具體的影響。
現在我大概知道了。狀態就是,一塊鼓皮的模樣。或是,我老師肚腩抖動的模樣。
因為是一對一的教學,在偌大的音樂課室裡,常常只有兩套鼓,與我們兩個人。我們的鼓,一如我們般彼此對坐。老師怎麼打,學生就跟著怎麼打。這看起來最為貼心的布置,其實常常苦了我。很簡單──老師的左手,是我的右手;老師的右腿,是我的左腿。我們互成鏡像,卻只有我需要時刻注視著鏡子。起初,開始學鼓的時候,非常簡單的敲擊法我也跟不上,我的腦袋花了太多力氣,去糾正我們左右對調的現實。
好幾次,鼓棒脫手而出讓我差點打到老師。
等到我的腦能熟練切換方位,自動調整左右,已是兩年多過去了。老師並沒有停下來等我,幾乎每一堂課,我們都在摸索新節奏。就在有一次我實在打得有夠糟糕的時刻,他說起「狀態」這件事。
老師不是華裔,他不講中文。說起狀態時,他用的是英語,那不是一個詞,而是一個句子──「有時就是會這樣。」
有時就是會這樣。
比起起落、好壞、能或不能,我聽到的那個最為關鍵的訊息,是「有時」。第二個關鍵的字眼是「就是」。這兩個詞其實相悖,前者多少有些猶豫、磨蹭,後者則果敢而確定。
我知道我的老師在安慰我。但他或許不會知道那樣的安慰不只能讓我安心打鼓,還讓我安心生活。
我實在打得有些糟糕的那次,學的是一套源於辛巴威的節拍。它們有些不按牌理,也非常靈活,反應稍微慢一些,左右手就如不厲害的周伯通互攪了。老師在前頭逐拍帶著,我盡可能亦步亦趨。我們一起練習敲擊了十五分鐘,我卻還是打得亂七八糟。正洩氣地垂下肩膀時,老師說,來,現在我們打另一種風格。
風格?風從哪裡來我還不確定呢,那刻我還在想著辛巴威在地圖上到底長什麼樣子,原有的節拍還學不會,你就要我學新的?說實在的有些氣。
但老師就是老師,我還怕他手上的棒子呢。只好趕緊跟著他的新節奏,能跟多少是多少。
當然,沒有奇蹟地,十五分鐘後依舊慘不忍睹。我想我的腳已經安接到手的位置了,下課後還記不記得正常走路也說不定。就在這時,老師說,好,你現在回頭再敲那一段辛巴威吧。
我敲了。居然,不誇張,真的如行雲若流水,還有些不假思索呢。
老師就抖動著肚腩說了:有時就是會這樣。
有時就是會這樣的吧。你以為什麼再也好不了了,走一走,甚至很可能無章法地亂走,忽然便又有路了。這種變來變去的、「有時」的東西,就叫狀態吧。
你若看到它凝固了,就像抖動肚腩,或敲擊鼓皮般地整整它好了。
知道要給這部舊小說集寫新序言的時候,我就想起這件關於狀態的小事。
這集子中的小說都是舊作,最早的一篇〈水顫〉大概要追溯到一九九九或二○○○年。最新的一則〈按摩〉,應該也是二○一三年的事了。
期間各篇書寫時的狀態都不一樣。但我想,最明顯的狀態上的改變,大概是文字吧。是字句的模樣,與節奏。
都說人生憂患識字始,有時我真覺得這句話的重點不在識不識字,而是,一旦懂得了字,人便會作怪,會在具象化的過程中,改變了事物的原貌。憂患,是因為再也難以趨近真實。彷彿那刻,你只有字,沒有別的,你只相信字,沒有別的。
我們一開始擁有的,自然是字。當然,我的意思不是沒有比文字更早存在的東西。而是,對在這裡的我們(這些馬華寫作者)而言,字的存在,往往先於一切。
在別人純熟講述自己的身世時,我們(這些馬華作者)一頭栽入了文字的形體中,文字先行,除此才來說別的。這幾乎是我們所有少作的樣貌。這是我們這種寫手的共同命運。我們總是先練字。
總要留到,或等到我們可以站到別處時,關於字的執念,才多少可以放開,身段變得不那麼緊繃,節奏變得比較從容。我們,要到這一個階段,似乎才能好好地說一個故事。
當然,也有最終仍不肯放棄的人。在那字與字之間的縫隙,不,它們幾乎沒有縫隙,也許會有終其一生,仍願意與字廝守,讓字始終厚重,以致成為畫布上的筆法,或筆觸般重要的人。那你閱讀它們,就不是在讀一個故事了。不是那麼簡單,以至於,你讀它們,會必須考慮到為什麼是這個字而不是另一個字,或會是這樣長的句子,而不是那樣短的句子。
我大概不會是這類作者了。我發現這十幾年來自己一直在變。那變,首先也確實在「字」身上。它們越來越鬆動。我曾想過,要把這本集子裡的故事重新寫一遍,用此刻當下的狀態。但確實,這同時也會是一個實驗,一個字的實驗,而不太會是小說的實驗。
在純粹的或天生的中文語境中長大的人,大概不會有我們這代/這帶人的困惑、企圖,與不甘吧。他們/你們從小就這樣說話,而我們不是。
但現在我想,也沒什麼關係了。有時就是會這樣,我的鼓手老師說。
序 有時就是會這樣
這幾年,不寫字的時候,我打鼓。每天定量,每天,盡可能準時坐在架子鼓前,讓肌肉熟悉抖動的節奏。
不打鼓的時候,我偶爾會想起課堂上一對一教學的鼓手老師。他的年紀不小了,養著一大坨肚腩,早早消除了我以為打鼓是一種瘦身運動的幻想。想起老師,我就會想起所謂「狀態」這回事。
以前,我是不怎麼確信「狀態」的存在的。哦,我當然知道狀態的意思,知道萬物不可能永遠保持在一個平衡點上,知道日常裡有高低起伏,身體有疲憊與舒服的時刻。我僅僅不太確定「狀態」的形狀,不太確定,它具體的影響。
現在我大概知...
目錄
序 有時就是會這樣
按摩
走索女
瑪喬恩的火
黃金格鬥之室
水顫
土遁
刻木
顛簸
應答的音調──讀梁靖芬的小說 賀淑芳
序 有時就是會這樣
按摩
走索女
瑪喬恩的火
黃金格鬥之室
水顫
土遁
刻木
顛簸
應答的音調──讀梁靖芬的小說 賀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