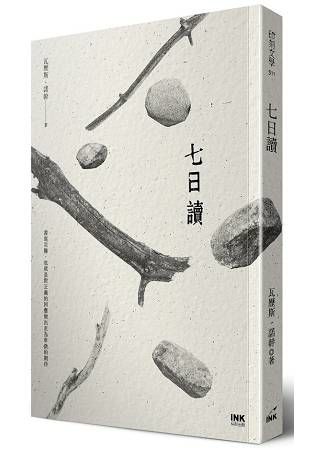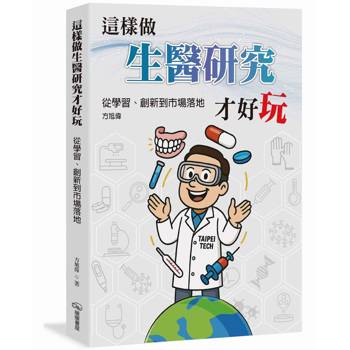災難當前,我們總是周而復始的流離失所
書寫災難,也就是對正義的回應做出至為卑微的期待
歷史再如何黑暗,夜空也會點綴星月的光芒
讀Walis的每一篇故事,故事的回音飄盪在我腦海,很難保持距離客觀閱讀,滿腦袋嗡嗡作響,lengaw、lengaw……。——孫大川
迷霧森林•殘酷之旅。瓦歷斯•諾幹的文學是加法哲學,百川匯入,俱成力量。——張瑞芬
點燃蠟燭,在黑暗包圍的雨夜中續讀一則一則歷史的隱喻,我期待隱喻也有雨過天青的時候,這樣,我的胸膛才不會傳來陣陣的陣痛。——瓦歷斯.諾幹
以上帝創世七日為喻,人類(部落)的白晝與黑夜就此展開,十五世紀遭毀村滅族的美洲原住民族的命運,與現今台灣原住民族的身影交錯穿行,從神話到現世,從狂風驟雨到巨大的毀棄,收錄1999至今,瓦歷斯.諾幹以澄澈的智識之眼所記錄下一切,來自林野的呼喚與部落生命印記。
輯一 籃子裡的世界
沒有了故事,我們就沒有了過去。
輯二 颱風的腳走上來了
大自然的混沌是經過偽裝的秩序,藉著自然模式我們才可以找到隱藏在混沌底下的秩序,我喜歡稱這個秩序為「節奏」。
死亡與新生只在零點一秒中決定,比數學計算還要快速,卻比文學敘述還要無情。
輯三 城市之前
人,即使是被視為最下等的人,都有權繼續過一種有目的感、有自我價值感的生活─一種尋常的生活。
歷史再如何黑暗,夜空也會點綴星月的光芒;烏雲即使完全遮蔽星月,那些光芒也會安放在人心的某個角落,直到甦醒、直到周而復始的災難嘎然而止。
作者簡介:
瓦歷斯‧諾幹
台灣泰雅族人,1961年出生於台中市和平區Miho部落。早期曾用瓦歷斯‧尤幹為族名,後正名為瓦歷斯‧諾幹。漢名吳俊傑,曾以柳翱為筆名。省立台中師院畢業,目前專職寫作,兼任大學講師。2011年「小詩學堂」組詩獲2011年吳濁流文學新詩獎,同年獲聯合報散文評審首獎。已出版作品《荒野的呼喚》、《泰雅孩子台灣心》、《山是一座學校》、《想念族人》、《戴墨鏡的飛鼠》、《番人之眼》、《伊能再踏查》、《番刀出鞘》、《當世界留下二行詩》、《迷霧之旅》、《自由寫作的年代》、《城市殘酷》、《字頭子》、《瓦歷斯微小說》、《戰爭殘酷》等。
章節試閱
七日讀
第一日
在台南某間舊書店以罕見的廉價一百二十元買下民國六十六年初版的《魂斷傷膝澗》一書,封面是狂馬酋長嶙峋岩石模樣的老年人頭照,半圓形副題以紅色字體寫上:狂馬酋長逝世一百年。
攜著宛如墓誌銘的磚頭書乘北上自強號列車,夜晚的列車冷氣彷彿是冬日,乘客蜷縮在座位,等到列車過了嘉義,自強號就像奔馳的詩劃過黑夜的平原。作者狄布朗在一九七○年的序言不無警示著北返的旅客:這不是一本歡欣愉快的書。雖然第一個章節「他們的舉止端莊,值得欽佩」彷如讚辭,但它出自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初抵聖薩爾瓦多島所見稟奏西班牙國王的報告:「這些人民是如此的溫順,如此的和平。臣可向陛下宣誓,世界上沒有一個比他們更好的民族,他們愛鄰如己,談話尤其愉快、斯文,說話時面帶笑容;他們全身赤裸屬實,然而他們的舉止端莊,值得欽佩。」
不到十年,這一支「舉止端莊,值得欽佩」的聖薩爾瓦多島泰洛族十萬人,盡遭毀村滅族。
第二日
黑夜還沒有撕開眼睛,父親已經「碰碰碰」駕馳搬運機開上果園的道路。種作果樹已經是門賠本的行業了,父親不願承認事實,依然故我歡欣上山,像是清晨承接露水的一片葉子。
我所知道的祖父的土地是童年父親帶我狩獵的夏坦森林,中海拔亞熱帶的樹冠底下隱匿著傳說與神話的樂園,日後卻在一紙命令的包圍下早已易手國家部門,現在它已是林務局與農委會的實驗機關所在地—中海拔特有生物中心—我曾試著來到父祖之地,卻因為沒有通行的公文而被排拒在紅色鐵門之外。
狄布朗書寫《魂斷傷膝澗》一書,為了杜白人諷刺之口,大量引用十九世紀美國政府軍方、官方代表的條約會議,和正式集會中的紀錄,為狄布朗的寫作留下了繁浩的官方紀錄,這些「我們說過、做過的事」的紀錄,無論是否為隨興的瑣事,就算是早已忘懷—阿爾維托.曼古埃爾提醒著—長久之後,卻還依然結出了綿遠的果實。雖然我們(台灣原住民族)缺乏與國家對話的紀錄,所幸還留有一支能夠吐出文字的筆,我願我的文字能夠為千百年被歷史壓伏的族人發出異於權力掌控的聲音。
第三日
你們都喝滿了白人的鬼水,就像暑月裡的狗群,跑得發瘋,猛撲自己的影子。美國《明尼蘇達歷史》記錄了蘇族小鴉酋長在一八六二年對年輕族人的訓誡之詞,將近一百五十年後閱讀這些文字,我依然感受到小鴉酋長的絕望之情多於訓誡之意。這一年,美國政府與蘇族間的條約被撕毀,族人染上喝鬼水的惡習,蘇族日漸失去土地,政府不再遵守諾言,部落進入到人為造成的饑荒。作為前進西部的貿易商販,名叫邁立克的白人輕蔑地說:「如果他們餓,讓他們吃草,或者吃自己的屎好了。」
美洲原住民喝了鬼水就會猛撲自己的影子,在我們部落,我們稱這是「公賣局拿走的人」,什麼被拿走了呢?當然是靈魂。
我透過窗戶看到母親從暗夜中顫抖著走回來,在餐桌兼客廳的椅子上坐下,母親說組合屋被燒了。組合屋就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後蓋起的臨時安置屋,好心的地主是長老教會牧師,小兒有個天使般的名字,是部落聞名的「公賣局拿走的人」。據稱傍晚時分又向牧師要錢討酒,「否則就燒了組合屋」—孩子向牧師父親下一道匪夷所思的恫嚇之詞,不到一小時,火光已經延燒到通往天堂的夢境裡邊,幸好鄰人拖著驚夢中的牧師。遠在五十公尺之遙的飲食小店主人老莊曾經敘述這段火災奇觀(包括半個部落的圍觀族人):火勢燒燙的溫度,我都可以賣烤肉了!
一八六三年「小鴉戰役」蕩平之後,美國軍方訂在「鹿脫角月」(十二月)執行絞刑處決,三十八名蘇族桑狄人的身軀,了無生命地在空中擺動。一個圍觀行刑的白人誇稱這一次是「美國最大規模的集體處決」。
第四日
美國小說家福克納一生經營在地寫作,像是用短暫的生命對抗巨大的歷史,他說:「過去絕未死亡,甚至還未過去。」過去其實就是日升月落,每天留下一點蛛絲馬跡,一點唾沫汗液,日久就成為面目可鑑的時間軌跡,歷史的軌跡從未消失,就像定居美國紐約的彼得.凱瑞在二十七年後返回故鄉澳洲寫下的《雪梨三十天》,重新檢視了澳洲原住民歷史,在擁有澳洲原住民血統的友人薇琪的陪伴下,才真正省悟這構成雪梨的土、火、風、水四大自然元素、長久冠以冒險精神的天然舞台—澳洲,其實是在踩碎著原住民的胸膛所建立起來的國度。
「我們的總理可以擁抱和寬恕殺害我們慈父與愛子的人(指的是土耳其),他理該這麼做,然而他卻不能也不願向我們的原住民道歉,為兩百年來的殺戮和虐待認錯。」彼得.凱瑞的歷史反省並非唯一,一八六七年美洲原住民南賽安族盡遭寇斯特(漢柯克將軍部下)率領的騎兵七團屠戮之後,一位有良心、綽號「黑鬍子」的沙朋反對漢柯克將軍的殘酷行徑,電告美國內政部長:「……像一個如我國的強權國家,對少數流離的游牧民族進行一次戰爭,在這種情形下,是一種最可恥的狀況、一種無從比擬的不義行為、一種最使人噁心的國家罪行,或遲或早,上蒼的裁決一定會降諸於我們,或者我們的後裔。」
窗外遲到的梅雨已經轉成颱風般的狂風大雨,溪水暴漲,土石流蕩,接著是,交通中斷,中南部多處成為水鄉澤國,新聞畫面剛剛警示大甲溪河水淹沒橋梁,夜晚的部落隨即停電。我只好點燃蠟燭,在黑暗包圍的雨夜中續讀一則一則歷史的隱喻,我期待隱喻也有雨過天青的時候,這樣,我的胸膛才不會傳來陣陣的陣痛。
第五日
雨水其實已經連下兩周之久,台灣小島已然是豪雨成災的景象。父親果園裡正待發果的甜柿樹,被狂風急雨摧折墜落,母親著雨衣從傾斜不定的雨陣中突圍前進,當作背景的藏青山巒流成黃泥瀑布,溪水氾濫成一面遼闊的流刺網,收拾著山林那些曾經美好的景致。當人類的欲望張掛在災難的面前—大地到底憐憫過什麼?我記起已逝的西蒙.波娃的一句話,特別感到歷史施加於人類的嘲諷:「我發現榮耀其實瞬息即逝,頓生鄙視。」
說不定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在最為黑暗的時刻總是向書籍取暖—詩歌提升我們生活的質量,特別是快樂的程度乃以痛苦衡量—一八七七年美洲洛磯山下的穿鼻族進行逃亡之旅,大兵緊追在後,等到穿鼻族約瑟夫酋長被運送到貧瘠的保留區生活,他日後的演說像極了一首一首的詩句,是以全族的痛苦所釀造出來的詩歌。「讓我做一個自由人吧—自由自由旅行,自由自由停止,自由自由工作……為了自己而自由自由的思想、談話和行動。」
約瑟夫酋長遲至一九○四年於美國政府「保護」下的保留區過世,保留區管理所醫師呈交給議會斷定的死因報告是—傷心。這顯然是對「不自由,毋寧死」所做出的凌遲的極致。
第六日
通電之後,電視螢幕被政治爆料、官商勾結、族群鬥爭的新聞淹沒了水患的災情報導,部落對外的兩條交通動線已遭山崩橋斷阻卻。吃著母親從山野林地取來的野菜,父親瞪著新聞畫面,好像擔心整個島嶼的動盪就要從電視螢幕噴瀉而出,我想到的是夏多布里昂在法國大革命的動亂裡,一位布列塔尼詩人央人帶他到凡爾賽宮參觀一事的感想:「在帝國天翻地覆的時候,還有人要參觀花園和噴泉。」《魂斷傷膝澗》的尾聲僅僅是黑糜酋長的一段話,卻為這本書定調:
「一個民族的夢在那裡黯然魂斷了。那是一個美夢呵︙︙民族的希望破碎、消散
了。再也沒有了中心,聖樹死了。」
我說過,這不是一本歡欣愉快的書。阿根廷文學大師波赫士的直言如劍,為我們的世界做出了美好生活的反證:「只要在世界上還存在一個有罪之人,天堂上就沒有幸福。」
第七日
上帝要休息,因為眾神編織了不幸。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出部落記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約九點,臨時作為緊急避難的國小操場剛剛結束了第二天的早餐,大家食用著前一晚地震過後向命運搶下來的剩餘物資,因此顯出劫後餘生以來至為滿足的神情。我記得前一天大家驚悸地準備著災難後的草率晚餐時,有人對著充斥調味料的各類速食麵發出這就是難民營所吃的食物這樣的言詞,一位老人家鄭重的說:「這樣,以後你們就不會再消遣電視機上的難民營了!」
我離開操場逕自來到已經殘破的老宅,因為我的母親正如部落裡的每個母親,他們都會尋到地震空餘的時間回到自家,期望還能在殘屋斷瓦中找到可以使用的東西,特別是壓在破碎屋瓦中的食物,我知道餘震將隨時來臨,而屋舍將再度玩笑似地趁機奪走人類的生命,我必須趕快到老家喚回我的母親不要再做無謂之爭,因為那將增加我們記憶裡的傷感。
我選擇部落的巷道前進,因為臨靠大安溪的主要交通道路已經出現微小的裂痕,另一方面是。我已經不願觸目我那逐漸崩塌的教師宿舍。到了老家,我懷疑眼前出現的景致應該是螢幕上的戰火剪輯某個片段,突然,一陣熟悉的晃動傳到敏銳的腳底,我驚呼的喊著:Yaya(母親)。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我的母親與掉落的屋瓦出現在咫尺之遙,母親驚疑的對我說:「我只想撿掉落的米粒。」我卻感覺到了死亡與新生擦身而過的驚奇。
我們一同回到操場時,道路的裂痕又擴寬了幾公分,假如這道裂痕垮到了大安溪底,可以想像得出,國小以及操場也將在下一次的餘震中崩塌。離地震已經三十個小時了,原來族人殷殷期待的救援也落空了,只能無助的對著接續而來的地震發著悶氣,但我們都沒有勇氣發脾氣,深怕地魔聽到將再次吞吐牠的巨舌。
從前一晚族人以發電機發電來觀看電視螢幕,我們知道整個災情嚴重至極,但是山區部落的災變在通訊完全中斷的情形下外界不得而知,宛如一座座失散的小島嶼。我因此與學校的主任、部落長老衡量飲食、食用水、衛生等都在極度不利的狀況(已經無法再撐一天)決定外出求援,而救援的唯一通道就是必須越過河水尚未暴漲的白布帆直抵卓蘭鎮。
我與表弟騎著摩托車先來到崩塌的北面道路,亂石與黃泥顯然都在等待下一次的餘震,快速的通過之後竟看到大安溪的溪水開始流瀉著黑黃色的流水,表示上游正下著大雨,這正是我們最不願意遇到的情況,因而加緊速度越離隆起或凹下的路面是我們唯一的做法,到達內灣,果然有黑水等待著我們的來臨,下定了決心,摩托車奮勇的闖越黑水,我回頭望著部落黃澄澄的山壁,它們似乎發出崩塌的歡宴,每一陣落石,都正確無誤的撞毀我的心坎,我對著自己說,這是我的部落,是我祖父的祖父的部落,我要讓它的呼痛聲傳出去,我要讓外界的人們知道受困的山區需要緊急的物資援救。崩塌的部落需要規劃緊急的臨時避難處所,我要我的族人都平安,我知道每一個人都希望他的家人、族人都安全,就是這麼微小的願望支持著往前衝的力量。
越過內灣急水,卓蘭鎮就在眼前,我如此倉皇的奔離部落,因為,離開是為了再一次的回來!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七日讀
第一日
在台南某間舊書店以罕見的廉價一百二十元買下民國六十六年初版的《魂斷傷膝澗》一書,封面是狂馬酋長嶙峋岩石模樣的老年人頭照,半圓形副題以紅色字體寫上:狂馬酋長逝世一百年。
攜著宛如墓誌銘的磚頭書乘北上自強號列車,夜晚的列車冷氣彷彿是冬日,乘客蜷縮在座位,等到列車過了嘉義,自強號就像奔馳的詩劃過黑夜的平原。作者狄布朗在一九七○年的序言不無警示著北返的旅客:這不是一本歡欣愉快的書。雖然第一個章節「他們的舉止端莊,值得欽佩」彷如讚辭,但它出自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初抵聖薩爾瓦多島所見稟奏西班牙國...
推薦序
(序)
lengaw
孫大川
0冷傲
Walis 突然打電話來,心想一定不會是什麼好事。果然,「要出書啦,在印刻老初那邊,當然想到老大哥你嘍。稿子怎麼給你?Line 嗎?」拜託,屬於手工業時代的我,怎麼可能用 Line 來閱讀,難道整本書只有十幾頁嗎?「好啦,Email 到你學校,信箱沒變吧?你列印出來,就幫我寫個序啊。」隔兩天,秘書將厚厚一疊文稿放在我桌上,順手翻閱幾篇,哇,簡直目不暇給。尤其 Walis 信手拈來的讀書摘記、神話傳說、部落紀實或想像的黑色連接,天馬行空,我完全跟不上。心裡不免暗罵老初,怎會答應這樣集結編排 Walis 的作品。在我看來,這些文章應該分成三本短薄的集子,讓讀者一篇一章、一字一句慢慢讀,統統放在一起,令人窒息。
序要怎麼寫呢?不想分析,更不想東拉西扯。我想起童年在部落後山,隨父親走在狹窄山谷間的回憶。父子對談的回音嗡嗡作響,我好奇的問怎會這樣?老人家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告訴我這種現象卑南語叫「lengaw」(冷傲)。少年時代彈吉他,愛死了音箱的共鳴,輕輕撩撥,同時響應。lengaw 就是回音,就是echo!能不能用 lengaw 的方式寫序呢?
1捕鼠人
卑南族的布勇(puyong),從小就是捕鼠高手,每回部落大獵祭他常獲「獵
王」的頭銜。前不久,他和我從政大側門恆光橋下來,在小公園的公告欄上看到一則海報,吸引他的是海報上畫著的一隻肥大全黑的老鼠。「哇,阿瑪,你們都
市人好狠啊,竟然要殺光老鼠!」我往前細看,原來是台北市文山區公所的滅鼠海報。上面寫道:公所在各里設有毒餌供應站,歡迎民眾來取。旁邊黑體大字,提出「三不」防治鼠患策略:「不讓鼠來,不讓鼠住,不讓鼠吃!」布勇嘴裡喃喃自語:「厲害!厲害!不怕動物保護團體抗議。」過兩天,布勇 Line 給我花蓮T大校門口的一座立牌,上面工整地寫著兩行字:本校校園嚴禁採集或獵捕動植物,違者法辦。」他評論說:「阿瑪,我們東部還是比較有學問,不但愛護動物,連植物都照顧到了。」
2土石流後的學校
八八風災投入救災工作,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同胞們面對災難後不失幽默的個性。某一晚,風雨中在太麻里某受災戶家討論災情。會後喝過鬼水,年輕人們開始唱起歌來了:
我家門前有土石流
後面有漂流木
漂流木的上面有偃塞湖
隨時會潰流
沒關係,沒有關係
原民會有補助
只要每天快樂喝酒
總會有永久屋
配上可愛的動作,風災的苦難彷彿一切凍結,像是大自然給我們製造的笑
料。沒多久,學校的小朋友也都會唱了。
3牧師的兒子
在東海岸部落參加婚禮,路邊辦桌,席開四十幾桌。遠遠看到一位三十多歲的部落青年搖搖晃晃來到我們桌前:「老師,你信耶穌嗎?」一身酒味,但目光有神。「我是天主教徒,當然信耶穌。」我回答說。「老師你一定要信耶穌,真的。耶穌愛我們,以前我曾被酒打敗,但耶穌救了我。每次人家倒一杯米酒在我眼前,我一定虔誠禱告說:耶穌我信你!耶穌我信你!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那杯酒立刻變成了水……。」他亢奮地說。「然後呢?」我問。他一臉虔誠的回答說:「我就恭敬地將那杯酒乾完了。」另一個青年攙扶著他離去時,隔座一位老師說:「他是部落牧師的兒子,三年遠洋漁船回來之後,就成了這樣。
」
Ending
讀Walis的每一篇故事,故事的回音飄盪在我腦海,很難保持距離客觀閱
讀,滿腦袋嗡嗡作響,lengaw、lengaw……。
二○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本文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
迷霧森林•殘酷之旅
瓦歷斯•諾幹及其《七日讀》
張瑞芬
說到瓦歷斯•諾幹,不由得想起二○一一年秋天盛況空前的《賽德克巴萊》,以及他當時獲聯合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的〈七日讀〉。這篇其實並不長的散文,以上帝創世紀七天分節,將山地部落的近年災厄與早期北美、澳洲原住民命運並舉。行文冷靜而節制,全無火氣硝煙。也因為文字的乾淨簡潔,掉書袋掉得剛剛好,反而襯出了背後巨大的悲傷怨念,實在是一篇好文,也成了當時《賽德克巴萊》電影最佳註腳。這之後,我到處都遇見瓦歷斯•諾幹的作品,也同在中興大學兼課並同台評審過文學獎。見他一筆字寫得潦草又不失款式,頗為性格,文壇上有關他的傳言不少,我卻一貫只是保持著距離看他。
這些年,瓦歷斯•諾幹和夏曼•藍波安,幾乎成了原住民作家山與海指標性的代表。多年筆耕不輟,累積的作品數量是其他人無法望其項背的,二人皆中壯之齡,還能愈寫愈多,真是不多見(所不同的是,瓦歷斯•諾幹似乎較諸夏曼•藍波安體制內一點,編雜誌,任小學教師,投稿演說不輟,編漢語字典,到國高中教人寫二行詩,臉書上跟讀者五四三,「瓦歷斯挖歷史」)。但同樣曾受漢化教育,跨越原運與社運,走了一條漫長曲折的返鄉(及文學)道路,切切為自己的族群發聲,我好奇今天在總統府前,如果被小英總統接見並道歉的是他們,他們的反應是否會大過巴奈與張震嶽(「ⅩⅩⅩ,我寫了那麼多你們到底是看了沒?」)。
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從來都只是虛言。小英自己的外祖母排灣族群的血淚,又上哪兒討去? 至於我(一個與瓦歷斯•諾幹約略同齡,疑似有平埔族血統的麻豆人,弱勢文評者),倒是知道當今世界還有歧視原住民的。幾年前在知名版本中學國文課本的編審會上,聽見天龍國某第一志願中學國文老師否決加一篇瓦歷斯•諾幹或夏曼•藍波安入課本,理由竟是「原住民已經有了嘛!總要明夷狄之辨」。身為編審委員之一的我,被後面那句嚇到掉下眼鏡,憤而(也只能)很俗辣的辭掉這個橡皮圖章差事不幹了(「我我我……此生與你漢夷不兩立」)。
日頭赤炎炎,如今想來,那麼多府會發言人或委員會鼓譟不休喬不定政策面,還不如先落實文學面——加一篇瓦歷斯•諾幹〈七日讀〉到課本裡。文章很短(符合需求),補充教材就用電影《賽德克巴萊》與導演魏德聖的訪問(教師手冊、主題討論與延伸閱讀都有了)。
瓦歷斯•諾幹〈七日讀〉是這麼說的:
美國小說家福克納一生經營在地寫作,像是用短暫的生命對抗巨大的歷史,他說:「過去絕未死亡,甚至還未過去。」過去其實就是日升月落,每天留下一點蛛絲馬跡,一點唾沫汗液,日久就成為面目可鑑的時間軌跡,歷史的軌跡從未消失……
歷史的軌跡從未消失。過去絕未死亡,甚至還未過去。小說家且心心念念:「童年父親帶我狩獵的夏坦森林,……在一紙命令的包圍下早已易手國家部門,現在它已是林務局與農委會的實驗機關所在地——『中海拔特有生物中心』。我曾試著來到父祖之地,卻因為沒有通行的公文被排拒在紅色鐵門之外。」
歷史的長河總是不斷向前推進,但只要有少數人記得,這世界就沒完沒了。電影《賽德克巴萊》如此,這本瓦歷斯•諾幹新結集的散文《七日讀》也是如此。風雨雷電兼土石流,幾乎成了一部「九二一後的部落災難學」。
《七日讀》除了篇首這篇主文〈七日讀〉外,如同細數創世紀以來不絕的人世苦難一般,輯一「籃子裡的世界」是部落哀歌,輯二「颱風的腳走上來了」是震災水淹組合屋,輯三「城市之前」談論歷史過往。那一種深切的痛,是漫到了無邊無際去,漫到了你覺得看了都累的心智狀態。你突然發覺,穿越了《戰爭殘酷》(二○一四)這俯瞰世界苦難的史詩小說系列,那個昔日寫《戴墨鏡的飛鼠》(一九九七)、《番人之眼》(一九九九)、《迷霧之旅》(二○○三)時而幽默時而迷惘的瓦歷斯•諾幹有點不一樣了。當然離《永遠的部落》(一九九○)、《番刀出鞘》(一九九二)、《荒野的呼喚》(一九九二)的激情社運與詩作時期就更遠了。
《七日讀》(二○一六)的體例與書寫手法,其實與《城市殘酷》(二○一三)是比較接近的。雖然結集有先後,但都收錄了十幾年間的散文隨筆而成,事實上可做同系列短篇散文來讀,基本上都是稍早《迷霧之旅》的延續。一點點家人,一點點史實,一點點族人流落大城的辛酸與對官方政策的批判,有些閑散隨心的收攏在一塊兒,只是《七日讀》土石流風災雷電特多,和短篇小說集《戰爭殘酷》「以史證文」的嚴謹結構完全不同。
二○一四年瓦歷斯•諾幹用力甚深的《戰爭殘酷》一書,展現了他作為說故事人的絕佳技藝,其實也恐怕是瓦歷斯•諾幹至今最好的一本書。那是鐵絲網和機關槍的悲慘世界,生存與血涙的灰敗天空。一篇小說附一段真實戰爭簡史,從以巴戰爭、國共內戰、車臣獨立、高棉屠殺、賴比瑞亞內戰、哥倫比亞毒梟、寮國生化武器,歸結到和泰雅族群有關的曾祖,祖母與父親以降的家族歷史。從〈羽毛〉、〈鹽〉、〈父祖之名〉、〈黑熊或者豬尾巴〉、〈姬娃斯〉、〈我正要拈熄開關〉以下,正當我以為要寫成一部泰雅版「百年孤寂」時,它嘎然而止了。那是瓦歷斯•諾幹未完成的家族史,還是以世界的苦難鳥瞰自己族群悲劇的宏圖,我為之震驚莫名。只是這部短篇小說出版後,不知是否因為主題太過沉重(正如《賽德克巴萊》般,上集是馘首,下集是肉搏,觀眾的腦袋幾乎是被打糊了,混漿一片),評論界的關注似乎也少了點。
《七日讀》起首幾個部落青年的淪亡記,寫得風生水起頗精彩;輯二則是風災水患不絕,九二一以降,真實的部落土石流悲劇一再重演。〈瑪莎颱風十日譚〉以十日分篇,大概最能總結輯二涵義,旁觀別人的痛苦其實是毫無痛苦的(想想那些在風災新聞裡渾身濕透站不住腳的女記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早期的《論攝影》中,對影像造成的情感疲乏就有過批判。當災難、戰爭影像每日每夜曝露並侵入我們的生活時,人的感受將被腐蝕,道德判斷也會流失,到最後可能無動於衷:「遙遠地,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的痛苦。」在〈瑪莎十日譚〉中,瓦歷斯•諾幹更引蘇珊•桑塔格的《旁觀他人之痛苦》說:
他們只不過要挑釁,你敢看嗎?能夠毫不畏懼的觀看,可予人一分滿足。不敢看的畏縮又是另一重快感。
這可真是當頭棒喝。對那些老覺得這些原住民幹啥不搬離山區水邊危險之地,成天災禍連連搞什麼常要出動直升機浪費社會資源之天龍平地人。
一九九四年,瓦歷斯•諾幹請調回故鄉台中縣和平鄉雙崎部落,任教自由國小,至今已然二十年。憤青成憤老。他人的隱痛,我們聽著只覺得新奇。例如「埋伏坪」(Mihu)這名字聽著就不懷好意,像有一支奇兵要時持突圍而出一般。在平地人心中,大雪山國家森林遊樂區是避暑勝地;鳶嘴山,稍來山適合考驗登山能耐;「三叉坑步道」號稱「小瑞士」,連結東勢舊火車站,小中嵙步道,人少冷門卻是極佳健走套裝行程。可是讀了瓦歷斯•諾幹《七日讀》中的〈舍遊呼〉與〈YAYAYA〉,才知道泰雅族人如狂野不羈的風,早期活動於清末隘勇線圈禁之地,「三叉坑」就是他們後來被無情侵奪,原稱Sr-yux的祖靈地。歸結到底,我們的旅遊勝地,原是建築在人家家園破滅的痛苦血淚上,就像瓦歷斯•諾幹早期的詩作〈關於1930年,霧社〉:「遙遠的記憶有如夢的泥土/深黑色的夢魘底下/有著肥沃的血液」。
這東勢北方大安溪的上游,乃至大安溪(男人之河)、大甲溪(女人之河)、中嵙崁(聚集樟樹的小山)可全是他們泰雅族北勢群神聖的祖靈之地,生身之所。九二一大地震重創「三叉坑」,部落餘生者集體遷出。〈YAYAYA〉寫的是母親伊娃蘇彥的一生,伊娃蘇彥生為泰雅女兒,父親客籍入贅部落,日治年代備嘗艱辛,〈延伸練習〉裡寫到外祖母生生為遠古泰雅的活化石,赤腳可把鐵釘踩彎(「雞爪番」又稱黥面番,足證名不虛傳),同樣的家族傳奇。
這些古調,看似尋常,《七日讀》用來作為結束的兩文〈尋常生活〉、〈周而復始〉,則用加薩走廊的以巴衝突歷史,對應泰雅族群的百年苦難,也回應了〈七日讀〉這個用美洲與澳洲原民對應台灣原住民的開篇。以巴衝突,是永無止盡的民族世仇,〈周而復始〉可與瓦歷斯•諾幹短篇小說集《戰爭殘酷》裡的〈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合看,巴勒斯坦女殺手,人肉炸彈,保證溽暑中讓你寒毛颼颼豎了起來。聖地實為戰場,和平其實並不和平,自由其實沒有自由。像一八七七年美洲穿鼻族被追殺滅絕,約瑟夫酋長被運送到貧瘠的保留區,發表的痛苦而心死的演說:「讓我做一個自由的人吧……」
自由不易,寬恕亦然。看著這原住民日的總統道歉戲碼,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是賠不起了,但說不出口,於是成為支支吾吾的空談嗎?瓦歷斯•諾幹《七日讀》最終回的〈周而復始〉或許給出了答案:「舞動民族大義大旗的往往是少數的政客。倖存者伊瑪奇蕾•伊莉巴吉札以《寬恕》一書對著殺害她家人的胡圖族商人費利先說:『我原諒你。』因為寬恕只有在暴力停止的時候才是可能的。」
暴力停止了嗎?誰能給出答案?
從族人、番刀、飛鼠到殘酷系列,瓦歷斯•諾幹是個道地「Atayal」泰雅魂,有著迅疾如風的意志。至今我仍然念念於他早期優美的詩句:「所有的謠言開始被河水證實……/那年冬天,立霧溪、中港溪/大安溪以及未名的溪谷/山羌再也越不過隘勇線飲溪水/有人看見男人的發火器/棄擲在冰凍而哽咽的溪水/散落的髮絲,再也找不到靈魂的居所。」 那是看完《賽德克巴萊》之後的懸念,至今不絕如縷。「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的意義其實超越了霧社事件或原住民抗暴,它所述說的是人之所以活著的意義,要活得像一個「真正的人」,也就是「用自己的樣子去活著」,然而現代人又有幾人能用自己的樣子去活著?早已面目全非矣!
迷霧森林•殘酷之旅。瓦歷斯•諾幹的文學是加法哲學,百川匯入,俱成力量。在蠻荒未闢的心裡,我們都是那個赤足踩過溪澗的年輕獵人,冷靜等待一頭月光下美麗的鹿,那是夢中的情景,那時清晨的西克麗鳥會預示我的未來,而我是善等待的……。
二○一六年八月三日
(本文作者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
(序)
lengaw
孫大川
0冷傲
Walis 突然打電話來,心想一定不會是什麼好事。果然,「要出書啦,在印刻老初那邊,當然想到老大哥你嘍。稿子怎麼給你?Line 嗎?」拜託,屬於手工業時代的我,怎麼可能用 Line 來閱讀,難道整本書只有十幾頁嗎?「好啦,Email 到你學校,信箱沒變吧?你列印出來,就幫我寫個序啊。」隔兩天,秘書將厚厚一疊文稿放在我桌上,順手翻閱幾篇,哇,簡直目不暇給。尤其 Walis 信手拈來的讀書摘記、神話傳說、部落紀實或想像的黑色連接,天馬行空,我完全跟不上。心裡不免暗罵老初,怎會答應這樣集結編排 Walis...
目錄
(序) lengaw /孫大川
(導讀) 迷霧森林•殘酷之旅 /張瑞芬
七日讀
輯一 籃子裡的世界
說個故事給你聽
我也要玩「印地安人」
盜走故事
救命啊!人類
籃子裡的世界
捕鼠人
猶達斯的老花眼鏡
部落觀光的故事
老議員的最後一擊
悲憐牧師的兒子
最後一滴酒
漂流木的下落
偏遠教師筆記
輯二 颱風的腳走上來了
攜子入山
夏天的節奏
閱讀自然的姿勢
出部落記
一九九九世紀末震魔錄
懸崖邊的野地
七二大流‧偶發記載
我與我的颱風們
土石流後的學校
部落災難學
瑪莎颱風十日譚
上山採果
住在水邊
輯三 城市之前
世界正萎縮成一顆橘子
走過裂島的痕跡
烏石柔軟
城市之前
延伸練習
YAYAYA
舍遊呼
尋常生活
周而復始
(後記)部落要書寫
(序) lengaw /孫大川
(導讀) 迷霧森林•殘酷之旅 /張瑞芬
七日讀
輯一 籃子裡的世界
說個故事給你聽
我也要玩「印地安人」
盜走故事
救命啊!人類
籃子裡的世界
捕鼠人
猶達斯的老花眼鏡
部落觀光的故事
老議員的最後一擊
悲憐牧師的兒子
最後一滴酒
漂流木的下落
偏遠教師筆記
輯二 颱風的腳走上來了
攜子入山
夏天的節奏
閱讀自然的姿勢
出部落記
一九九九世紀末震魔錄
懸崖邊的野地
七二大流‧偶發記載
我與我的颱風們
土石流後的學校
部落災難學
瑪莎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