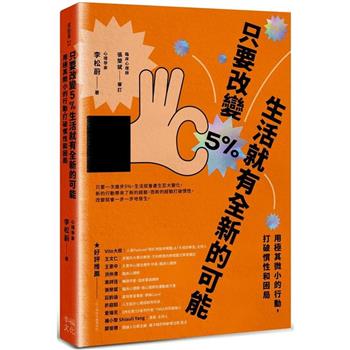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青蚨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青蚨子
番薯島有餘村的頑童金生和死黨羊頭,外加羊頭的瘋癲老爸羊先生,無所事事的三人組合,意外發現隱藏在有餘村的大祕密?蓬萊村裡掌管陽間生死的崔判官,竟一夕丟失生死簿,還連累了七爺、八爺、土地公、土地婆等一干神仙鬼差,翻天覆地四處尋找,卻沒人(鬼?)知道生死簿的下落!陰錯陽差跑到金生家裡的小烏龜,又會將他帶往哪個目眩神迷的生死之境?煙霧繚繞的有餘村裡,陰陽泯沒無界,人鬼相伴相生,跨越生死的追逐與冒險由此展開。
完成《番茄街游擊戰》的異地觀察之後,連明偉將他的目光與書寫心力投注於故鄉母土,藉由孩童與大人相互穿插的視野,審視看似堅實卻又歪斜多元的世界,以充滿魔幻奇想的鄉野傳說和村閭閒話,重構飽滿完足的鄉土空間。
作者簡介
連明偉
1983年生,暨南大學中文系、東華大學創英所畢業。曾任職菲律賓尚愛中學華文教師。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第一屆台積電文學賞、中國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等。著有《番茄街游擊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