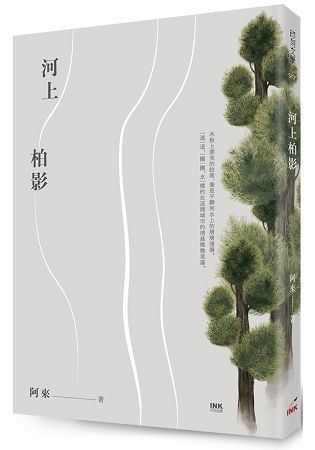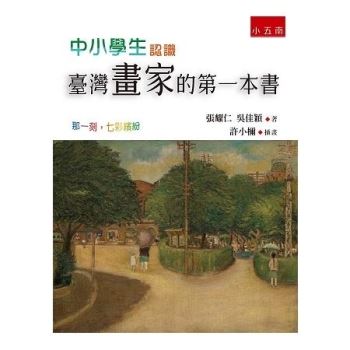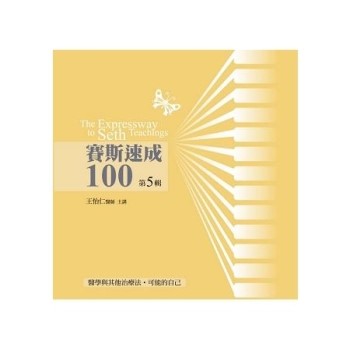序篇二:人。人家。柏樹下的日常生活。
岷江柏是植物。自己不動,風過時動。大動或小動,視乎風力的大小。那大動與小動,也視乎樹齡的大小,幼樹或年輕的樹容易受外界刺激,呼應風的動作尺度就大些。當一株樹過了百歲,甚至過了兩三百歲,經見得多了:經見過風雨雷電,經見過山崩地裂,看見過周圍村莊的興盛與衰敗,看見一代代人的從父本與母本身上得一點隱約精血便生而為人,到長成,到死亡,化塵化煙。也看到自己伸枝展葉,遮斷了那麼多陽光,遮斷了那麼多淅瀝而下的雨水,使得從自己枝上落在腳下的種子大多不得生長。還看見自己的根越來越強勁,深深扎入地下,使堅硬的花崗岩石碎裂。看見自己隨著風月日漸蒼涼。
人是動物,有風無風都可以自己行動。在有植物的地方行動,在沒有植物的光禿禿的荒漠上行動。
現在,有一個人在動。
她拄著一根花楸木的杖,順著一條小路來到了那幾株高大的岷江柏跟前。柏樹長在一個近乎於正方形的花崗石丘上。石丘足有一層半樓房的高度,年輕人攀住包裹著石丘的粗壯的柏樹根,很輕易就上去了。但這個人老了,不能像年輕時候那樣子迅疾輕盈地行動。她的手杖上有一個漂亮的龍頭,那是她木匠丈夫的手藝。木匠做了架木梯,放在花崗石丘跟前,以供他妻子每天去石丘頂上的五棵老柏樹下收集柏樹的香葉。後來,縣裡開發旅遊,這幾棵老柏樹成了景點,在石丘上鑿出了石階,就不用這木梯了,那是後話。有時,木匠也從自己做的梯子上去,站在老柏樹下,用勁從樹身上撕下一長綹暴裂開的棕色樹皮,湊近鼻子,嗅聞這樹的芳香。那些隱約的香氣,像是他身後那條小路上顆粒粗糙的泥土中那些雲母碎片閃爍不定的亮光。風拂動這些碎片時,如果恰巧與陽光相撞,它們就無聲地閃閃發光。就像是它們之間在斷斷續續,不明所以地竊竊私語。太陽被雲遮去,它們集體噤聲,太陽從雲縫中露出半邊臉,它們又一致地興奮起來。
這是五株學名叫岷江柏的樹,枝柯交錯成一朵綠雲,聳立在村前這座突兀的石丘上。
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說是某位高僧念惡咒發大法力,把這石頭從對面山頂上弄下來的,是一塊飛來石。當然,那位大法力的高僧肯定不是為了讓這五棵柏樹有個生根之處,也不是為了使石丘旁邊的村莊看起來有某種好風水,他是為了某種懲戒的目的,為了向人示威而把這石頭從高高的,從村裡仰著頭都看不見的對岸山頂上弄下來的。這個且不去說它。倒是有地質學家認定,這塊石頭的歷史,比旁邊村莊古老許多。許多是多少呢,好多好多個一萬年。也許是一萬個一萬年。至少有這塊岩石在的時候,村子裡的這些人的祖先還是在林中尋食的猴子。
到了後來,當這裡成為一個旅遊景點,為了文化內含的挖掘,宣傳材料上就只說那個傳說,而不肯說地質學家的判斷了。
那個木匠曾經被人安排,每天坐在石丘跟前,一邊給遊客講飛來石的故事,一邊向顧客收取停車費。景點是不收費的,但停車場占了村裡的地面,所以,要收取每車五元的停車費。其實,他就只是一個木匠,一個性格隱忍軟弱的中年人。
性格隱忍怯懦是因為在此之前的人生中,這個人還沒有遇上過什麼讓他能夠揚眉吐氣的事情。在我們的故事開始的時候,終於算是遇上了一件。他的兒子,在這個夏天,高考一舉而中,成為這個僻遠鄉村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孩子。
他的兒子,也是個像他一樣沉默不語的人,一個時常皺著眉頭的人。
那個天天到老柏樹下收集香柏葉的婦人是這個孩子的母親。她見自己兒子皺著眉頭的樣子,總是會心痛不已:孩子,人生來不是為了無故憂慮愁煩的呀!這孩子那時純善,只是笑笑不說話。於是,這女人就埋怨她的丈夫,你這個死人,沒什麼可以傳給兒子的,就把皺眉頭的樣子傳給他了。
木匠這時候卻舒展開眉頭,笑了,這個村子裡的男人有什麼好東西傳給後人呢?獵人把追蹤麝香鹿的本事傳給兒子嗎?政府把禁獵的布告都貼到村裡了。馬幫首領把趕馬的訣竅傳給兒子嗎?村裡家家都有拖拉機,還有人都買了卡車了。他還有一句話沒有說,難道讓驅雹喇嘛把對著天上烏雲念出的咒語傳給他?對喇嘛不敬,在這個村子肯定是不受歡迎的。雖然,現在村裡有接受過培訓的防雹隊用火箭彈驅雹,喇嘛的咒術怕也是要失傳了。
女人說,那麼木匠的手藝呢?
木匠說,手藝還有用,可是,我兒子要上大學了,不用當個沒出息的木匠了。
他還說,善織氆氆的女人會手把手教會女兒嗎?供銷社的機織花布比這個漂亮多了。於是,女人停止了手中紡織羊毛線的陀螺,說,那我紡下這些線也沒什麼用處了?木匠說,差不多吧,你又不是沒看到過商店櫃檯裡那些各種色彩的機紡毛線,不過,你的手沒這個東西也沒地方放著啊。
女人又拿起紡線陀螺,左手轉動了墜在下方的轉輪,右手越舉越高,看著手指間漏下蓬鬆羊毛旋轉扭結,變成交織緊密的毛線。這個女人像大多數婦人一樣,對自己艱辛的生活不以為意,卻不能見別人心靈與身體受到小小的折磨。她見了別人哪怕輕皺個眉頭,都會以為別人內心有多麼難當的煎熬,都要以手加額,說:天可憐見!天可憐見!更何況還是自己的兒子,常常眉頭深鎖,來來去去都在她眼前。
當她和木匠的兒子已經是大學一年級學生時,母親再說天可憐見,兒子就說,媽媽,我不是憂愁,我只是喜歡想想事情。
天可憐見,你那腦袋裡在想些什麼?
嘴唇上剛長出了茸茸鬍鬚的兒子就說,生命啊,世界啊,好多好多啊!這孩子說這話時,有些驕傲的味道,也有些為了皺眉而皺眉的味道。
這位大學生說這話的時候,剛回到鄉下家裡過他這一生中許多個假期中的又一個暑假。從到鄉中心小學上三年級開始,他就離家越來越遠。家隔鄉政府所在的鎮子十五公里。距上初中的縣城五十公里。隔上高中的州府一百七十公里。離上大學的省城五百三十公里。這是他上大學後的第一個暑假。
他和母親說話的地方就在村前那座突兀而起的花崗石丘跟前。
石丘上長著五棵村人尊為神木的老柏樹。
太陽升起來,驅散了峽谷中夏天早晨稠濕的霧氣。曬乾了玉米、土豆和核桃樹上的露水。
母親剛洗了頭髮,正對著鏡子細細梳理。她對站在窗前的兒子說:王澤周,你說柏樹上的露水也乾了吧。
王澤周沒有說話。
母親又說:王澤周,你站開一點,你把光線都擋住了,我從鏡子裡看不清頭髮梳好沒有。
王澤周把身子挪開一點,站在母親身後從鏡子裡看她。母親披散的長髮閃閃發光,直垂到胸前,那面鏡子太小,照不出那麼長的頭髮。王澤周就笑起來,這面鏡子照不出那麼長的頭髮。
母親不說話,她用梳子從頭頂把頭髮一分兩半,在鏡中細細端詳那被梳齒犁開的髮線,是不是端正筆直。
當她開始編結辮子的時候,又對兒子說,王澤周,我讓你看看柏樹露水乾了沒有。
從樓上的窗口望出去,王澤周先看到家裡院子,院子中投下核桃樹的蔭涼,然後是院牆外正在揚花的玉米地,和同樣正在放花的一壟壟土豆。越過這些莊稼地,視線盡頭才是那座花崗石丘和石丘頂上的五棵柏樹。隔著這麼遠的距離,柏樹細碎的枝葉失去了細節,像是一團深綠色的雲,哪還能看到上面露水的情形呢?倒是能隱約聽見石丘背後,湍急的河流發出轟轟的聲響。
王澤周笑了,你這是沒話找話。
母親把編好的辮子盤在頭頂,我兒子好不容易回來一趟,我就是要沒話找話。母親說這話的時候,幾乎都有些撒嬌的意思了。她說,我要是不沒話找話你會打開眉頭笑起來嗎?
母親這樣說話的時候,對著鏡子歪著頭,臉上浮現出年輕女子嬌羞的表情。
王澤周知道,現在該是母親往柏樹下去的時候了。三月,地裡種下了玉米、土豆;四月,給它們間苗,追肥,鋤草;五月,六月,玉米嗖嗖生長,土豆的鬚根四出竄動,又給它們培墒,除草,追肥。現在,它們在七月開花了,傳粉了,珠胎暗結了。農家人才鬆弛下來,在一年中最美好的夏天,獲得一些閒暇的時間,消消停停地做一些美麗的事情。
只有王澤周的父親,周圍幾個村子裡唯一的木匠,永遠不得空閒,忙完了地裡的活計,遠遠近近的人家早捎了口信來。這時節,他就得了空應了口信去給那些需要新家具的人家做几案,做櫃子,往那些几案和櫃子上作繁複的雕花。都是佛教的七寶:蓮花、經幢、海螺、雙魚,等等,等等。母親就留在家裡,把家裡和自己收拾齊整,等兒子回家。
王澤周知道,母親梳洗齊楚了,就該往老柏樹那裡去了。
他取下掛在牆上的籃子,隨了母親下樓。
他提著籃子,和母親一起經過那些茂盛的玉米和土豆,往那座花崗石丘去,往石丘頂上的五棵老柏樹跟前去。母親剛梳洗過的,盤在頭頂的髮辮被太陽曬得更顯烏黑,閃閃發光。王澤周覺得自己提著個籃子,亦步亦趨跟在剛把自己拾掇得容光煥發心情舒暢的母親身後,自己在那種氣氛中都變得有點像是個姑娘了。
於是,他就要把籃子塞到母親手中。
母親頭也不回,你提著!
王澤周便緊走幾步,超過母親,一路小跑,到了那石丘跟前,才回身看著母親不緊不慢地走近前來。這時,他的眉頭又習慣性地緊鎖起來。母親走上前來,捧住他的臉:可憐見的,這麼好的日子,你有什麼樣的心事啊!
王澤周搖搖頭,從母親親暱的手中擺脫出來。我沒想什麼。於是,他說出了那句話:我不是有什麼心事,也不是有什麼憂愁,我只是喜歡思考。
說話的時候,幾棵老柏樹散發出隱約的香氣。
這句話從一個唇上剛長出茸茸鬍鬚的嘴裡說出來。立即就把母親鎮住了,但她還是很鎮定,並不把內心的震動表現出來。她只是重複了一下那個似乎距自己的生活太遠的詞:思考,她又重複了一次那個對她的嘴巴來說還很生疏的詞:思考。
王澤周聽母親說出這個對她來說很陌生的詞,立即眉開眼笑,對啊,思考!
這時兩個人已經走到了花崗石丘跟前。石丘向著村子這一面有好幾米高,柏樹虯曲粗壯的根盤繞其上。王澤周踩著一條斜著的樹根幾步就上去了,顯得靈活矯健。而母親是踩著父親做的木梯一級級走上石丘的。
站上石丘頂上,河水聲猛一下大了起來。河就在石丘的下方,隔著公路,在那裡大聲喧譁。母子兩人對此並不在意。他們在意的是立時充滿鼻腔的柏樹的馨香。空氣如此濕潤,但老柏樹散發出來卻是乾燥的香味。昨天黃昏,王澤周就把一張毯子鋪到了柏樹下面。晚上,群鳥宿在樹上,早晨,鳥群又從樹枝上奮力振翅起飛,那些所有動靜,會使鱗狀的細葉簌簌落下。鋪下那張毯子,為的就是接住這些自然掉落的香柏葉。在樹的上方,二十多米三十多米的高處,不止是鳥,還有河上起來的風,山上下來的風,都會把好些香葉搖落。甚至是沒有風,沒有鳥,只是太陽出來,使枝上稠密的露水蒸發的那一點點動靜,都會使一些香柏葉簌簌脫離枝頭。
新葉長出的時候,就是老的葉子掉落的時候了。
村裡人會來收集這些針葉,作為薰香煨桑的材料。
經過了一個夜晚,和一個早晨,毯子上早已落滿了馨香的柏樹葉。母親把這些細葉都收進籃子裡。王澤周又在周圍那些裸露的岩石上,盤曲在岩石表面的樹根上,收集了另外一些落葉。很快,籃子就滿了。
收集這些柏樹潔淨的香葉時,王澤周問母親,求神佛佑護非要用這樣的香葉才行嗎?
母親答非所問,我不知道神佛要不要我們的供養,我只知道這是自己的心願。
這是上世紀八○年代的某個夏日,這個村子所出的第一個大學生的第一個暑假。這個村子沒出過什麼人物。村子裡有小學校已經三十多年了,但全村讀完小學,中學,又考上大學的,王澤周是第一個。之前,聰穎的,還有更多不甚聰穎的男孩也上學,但沒有讀出過什麼名堂。也有到廟裡出家的。但出了家也是平常,念念經,打打卦,夏天,還帶著經書、鼓、鑔在各村遊走,誦經化緣。也是從這個村裡出去的一個喇嘛,從山頂上俯瞰過這個村莊的地形,說不應該呀,這麼好的風水,不會不出個人物的呀!但這個平靜美麗的村子就這麼平靜地過了說不上多少年頭了,的確也沒出息過什麼人物。那個喇嘛說,不要說這些蓮花一樣環抱村子的山,不要說從村旁奔騰而過這麼大聲的河,就是石丘上那幾株不要一點泥土,直接就把根扎進堅硬的花崗岩的老柏樹了。老柏樹有多老?反正村裡最老的老人生下來,看見它們就是眼下這個樣子:蒼老的樹皮深深爆裂,虯勁的樹根,有些盤曲在岩石表面,有些深深地楔入岩石,使得堅硬的岩石裂開了一道道縫隙。五棵柏樹,和那座石丘就是一個奇觀。但是,在這個村子的第一個大學生王澤周回到村子裡過第一個暑假的時候,中國人四處尋找奇觀的全民旅遊時代,一大巴車的人被一個搖著三角旗,沒心沒肺地背著現成解說詞導引著的時代還沒有真正到來。更不要說後來的自駕車旅遊時代了。
很多很多年來,村裡人的確也認為這座石丘與這幾棵老柏樹確實是這個平常村子的一個不那麼尋常的部分。的確也有從這個村子出了家的人提過,說這樣的風水出現在村子裡,應該是不尋常的啊!但就是說這些話的人本身也沒有顯露任何非同尋常之處。他們自己也沒有成為遠近有名的高僧大德,也就只是能念念度亡經能做做驅除冰雹的法事的尋常之輩。
拋開玄妙的風水不談,這座石丘有一個好處是所有村人都知道的,那就是花崗石丘和靜穆的柏樹一起,遮斷了村前那條湍急河水的喧譁。
越過這座石丘,是公路,公路之外,十幾米高的河岸下,就是在嶙峋的花崗岩間奔湧的大河。這條河在上游和下游都平靜無聲,獨在這一段,在陡然下降的河道中急奔如雷。
這條河該是有名字的:叫岷江,或者叫白龍江,又或者叫大渡河。或者是這三條大水上眾多支流中的某一條。總之是生長著岷江柏的河流中的三條大水中的某一條。或者在四川省,又或者在甘肅省。反正都是一個中國地方。
三條大水都一樣奔流在時而逼仄時而開闊的深峽中間,有些地段被陽光照亮,有些地段則沉沉地蜿蜒在大山移動的濃重陰影裡。
這個村子就坐落在其中某一條河邊。
這座村子是有名字的,但是既然我們準備將其看成是這三條大水邊上的任何一個村落,那麼,就讓其處於無名狀態。有些時候,使某些有名的事物無名也是強調其普遍性的一種方法。
如果不太拘泥於細節,而從命運軌跡這樣的大處著眼,這個村子和坐落在這三條大水邊的那些村子真的幾乎一模一樣。都是在村前村後,立著一株或者幾株岷江柏。這些村子從沒有被書寫過。也許有過自己的口傳故事,但這些故事流傳過三五代人後,又從人們的口邊流失了。所以,它們都是些有著漫長歷史的村莊,但同時又是沒有歷史的村莊。
對這個問題,前些年,村裡來了大學人類學專業和社會學專業的調查人員,打開錄音機想要從人們嘴邊搜集遙遠年代的故事時,村子裡的人說,以前的事情,也許那些老柏樹是曉得的吧。那也是樸素時代,還沒有人為旅遊業,也是某種奇觀化創造早前的故事。比如奉某種動物為圖騰的故事。再比如虔信宗教而純淨明澈的所謂原生態生活。而且,也還沒有人刻意在外來人面前過那種新構造的故事裡的生活。
在過他大學第一個暑假時,王澤周只是登上村前的石丘,幫助母親搜集從柏樹上掉下的帶香味的針葉。他提起鋪在樹下的毯子的兩隻角,母親提起毯子的另兩隻角,那些針葉便簌簌作響滑向了毯子中央。母親半跪在地上,一捧又一捧,把柏樹葉裝了大半籃子,王澤周又從周圍石頭上和裸露在岩石表面的虯勁的樹根上收集了一些針葉,把籃子裝滿。他收集這些柏樹葉的時候,母親要他小心,不要碰壞了石頭上面薄薄的苔蘚。王澤周笑著說,媽媽有環保觀念。
母親露出了女孩一樣天真的笑容,然後,她的臉上露出了憐惜的表情,她說,它們生長得那麼不容易,應該憐惜的啊。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河上柏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90 |
中文現代文學 |
$ 204 |
小說/文學 |
$ 211 |
中文書 |
$ 211 |
現代散文 |
$ 216 |
小說 |
$ 216 |
現代小說 |
$ 21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河上柏影
這個故事從說樹起頭,最終要講的是人的故事,
樹不需要人,人卻需要樹,但人使這個世界上的樹越來越少……
山區小鎮與城市生活的記憶、人與樹的命運。
青藏高原特有的植物岷江柏,是「邊疆」與「中心」的象徵物。
一個偏僻的小村莊與五棵坐落江邊、枝柯交錯成綠雲的老柏樹,那裡是孩童的童年課堂,也是村人的精神信仰和依靠。
當商業侵入農村,轉變慢慢發生……
《河上柏影》中,阿來以主角王澤周的觀點,述說一段關於視五棵柏樹為精神依靠、心靈純凈善良的藏族母親,沉默寡言、勤懇辛勞的木匠父親,以及村莊的故事。在書中展現出人類對自然無盡索取的同時,也對藏區自然資源的未來表示深深憂慮。
樹們競相生長,不分彼此,不分高下並肩一起,櫛風沐雨;
人們卻在製造種種差異、種種區隔,樂此不疲。
作者簡介:
阿來
藏族,生於四川阿壩藏區的馬爾康縣。畢業於馬爾康師範學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雜誌主編、總編及社長。現為四川省作協主席。一九八二年開始詩歌創作,八○年代中後期轉向小說創作。二○○○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為該獎項有史以來最年輕得獎者及首位得獎藏族作家。主要作品有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蘑菇圈》,長篇《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瞻對》,散文《大地的階梯》等。
TOP
章節試閱
序篇二:人。人家。柏樹下的日常生活。
岷江柏是植物。自己不動,風過時動。大動或小動,視乎風力的大小。那大動與小動,也視乎樹齡的大小,幼樹或年輕的樹容易受外界刺激,呼應風的動作尺度就大些。當一株樹過了百歲,甚至過了兩三百歲,經見得多了:經見過風雨雷電,經見過山崩地裂,看見過周圍村莊的興盛與衰敗,看見一代代人的從父本與母本身上得一點隱約精血便生而為人,到長成,到死亡,化塵化煙。也看到自己伸枝展葉,遮斷了那麼多陽光,遮斷了那麼多淅瀝而下的雨水,使得從自己枝上落在腳下的種子大多不得生長。還看見自己的根越...
岷江柏是植物。自己不動,風過時動。大動或小動,視乎風力的大小。那大動與小動,也視乎樹齡的大小,幼樹或年輕的樹容易受外界刺激,呼應風的動作尺度就大些。當一株樹過了百歲,甚至過了兩三百歲,經見得多了:經見過風雨雷電,經見過山崩地裂,看見過周圍村莊的興盛與衰敗,看見一代代人的從父本與母本身上得一點隱約精血便生而為人,到長成,到死亡,化塵化煙。也看到自己伸枝展葉,遮斷了那麼多陽光,遮斷了那麼多淅瀝而下的雨水,使得從自己枝上落在腳下的種子大多不得生長。還看見自己的根越...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篇一:岷江柏。
序篇二:人。人家。柏樹下的日常生活。
序篇三:一次遊行,或者木匠故事
序篇四:花崗石丘和柏樹的故事
序篇五:家鄉消息
正文:河上柏影
跋語:需要補充的植物學知識,以及感慨
序篇二:人。人家。柏樹下的日常生活。
序篇三:一次遊行,或者木匠故事
序篇四:花崗石丘和柏樹的故事
序篇五:家鄉消息
正文:河上柏影
跋語:需要補充的植物學知識,以及感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阿來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12-13 ISBN/ISSN:978986387137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16頁 開數:14.8*21 1.2C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