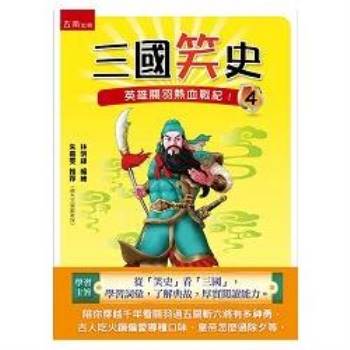尋找河神
都市傳說等級的渠道搜查員
水岸邊的文學精靈訓練師
都市傳說等級的渠道搜查員
水岸邊的文學精靈訓練師
那些歷兩個世紀經由不同統治者實施現代化、都市化,僥倖不死去而被活埋柏油路地面下的溪河圳溝,長久時間等待著有人喚醒他們的靈魂,一起呼叫阿基米德,Eureka!我發現了,我找到了!——林俊頴
謝海盟的追蹤,不是依賴記憶,而是辛勤的踏查,一步一步將水道走成自己生命中分不開的風景;謝海盟的重建,不只有懷舊與感喟,更多加了清楚的歷史詮釋與價值態度。——楊照
刷一層灰,立一面碑,我們凝視災難,把痛苦記憶從城市的河底打撈上岸,阻止世界太快掉落輕薄失憶的滑坡。我不得不召喚班雅明來背書,他筆下背對未來的新天使,張開雙臂抵抗名為「進步」的風暴全面來襲;他徘徊不去,面向歷史廢墟,撿拾斷瓦殘骸,不願順風走,拒絕遺忘。——顧玉玲
我告訴河神,我會一直一直來到舒蘭河上,以我自身的行腳與記憶證明祂存在過,證明祂在這座城市中,並非枉然一場。——謝海盟
第17屆臺北文學年金得主
他看見的是你不曾想像,或已然遺忘的城市紋理
涵蓋水文、人文、社運、文學、電影、動保、社會議題等多元面向的關照,以個人每日五小時的步行,穿越新舊交疊三百年的台北地圖,找尋消失的河道與埤塘、遭加蓋掩埋的水圳、已成遺跡的橋墩、待廢的老宅、駐足過的人、被遷移的墓塚、刷上灰影的死亡、來了又走了的貓族、護守地靈的老樹……沿著水路徒步踏查,逐一指認河神的蹤跡、種種存在過的時光、活過的證明,鉅細靡遺地刻記已逝或將逝的物事人影。他說:「城市河神是最見多識廣的,祂們親眼見證過這座城市三百多年的歷史。」記憶不該被遺忘,縱使人類早已搞不清河圳的流向,他仍執意找到祂們,把河神的記憶還給河神,讓祂們重新擁有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