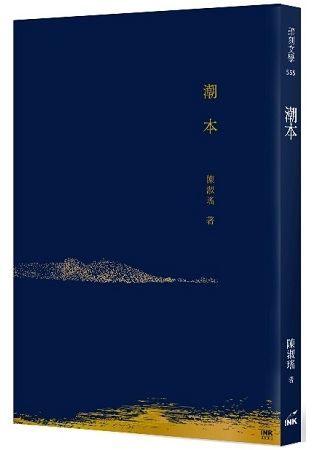湯
只不過上樓去了一會兒,他們已經把我留在廚房湯鍋裡的一碗湯倒進火鍋裡去了,我目瞪口呆,幾乎要哭了。
冬日裡父親喜歡在飯桌上擺個火鍋,將煮好的湯倒進去,再放魚丸,涮些肉片、田裡種的茼蒿青蔥一起吃,我也喝火鍋湯,沒那麼怕湯濁不養生,只是更愛母親煮的湯,簡單扼要,四季分明,清鮮得有種近乎原始的淨化感。
湯是開胃菜,也可以是我的主食,煮了湯常常就不備飯菜了,省下力氣和時間優雅地品嘗桌上唯一一碗湯的沉靜之美,一心一意的滿足。假如桌上有其他東西勾引了我,回頭發現湯冷了,會有點兒懊惱,沒能抓住溫度的起承轉合。
從前工作的地方有餐廳和廚師,餐飯由廚娘分配,湯要自己盛,有個毒舌的大哥每每看我們不顧後面有人排隊,自顧自拿著大湯勺在那大鋼桶裡慢慢技巧的想撈出點青菜豆腐渣兒,總是笑:「呦!撈女啊!」廣東話,意指賣笑的女人。
那時廚師最常煮的是味噌湯和薑片排骨黃豆芽海帶絲湯,後來我也在家裡煮,料浮於湯,不再有撈菜的樂趣了。
以前我對冬天的湯既愛又怕,取暖取到肚裡一碗熱最是舒服,尤其夜裡,一日的冰雪都融了,喝得熱血沸騰;但總是家裡種的高麗菜湯大頭菜湯,一鍋慘白,如冬天的海水望之淒淒涼涼。
一種非常澎湖風味的湯,之所以嘗試煮它,並非鄉愁之類的原因,夐虹詩:「美好是淡的,濃豔也是淡的。」家裡煮的湯我淡記淡忘,而是有回在台北朋友家喝到「螺肉蒜」,老實說我真有點鄙視罐頭螺肉,但也覺得這湯頗有破舊老屋長出蕨葉的孤芳自賞的美,電話裡問了母親我們的做法,用長得像章魚更古怪倔強的石鮔乾代替螺肉,其他排骨或三層肉、畫龍點睛的青蒜照舊。後來在書裡看見這湯也適合添加木耳,尤其是肥滋滋我最愛的豆乾,才真正引發我的興趣。多虧朋友送來越來越珍稀其貌不揚的石鮔乾,像一葉飄搖的扁舟將市場裡平淡無奇的其他食材載來,一鍋香氣熏人的湯煮了出來。
學生時代在一個香港朋友的親戚家喝過一種「西洋菜」湯,用馬克杯盛著喝,特殊的野菜味印象深刻,但葉梗皆已暗黑,色相悽苦。某日在傳統市場遇見一個老婆婆賣著一種陌生的菜,乍看彷彿空心菜,用青草紮成一捆,一問竟就是西洋菜,我躍躍欲試買了一捆回家,耗費大量清水沖洗,下鍋還見一條條青白的小菜蟲浮在湯面上,世界末日的營養湯大概是這樣的吧!
有樣學樣,看見湯裡有什麼就跟著煮什麼,我少嘗試煮西式的湯,以前偶爾煮康寶濃湯,加紅蘿蔔、青菜、香菇、雞蛋,速成,畢其功於一役,曾經和碰巧來訪的朋友分享過這湯,她喬遷新居也用這湯招待我,讓我突然好恨那湯,沒廚藝的人互相做朋友就是這麼回事,圖個溫飽。
傳統家庭煮飯一定有湯,湯意即一個句點。母親煮湯有什麼煮什麼,平常到好像不加思索。夏天我看父親三天兩頭買兩三根綠竹筍回來,冬天則是兩三根白蘿蔔,要不就是苦瓜、大黃瓜、冬瓜,都是用當令的蔬菜煮當令鮮魚或排骨,近乎單調,像小朋友畫圖,一層藍天白雲一層花草樹木一層水底世界。我懷疑是不是還在添加味精,怎麼特別甘甜。有時我嫌那湯過鹹,父親說我們種田人流汗多需要多點鹽分,這種說法倒是很讓人歡喜無言。
那日懊惱沒喝到的是白蘿蔔魚片湯,那值得鮮魚捕手的父親買的魚片之鮮美可想而知,台北也有宜蘭來的基隆來的鮮魚我只是不捨得買,又錦上添花的加了近海的厚殼仔小蛤蜊,常常一袋子或買或送的擱在灶台上,彷彿調味料。不可思議的是這種幸福對他們而言已經乏味似的,為了煮火鍋,又加入清水,和一點泡麵調味包,完全就是暴殄天物,我湯的幻滅。倘若阿嬤還在,他們必定會留碗清湯在鍋底,這麼攪和彷彿就是一種任性的快樂。
------
橋
彷彿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打電話回家,卻顧左右而言他,母親說到了,「這陣子橋上都沒啥車,若往年這時陣,遊覽車,機車,一台接一台&&」我想也是,發生重大飛航意外之後,剩下的夏天會是這樣,我完全了解,但不願想像。那真是落寞啊!不是左外野手,也不是看球賽的人,而是住在球場邊始終遠遠看著他們的人的落寞,球季裡空蕩的球場。
她一定是在田裡工作才看得到那些車,那條橋,和前所未有的八月無蟬的冷寂。她現在走一趟田裡都氣喘咻咻了,工作量遠比從前少得多,也許有較多時間往橋的方向眺望。一次次望不見陽光灑落在漂亮的交通工具上面,蒸騰的熱空氣凝在熱切的眼眸裡,一片流動的幻影。
我們鄰近橋頭的小學,熱天尤其無法專心聽講的學童,潮風中以為有鴻鵠將至,頻頻瞥著窗子。小一升上小六,教室越換越近橋邊,從窗口可清楚看見自橋上慢慢減速轉入村莊的車子,得到親友自遠方捎來歸期的孩子,他更是心不在焉了。那時橋頭有個阿兵哥駐守的崗哨,崗哨上有一盞紅綠燈,我們的生活中唯一的一盞紅綠燈,我小時候還以為阿兵哥是專門躲在裡面管控它的人,看見橋的那頭有人要來就把紅燈切換成綠燈。現在大不同了,瘦橋變胖橋,軍哨撤了,畫蛇添足的交通號誌也不見了。
年初我和朋友在馬公閒晃,她帶我去看一個當兵時愛上澎湖的人刻的貓頭鷹,我看這隻花蓮白石刻的也喜歡那隻澎湖海竹刻的也喜歡,她突然接到女兒求救的電話,說:「公車把同學載走了!」冷靜傾聽,事情是這樣的,她送馬公來的同學到車站,(那是件相當重要的事,別具意義的校外教學,找一天去鄉下同學家玩,看看她片片段段描述的跟你不知不覺想像的一不一樣。)她不停地對著車窗內的同學揮手,想必是一臉熱切依依不捨,卻眼睜睜看著該南下的公車竟然來個大轉彎往北馳去,把同學反方向載走了。媽媽聽女兒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只能一直說:「快叫阿爸去追!」我在一旁只是覺得好可愛喔,追!不要浪費時間想,快追就是了,追回你不能失去的!天真的小孩最怕的事就是「被載去賣掉!」
不一會兒危機便告解除,原來是那司機車開得太順暢,竟然把村子裡的小站給遺落了,只得趕緊掉頭重新來過,那裡固定幾個忠實乘客還在癡癡等待著公車,豈能失信於他們。小女孩站在車站等著,再一次跟同學揮手,更睜大眼睛盯著同學搭乘的車,老老實實開上迎接他們前來的橋,朝遠方奔去。
而後呢,她會有些悵然的獨自走回家,頓時覺得沒有他們一切都失色了,都成了枯山水。和他們共度的這一天她巴不得把生活周遭最美好的部分一次向他們傾現,他們躍躍欲試,更怪的是他們還發掘了她所忽略的,甚至她習以為常都生厭了的東西也值得驚呼連連。最後不是他們意猶未盡把傍晚五點以前要回到家的約定拋在腦後,就是在黏人的主人的懇求下,多玩耍了一班車的時間。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這般多情,年幼時還是個小鄉下人的我也常是這樣。是那些美麗的夏天讓人養成了寂寞的習慣。不過是個來度假的別人家的親戚朋友,和他做成朋友的弟弟或同學不時提起他,一天到晚眉飛色舞說著他,彷彿發現新大陸,轉述他說的話,模仿他說話的腔調和樣子,笑他出的糗,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驚奇演出,足以構成一部冠上他名字的夏日電影。你會看到他的朋友越來越多,遊歷的地方和方式越來越晉級,皮膚有了一層亮彩,髮梢也有幾根曬紅的番毛,站在村裡孩子旁邊不再有黑馬白馬之分,當然羞怯驕傲的神氣也不見了。
有一天他們的語氣會變得低沉,卻憨笑著亮了一下握在掌中的小東西,他送的紀念品。那一天他再度穿上最美的夏裝和新買的涼鞋,忙著檢查東西有無帶齊,還要應付話別的七嘴八舌,額頭上的汗珠一滴滴掉下來。也許此後他會像候鳥般年年歸來,也許僅到此一遊,他會永遠記得那是他幾歲時候的事,而我們有的會漸漸忘掉他,有的會一直記著。
不想裝作若無其事的孩子站在屋頂上,追蹤夏日的朋友乘坐的車子像一個亮點快速劃過馬路,走上橋去。烈日當空,寂寥當空,泛黃的海水襯托著橋的存在。為了帶他遊山玩水,從沒有一段日子那麼地緊扣潮信,剛開始天天煩問大人天天觀看海水,三四天後以此類推,不須上屋頂眺望也能掌握潮起潮落。這片刻的恍惚,竟又將它丟失了,忘記今夕何夕何去何從。還是因為久久注視那橋才知道潮水正在升起,像一張黑膠唱片,在那唱針似的橋桿下默默旋轉。
他繼續在屋頂坐著,不時仰臉逡巡天空,等候友人的飛機起飛。天空亦是一張偌圓的唱盤,唱針是他的眉睫。耳鬢上的髮絲輕撲了兩下,他趕快抬頭挺胸站了起來,那是木心的詩句,「迎面吹來偉大慢板的薰風」,肥壤氣魚騷味鱗金色的風,慈悲的慢板,迎面吹來。
--
除濕機
三月的某一天,我和除濕機一起關在房間。推開房門見它在那兒嗡嗡低迴,反射動作隨即退了出來,怕打擾母雞孵蛋似的,更怕身上的水分被它吸乾。忽然改變想法重啟房門,我只是要來整理一小個抽屜,我在心底跟自己說,也好像是在跟它解釋,它一向獨處。
春潮消退,腳板微微踩到一股地熱,這是適合與除濕機共處一室的季節,也是不能沒有除濕機的季節。
然而它的呼吸聲突然變了,持續地用力喘息,像飛機起飛那樣加足馬力全身顫動,那種壓迫感讓人想奪門而出。
夜以繼日孤苦的掘井人,我知道他累了,但不知道累成這樣!接著他突然安靜無聲。急速拉弦弦音乍斷,不管這空白是樂曲的一部分,還是差錯都好,我需要喘口氣。邊還屏息以待,持續數分鐘,當他又轟隆轟隆排山倒海演奏起來,部分聽眾忍不住鼓掌喝采,部分仍舊保持哀矜的觀望態度。
除濕作業以禮拜作為單位,這是工作,也需一例一休。下個禮拜它上工時飄出悶熱的膠味,愚昧的主人等異味散去,隔天重新開機,狀況依舊。至此終於證實它被榨乾了,拔掉插頭,結束十二年的主雇關係。
這是第一部被我買來被我用壞的除濕機,於情於理我是該憑弔,就算不為機器,也為那一桶桶從屋井打上來倒入馬桶流逝的水,等同我們—屋子和我—的青春之泉。
很快我就忘掉它的樣子,只記得是米白色的,一彎虹柄曾經因吊掛移動笨重的納水塔而斷裂,上面纏繞著數圈透明膠帶。
銘記在心的是上一部除濕機,第一次接觸除濕機這東西,山腳下的老房子空空蕩蕩,基本的家具全無,房東太太只願提供一部可有可無的除濕機,它立在陰暗霉灰的房間白色幽靈似的。兩千多個日子過後,房屋再度清空,曾經像一塊磁石在屋裡巡迴探測吸取霉礦的它依然冷冷立在那兒,彷彿一切從來沒有發生過,它從來不是站在我這邊。
四月我往西南方海潮的方向走,暫時忘卻盆地裡荒廢的除濕作業。以往都是我先打掃完塵封的房屋,才輪到它上場工作,我負責收復,它代表占領,此時有一種有人接替我,我可以休息了的美好感覺。這一次當我踏進房間馬上發現它不在老地方了,放好行李我認真徹底的找了一遍,它真的不見了,驚恐如發現手下唯一的駐兵棄哨潛逃,雖打起精神做我該做的,但無助的哀傷像瀰漫在空氣中的濕氣,緊緊包圍著我。
吹慣冷氣的人到這裡來不慣沒冷氣,用慣除濕機的人不慣沒除濕的地方,我託弟弟幫我買來這部除濕機,妹妹笑說哪有人除濕機買二手的,原先我也有微詞,後來產生革命情感,便覺得這樣也好,一個沒人要用的老兵適於發配邊疆,他定能耐寂寞空虛。這部除濕機開關形同虛設,無論箭頭指向何方,插頭一插便坦克車般的往前開,關閉也靠直接切斷電源,想是前主人曾令它不眠不休的工作,它再不接受別的指令。加上面對的是一個凹陷的插座,冒著觸電的危險換取滿滿一槽水,有水為憑,並非徒勞。種種感官接觸帶來心理滿足,棉被床鋪四壁都擰乾了,住居又從岸邊推回高原。
我是唯一的使用者,肯定沒有人會去動它,但還是開口問了可能知道它行蹤的人,最後他們都說誰會從樓上偷走那部又舊又重的除濕機!
五月我有了一部新的除濕機,進化改良後的它更見輕薄靈巧,不再令我想起「噸」這個字。淺灰色的身軀,濃茶色的水箱,神祕時尚,樣子像早期的收音機,不過是直立起來了,插上插頭,便可聽見屋內的潮聲。水箱積水的高度若隱若現,讓人忍不住擺頭側臉地打探,不過左上角有個一元硬幣大的凹口,水滴滴落的聲音一豆一豆的,光線充足時可看見濺起附著在箱壁上一顆顆亮晶晶的水鑽,要你聽見看見這採集的過程。好像讀一首未翻譯的詩,我明明是不懂,也裝懂了。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潮本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8 |
二手中文書 |
$ 190 |
現代散文 |
$ 190 |
中文現代文學 |
$ 204 |
小說/文學 |
$ 211 |
中文書 |
$ 211 |
現代散文 |
$ 216 |
現代散文 |
$ 21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潮本
這般多情。
想來,是那些美麗的夏天讓人養成了寂寞的習慣。
細流微光,星潮小徑。輕靈字詞翻飛,如晨曦貼行流動,穿透記憶窗格,一格一格閃爍晶瑩泡泡。「我們都太泡沫用事了。」但它能為沉重的身軀幻出雪白的翅膀,飄盪,遊晃,擷收氣味、光影、溫度、聲響,種種藏躲於日常的會心一笑。那些兀自鳴動的纖纖小事,那些浮散於世的偶遇與重逢,化為薰風,和煦地迎面吹來。
點收摺藏一件件慧黠真心,在田壤瓜棚和築了蜂巢的陽台遍灑魔法,尾隨時間穿透夏日的餘光重返離別的橋,或者等一隻瓜帶回來的情感與偏見,憐惜一口被銀合歡包夾的井、一頭困在蓮蕉葉裡的熊,以及想念一碗澄澈的湯。
尋常物事悠悠轉醒,老掛鐘、電視、電話、冰箱、風扇和冷氣機都有了戲,夙夜匪懈的除濕機不眠不休從屋井打上來的,竟是房子與人的青春之泉;脾氣暴躁的洗衣機,則不斷堅持要一切重來。最終,心心念念仍然是人,每一次汲取都是眷戀,時光的潮洗留住了種瓜的父親、拖延旅行的母親、愛聊天的阿嬤、孩子氣的學姊、挽著手一起逛街的外甥女,以及錯身而過的鄰人、徬徨的街頭家庭……啊,還有右手寫給左手,一封虧欠的信。
五十八扇散文窗景,照見水澤閃現又沒去,伏流變成伏光再回到伏流。
作者簡介:
陳淑瑤
天秤座,「生著翅膀的掘井人」,出生成長於澎湖,生活在北部。
採集過多種文學獎雨露,掘有《海事》、《地老》、《瑤草》、《流水帳》、《塗雲記》、《花之器》、《潮本》等七口井。
TOP
章節試閱
湯
只不過上樓去了一會兒,他們已經把我留在廚房湯鍋裡的一碗湯倒進火鍋裡去了,我目瞪口呆,幾乎要哭了。
冬日裡父親喜歡在飯桌上擺個火鍋,將煮好的湯倒進去,再放魚丸,涮些肉片、田裡種的茼蒿青蔥一起吃,我也喝火鍋湯,沒那麼怕湯濁不養生,只是更愛母親煮的湯,簡單扼要,四季分明,清鮮得有種近乎原始的淨化感。
湯是開胃菜,也可以是我的主食,煮了湯常常就不備飯菜了,省下力氣和時間優雅地品嘗桌上唯一一碗湯的沉靜之美,一心一意的滿足。假如桌上有其他東西勾引了我,回頭發現湯冷了,會有點兒懊惱,沒能抓住溫度的起承轉合...
只不過上樓去了一會兒,他們已經把我留在廚房湯鍋裡的一碗湯倒進火鍋裡去了,我目瞪口呆,幾乎要哭了。
冬日裡父親喜歡在飯桌上擺個火鍋,將煮好的湯倒進去,再放魚丸,涮些肉片、田裡種的茼蒿青蔥一起吃,我也喝火鍋湯,沒那麼怕湯濁不養生,只是更愛母親煮的湯,簡單扼要,四季分明,清鮮得有種近乎原始的淨化感。
湯是開胃菜,也可以是我的主食,煮了湯常常就不備飯菜了,省下力氣和時間優雅地品嘗桌上唯一一碗湯的沉靜之美,一心一意的滿足。假如桌上有其他東西勾引了我,回頭發現湯冷了,會有點兒懊惱,沒能抓住溫度的起承轉合...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代序)
巢
初發現陽台冷氣台上有個小蜂巢,我又是一陣急驚風,慌想著如何除之而後快。然而憂患意識常常是這樣來得有憑有據,又去得無影無蹤,乍看彷彿包容了令人擔憂的事物,實則越來越慣性的暫且擱置。
這巢築造在那綠辮子狀的多肉藤蔓上,巢脾以一根枯草梗似的東西固著,外表泛著蠟質油光,好像是焊接上去的,在蒼綠的植物身上燒灼出一塊焦黑。這讓我想起小時候模仿大人的動作,將燭條斜傾,燭油滴在桌面上,趁熱把蠟燭用力黏立在燭油堆上,燭油冷卻成為固態,無依無靠的燭條便直立在桌子上了。不同的是火苗向上燃燒,蜂巢則垂直向...
巢
初發現陽台冷氣台上有個小蜂巢,我又是一陣急驚風,慌想著如何除之而後快。然而憂患意識常常是這樣來得有憑有據,又去得無影無蹤,乍看彷彿包容了令人擔憂的事物,實則越來越慣性的暫且擱置。
這巢築造在那綠辮子狀的多肉藤蔓上,巢脾以一根枯草梗似的東西固著,外表泛著蠟質油光,好像是焊接上去的,在蒼綠的植物身上燒灼出一塊焦黑。這讓我想起小時候模仿大人的動作,將燭條斜傾,燭油滴在桌面上,趁熱把蠟燭用力黏立在燭油堆上,燭油冷卻成為固態,無依無靠的燭條便直立在桌子上了。不同的是火苗向上燃燒,蜂巢則垂直向...
»看全部
TOP
目錄
(代序)巢
輯一
田
草
熊
瓜
湯
橋
無
羊
荒井
晨光
陽台
煙火
輯二
蠢事
蒼蠅
時間
擱置
鬥志
電視
電話
饅頭
便當
零食
冰箱
泡沫
水溫
髮束
耐熱
風扇
輯三
下午
我歌
女傭
女廁
咪咪
學姊
型男
井上記
螢火蟲
流水障
除濕機
小麵店
西門町
咖啡館
鉛筆盒
輯四
餵貓練習
聊天時光
時移季往
照片輸出
作文分數
街頭家庭
繞道而行
十六度C
隔壁的房間
浮現的窗子
伺弄與綠韻
右手寫給左手
幫忙澆水的朋友
第三株沙漠玫瑰
輯一
田
草
熊
瓜
湯
橋
無
羊
荒井
晨光
陽台
煙火
輯二
蠢事
蒼蠅
時間
擱置
鬥志
電視
電話
饅頭
便當
零食
冰箱
泡沫
水溫
髮束
耐熱
風扇
輯三
下午
我歌
女傭
女廁
咪咪
學姊
型男
井上記
螢火蟲
流水障
除濕機
小麵店
西門町
咖啡館
鉛筆盒
輯四
餵貓練習
聊天時光
時移季往
照片輸出
作文分數
街頭家庭
繞道而行
十六度C
隔壁的房間
浮現的窗子
伺弄與綠韻
右手寫給左手
幫忙澆水的朋友
第三株沙漠玫瑰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淑瑤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01-03 ISBN/ISSN:978986387220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0頁 開數:14.8*21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