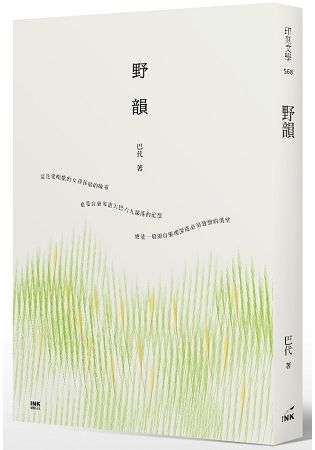這是愛唱歌的女孩莎姑的故事
也是台東卑南大巴六九部落的土地記憶
一股源自靈魂深處必須發聲的渴望
悲傷的時候,害怕的時候,歡樂的時候
就唱歌吧,盡情地唱
如果有一首歌能急躁的心安靜下來
那個第一個起音的顫動,必定從這裡開始
這是虛構的人物與真實故事的交織,顯影部落的過往遺事,那些緊依主流社會又獨自律動的鮮明存在,也紀念我記憶中的美好野溪。--巴代
莎姑出生的村子叫「大巴六九社」,倚靠中央山脈東麓,面向台東平原與太平洋,法魯古溪潺潺流動,那裡有小米田、水稻田和獵場,炊煙升起,夕陽餘暉下,食物的香氣、山羌的叫聲,以及不同家族之間的故事流傳著。
莎姑四歲那年被日本姑丈松本家收養,卻不受新媽媽疼愛,時常挨打受罵,疼愛她的養父過世後,日子更難過,除了擔心受罰,還要躲恐怖的空襲。這時國民學校的先生對她說:「如果你的心被石頭重重壓著的時候,妳可以唱歌,像很久以前一樣。」她哼著歌,偷偷搭上火車,涉過大巴六九溪,回到了原來的家,才發現爸爸跟姑姑一樣壞脾氣,而且她已經聽不懂家裡的話,只會說日語的她重新學習族語。
又過不久,大巴六九部落變成太平村,聽不懂漢語不會說中文的她,才剛將「卡桑」改為「伊娜」(母親),又要煩惱自己該取什麼新名字了。愛唱歌的莎姑,後來不只影響著她的子女,也影響了整個部落。
莎姑和她的先生德里日後成為部落的靈魂人物,只要有部落性的表演或祭儀需要編舞,總是第一個想到他們夫妻,他們的歡笑與眼淚交織出一幕幕動人的生活回憶。
隨著夢境的不斷指引,莎姑的生命軌跡愈發與部落脈動高度結合,那強韌的生命力,呈現天主信仰和搭拉冒(巫術)並存,祭儀與百朗(漢人)的宮廟相互輝映,連一起生活數十年的魯跌(外省人)和發拉嘎(洋人)也有著相近的律動,兀自低鳴不止。
莎姑,抑或者部落,一如野溪的生命力,緊密相依又自外於主流,有著鮮明的律動與傳唱不止的歌謠。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野韻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2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45 |
小說 |
電子書 |
$ 245 |
小說 |
$ 277 |
現代小說 |
$ 277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77 |
中文現代文學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小說 |
$ 315 |
現代小說 |
$ 315 |
小說 |
$ 31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野韻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巴代
Badai,卑南族Damalagaw(大巴六九)部落裔。部落文史工作者、專職寫作。曾獲山海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吳三連獎、全球星雲文學歷史小說獎。著作有研究專書《Daramaw: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巫覡文化》,《吟唱.祭儀: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祭儀歌謠》;短篇小說集《薑路》;長篇小說《笛鸛》、《斯卡羅人》、《走過》、《馬鐵路》、《白鹿之愛》、《巫旅》、《最後的女王》、《暗礁》、《浪濤》等。
巴代
Badai,卑南族Damalagaw(大巴六九)部落裔。部落文史工作者、專職寫作。曾獲山海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吳三連獎、全球星雲文學歷史小說獎。著作有研究專書《Daramaw: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巫覡文化》,《吟唱.祭儀: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的祭儀歌謠》;短篇小說集《薑路》;長篇小說《笛鸛》、《斯卡羅人》、《走過》、《馬鐵路》、《白鹿之愛》、《巫旅》、《最後的女王》、《暗礁》、《浪濤》等。
序
後記
小溪之歌
我一直想起一條無名溪,尤其當我焦慮部落的未來時。
那是在村子北面,一條地圖上沒註記名稱的無名溪。在我童年時期的印象中,那是一條終年不乾涸的溪水,也是記憶最多的小溪流。溪床最寬廣處只有二十公尺左右,水利失修以前,小溪會流入並溢出橫越溪床的灌溉小水道,繼續往下流去,再匯入村子下方更大的灌溉渠道,在冬天或較為乾旱的季節,除了水量變小,這情形大致不變。橫越溪床的灌溉水道旁,是村子向北出入的路徑。這溪段,經常是村民洗衣、簡單梳洗的地方。早年還經常可以看見太平營區的軍人老兵,採割生長在溪床的瓊麻,在溪中拍打揉洗,並帶回瓊麻線。這也是我們戲水游泳,以及學校辦理遠足活動常來的旅遊地。
溯著溪床往上,有一大片水麻生長的溪段,溪水流經較大的卵石區逐漸上升,那大致是比較寬直、穩定、無水窪的溪段,溪水流速較快。在往上到溪水出山口之間,溪水的落差變大,其中錯落著大小、形狀不一的大石塊,那是每一次颱風沖刷而下,經年累積淘洗所形成的,水流鑽著大小石塊之間,或成細長的瀑布,或像桶子倒水那般從一個石縫間迸出,形成一個水量充沛的小潭,隨後在幾個已經深埋固定在溪底的石頭上,又向下分岔流洩。過了大石區往上,溪床變得稍稍平緩,幾戶村民在這裡栽種了不少的經濟作物,我總是沿著既成的農作小徑繞過這個區塊,再進入溪床。這裡幾乎就已經是小溪的上游段,這裡的岸生植物非常茂密,水道因為長年的下切力量,形成兩側高水道低深的凹谷地形,有些溪段變得既深且窄。因為日照亮減少,兩側植物接連著溪水競相爭高與枝長,枝葉經常大面積的掩覆溪床,以至於溪床的石板石塊都成了暗黑色。大體而言,這一溪段的水流較為活潑與不穩定,大小不一的石板石塊間,高低落差會形成大小不一的空間。有的形成水簾洞似的掛著水簾,有的開散形成可容納一個人平躺的水潭,甚至又分流出去,安靜的形成一處有許多落葉、斷枝、水面下青苔雜生的,看似死水的小水窪。於是,蝌蚪聚生、螞蝗、水蛭暗伏,而毛蟹在水底石塊找尋食物或爬上露出水面石頭上,各自盤據與觀望。青蛙在大小不一的水簾洞內的石層、石片上集體歇息,或偶有幾隻在水道兩側涼濕處獨享空間。於是,蛇來了,食蟹獴來了,探險的我們來了,專業採集捕食青蛙、毛蟹的村民趁著黑夜來了,這裡成了整條溪最繽紛熱鬧又卻極其安靜的溪段。再往上,地勢更陡,陽光卻忽然多了起來,不再切割的地形,有三五處不斷滲出的水流,涓滴成串往下流淌,流經之處,長滿了翠綠的水生苔以及諸多我始終叫不出正確名稱的低矮、伏貼生長的植物。這裡,已經是小溪的源頭之一了。
這溯溪的旅途獨特、處處令人驚豔啊。而最被忽略的,卻是溪水那時刻存在,有時令人煩躁的聲音,但仔細聽,協鳴、錯落、各自有韻味。
先說那源頭吧。水氣從斜坡壁滲出,分別在青綠的苔葉上附著、凝結成水珠,逐漸變大,而後順著壁面滑落,紛紛又爭先恐後的掉落在壁面下端,那山壁剝離堆積的一攤碎屑上,發出極輕微的,連續不斷的「喳」聲。再往下滲透、匯集而後順著一株有數根節理條狀的植物,向下滑落滴成一處淺淺小窪,而終於發出較大的「滴哩」聲響。接著,順勢沿著小水窪的縫隙流成一條逕流流竄,與其他逕流結合壯大,在高低落差下,開始發出「稀哩」的聲響,以慶祝眾多水珠們開始奔向遠方的旅途,聲音越發清亮與持續。到了那日照大多被遮蔽的溪段,形成更多的匯集,發出更自信的「嘩啦啦」聲響;來不及加入的,被擠向一邊的水流,順著石塊表面凹處,跳水似的縱跳而下,發出不間斷的「唆」聲;迷了路的水流,流向一灘看似死水的水窪,瞬間認分的,安靜無語的不停轉圈圈伺機找罅隙重回溪流。再往下,農作區的流水聲「空蔥」「里拉」的回應山壁的娑撫與碰撞;大石塊區的各個水流,倒像是慶祝終於流出山口奔向大溪床,因而「淅瀝」「嘩啦」「轟隆」地聲嘶力竭吶喊,以至於到了水麻區,變得沙啞,只能發出「撒啦」的啞音,甚至終於抵達瓊麻與灌溉水道後,勉強的竊竊低語,偶而「稀啦」偶而「唰」的發出聲響,令人一時無法辨識出那是水流聲,抑或是長腿水鳥走過的划水聲。
無名的小溪就是如此生猛、活躍,一如其他的名江大河,有著各自的身世與獨特的故事,也有著相同的滲出、交融、匯集與奔流的過程,如歌如泣,歡樂或悲喜,情緒俱在。
這條小溪後來成為一條乾涸溪床,只在颱風來時,或長期強降雨的非常時期才有出現沖刮、吞噬一切的洪水、土石流。那是在我剛好熟記長江、黃河的地理、歷史資料的時期,也是我剛探索淡水河、濁水溪的故事的時候。多年來,我,或者村子裡的人,似乎都接受溪水死去的事實,沒有人對上游集水區被伐木開墾的事提出異議。直到後來,我開始做部落文史工作的調查、記錄與整理,我忍不住給小溪以她所在地之名,取名「法魯古溪」,紀念我的記憶,紀念村民們來不及產生的警覺。
我寫《野韻》,也是我對部落文史工作的調查、記錄與整理之後,一種文化的警惕與焦慮。部落,會不會如小溪那般,在大社會主旋律之外,即便鮮明的擁有自己的記憶、節奏、旋律、音韻與情感,也迴避不了外部因素的強烈主導與干擾。部落的未來,終究只是瘖啞、無語?或者慘落到悲鳴甚至消失而「無鳴」?最後,只能成為別人的記憶與記錄?
盡管心驚,收稿前,仍不免俗的,借書頁一角,感謝妻子阿惠全心的支持與鼓勵。也謝謝「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的創作補助,讓我可以專心創作。更謝謝「印刻出版社」的全體夥伴,辛苦付出順利出版,讓我獲得持續寫作的動能。
小溪之歌
我一直想起一條無名溪,尤其當我焦慮部落的未來時。
那是在村子北面,一條地圖上沒註記名稱的無名溪。在我童年時期的印象中,那是一條終年不乾涸的溪水,也是記憶最多的小溪流。溪床最寬廣處只有二十公尺左右,水利失修以前,小溪會流入並溢出橫越溪床的灌溉小水道,繼續往下流去,再匯入村子下方更大的灌溉渠道,在冬天或較為乾旱的季節,除了水量變小,這情形大致不變。橫越溪床的灌溉水道旁,是村子向北出入的路徑。這溪段,經常是村民洗衣、簡單梳洗的地方。早年還經常可以看見太平營區的軍人老兵,採割生長在溪床的瓊麻,在溪中拍打揉洗,並帶回瓊麻線。這也是我們戲水游泳,以及學校辦理遠足活動常來的旅遊地。
溯著溪床往上,有一大片水麻生長的溪段,溪水流經較大的卵石區逐漸上升,那大致是比較寬直、穩定、無水窪的溪段,溪水流速較快。在往上到溪水出山口之間,溪水的落差變大,其中錯落著大小、形狀不一的大石塊,那是每一次颱風沖刷而下,經年累積淘洗所形成的,水流鑽著大小石塊之間,或成細長的瀑布,或像桶子倒水那般從一個石縫間迸出,形成一個水量充沛的小潭,隨後在幾個已經深埋固定在溪底的石頭上,又向下分岔流洩。過了大石區往上,溪床變得稍稍平緩,幾戶村民在這裡栽種了不少的經濟作物,我總是沿著既成的農作小徑繞過這個區塊,再進入溪床。這裡幾乎就已經是小溪的上游段,這裡的岸生植物非常茂密,水道因為長年的下切力量,形成兩側高水道低深的凹谷地形,有些溪段變得既深且窄。因為日照亮減少,兩側植物接連著溪水競相爭高與枝長,枝葉經常大面積的掩覆溪床,以至於溪床的石板石塊都成了暗黑色。大體而言,這一溪段的水流較為活潑與不穩定,大小不一的石板石塊間,高低落差會形成大小不一的空間。有的形成水簾洞似的掛著水簾,有的開散形成可容納一個人平躺的水潭,甚至又分流出去,安靜的形成一處有許多落葉、斷枝、水面下青苔雜生的,看似死水的小水窪。於是,蝌蚪聚生、螞蝗、水蛭暗伏,而毛蟹在水底石塊找尋食物或爬上露出水面石頭上,各自盤據與觀望。青蛙在大小不一的水簾洞內的石層、石片上集體歇息,或偶有幾隻在水道兩側涼濕處獨享空間。於是,蛇來了,食蟹獴來了,探險的我們來了,專業採集捕食青蛙、毛蟹的村民趁著黑夜來了,這裡成了整條溪最繽紛熱鬧又卻極其安靜的溪段。再往上,地勢更陡,陽光卻忽然多了起來,不再切割的地形,有三五處不斷滲出的水流,涓滴成串往下流淌,流經之處,長滿了翠綠的水生苔以及諸多我始終叫不出正確名稱的低矮、伏貼生長的植物。這裡,已經是小溪的源頭之一了。
這溯溪的旅途獨特、處處令人驚豔啊。而最被忽略的,卻是溪水那時刻存在,有時令人煩躁的聲音,但仔細聽,協鳴、錯落、各自有韻味。
先說那源頭吧。水氣從斜坡壁滲出,分別在青綠的苔葉上附著、凝結成水珠,逐漸變大,而後順著壁面滑落,紛紛又爭先恐後的掉落在壁面下端,那山壁剝離堆積的一攤碎屑上,發出極輕微的,連續不斷的「喳」聲。再往下滲透、匯集而後順著一株有數根節理條狀的植物,向下滑落滴成一處淺淺小窪,而終於發出較大的「滴哩」聲響。接著,順勢沿著小水窪的縫隙流成一條逕流流竄,與其他逕流結合壯大,在高低落差下,開始發出「稀哩」的聲響,以慶祝眾多水珠們開始奔向遠方的旅途,聲音越發清亮與持續。到了那日照大多被遮蔽的溪段,形成更多的匯集,發出更自信的「嘩啦啦」聲響;來不及加入的,被擠向一邊的水流,順著石塊表面凹處,跳水似的縱跳而下,發出不間斷的「唆」聲;迷了路的水流,流向一灘看似死水的水窪,瞬間認分的,安靜無語的不停轉圈圈伺機找罅隙重回溪流。再往下,農作區的流水聲「空蔥」「里拉」的回應山壁的娑撫與碰撞;大石塊區的各個水流,倒像是慶祝終於流出山口奔向大溪床,因而「淅瀝」「嘩啦」「轟隆」地聲嘶力竭吶喊,以至於到了水麻區,變得沙啞,只能發出「撒啦」的啞音,甚至終於抵達瓊麻與灌溉水道後,勉強的竊竊低語,偶而「稀啦」偶而「唰」的發出聲響,令人一時無法辨識出那是水流聲,抑或是長腿水鳥走過的划水聲。
無名的小溪就是如此生猛、活躍,一如其他的名江大河,有著各自的身世與獨特的故事,也有著相同的滲出、交融、匯集與奔流的過程,如歌如泣,歡樂或悲喜,情緒俱在。
這條小溪後來成為一條乾涸溪床,只在颱風來時,或長期強降雨的非常時期才有出現沖刮、吞噬一切的洪水、土石流。那是在我剛好熟記長江、黃河的地理、歷史資料的時期,也是我剛探索淡水河、濁水溪的故事的時候。多年來,我,或者村子裡的人,似乎都接受溪水死去的事實,沒有人對上游集水區被伐木開墾的事提出異議。直到後來,我開始做部落文史工作的調查、記錄與整理,我忍不住給小溪以她所在地之名,取名「法魯古溪」,紀念我的記憶,紀念村民們來不及產生的警覺。
我寫《野韻》,也是我對部落文史工作的調查、記錄與整理之後,一種文化的警惕與焦慮。部落,會不會如小溪那般,在大社會主旋律之外,即便鮮明的擁有自己的記憶、節奏、旋律、音韻與情感,也迴避不了外部因素的強烈主導與干擾。部落的未來,終究只是瘖啞、無語?或者慘落到悲鳴甚至消失而「無鳴」?最後,只能成為別人的記憶與記錄?
盡管心驚,收稿前,仍不免俗的,借書頁一角,感謝妻子阿惠全心的支持與鼓勵。也謝謝「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的創作補助,讓我可以專心創作。更謝謝「印刻出版社」的全體夥伴,辛苦付出順利出版,讓我獲得持續寫作的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