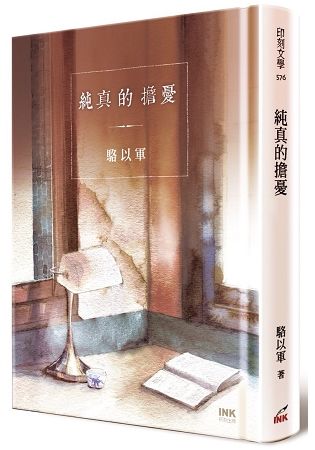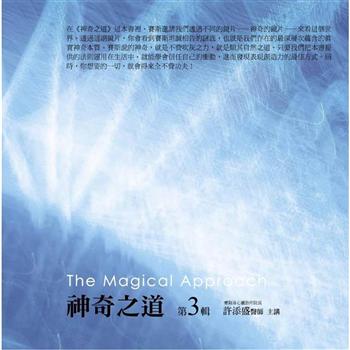圖書名稱:純真的擔憂
我們都活在失落之城裡,努力想把自己修復回來。
在這光速演化瞬燃又寂滅的世間,眼前流洗過的一切,都注定奔向空無嗎?樹葉的光影中翻動的「碎時光」裡,小說家任意垂下一縷鑲上時差的棉線,勾撈出一顆顆如冰糖般凹凸結晶的故事雛形:那些雜沓老舊之街、煙花迷離之物、層次繁複的幽香,栩栩如生封存於記憶的淨瓶中,均是如實存在的生命樣態。
與歪斜抵抗的,在傷害扭曲間倖存的,身體如極限運動般耗損後的修補,向無有之處提取借貸的種種,年輕時光的純真的擔憂,以及創作路上的焚燒,貪戀,踩踏吞食無數壞毀之境的自傷。明亮又閃滅的花火,迴旋飛行的姿態,夢裡尋夢的憾恨、哀逝,吞食過又吐哺出的世界的變形記,這些都存在著,比創作出它們,或正要創作它們的主人,與創作無關的世代資源尖銳對峙,其實要更柔慈的混淌在一塊。
我們活在這城市裡,終會失魂落魄的沿途丟失重要的東西,它或是以玷汙的形式,或是以不那麼醜惡的形式,或是,當你開始回憶、回想它們時,那些東西早已遺棄很久很久了。--駱以軍
本書特色
◎為這個世代、這座城市、這座島,銘刻永恆的喟嘆。
◎66篇穿越舊巷弄、老時光、無人知曉邊陲的繁華如夢。
作者簡介
駱以軍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榮獲2018第五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首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台北文學獎等。著有《計程車司機》、《匡超人》、《胡人說書》、《肥瘦對寫》(與董啟章合著)、《願我們的歡樂長留》、《女兒》、《小兒子》、《棄的故事》、《臉之書》、《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西夏旅館》、《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降生十二星座》、《我們》、《遠方》、《遣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妻夢狗》、《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紅字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