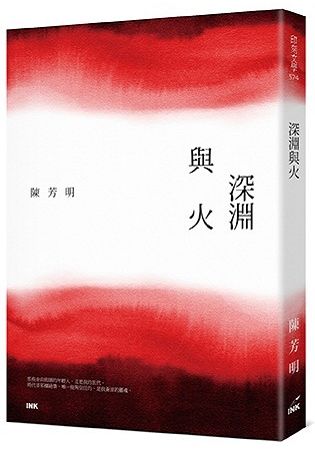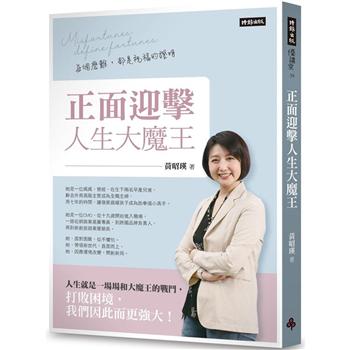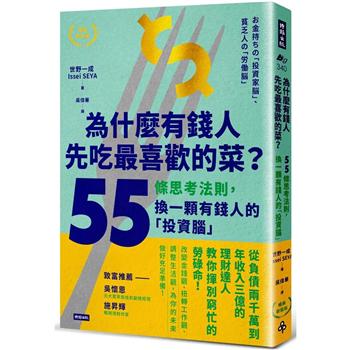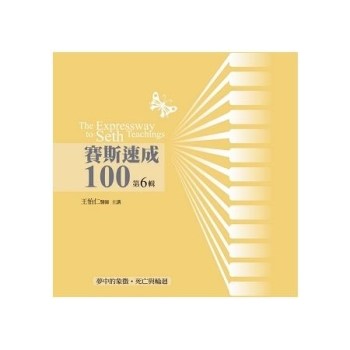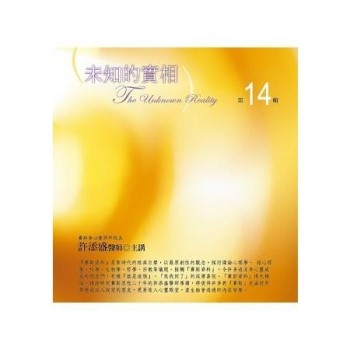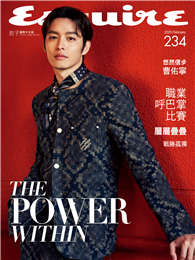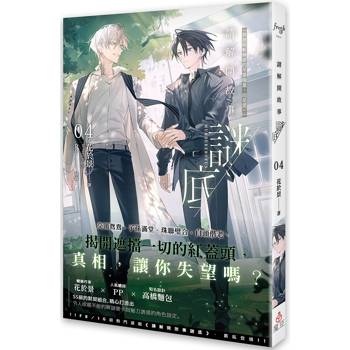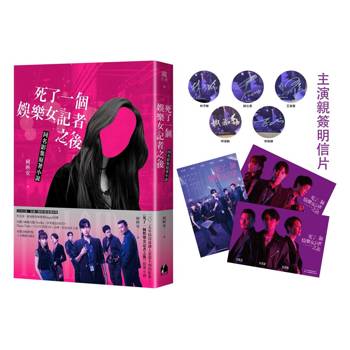牢門打開時
1
春天來時,洛杉磯又回到燦爛的季節。行道樹變得更綠,路邊人家的前院花圃也盛放著豔麗花朵。加州罌粟花(California poppy)開在矮矮的圍籬周邊,燦爛地反射著豔陽光線。編輯部辦公室後面的酪梨樹(avocado),已是果實纍纍。那是加州特有的產物,在西雅圖未曾見過如此碩大的果物。微風襲來,夾帶著南國的悶熱。枝葉徐徐搖晃,唯獨那果實不動如山。那天下午到達辦公室,發現艾琳達正在攀爬枝幹之間。常常來辦公室協助的艾琳達,從聖地牙哥北上夜宿在辦公室。她大概是我所見過,使用流利中國話的洋人。她那時是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候選人,正在從事台灣女工的研究。她到台灣去便是實地考察台灣工廠女性工人的處境。她深深信奉馬克思主義,每次發言時都堅持鮮明的階級立場。艾琳達的生活模式,也是左派人士的典型。她常常在辦公室指控許信良是機會主義者,往往左右搖擺,喪失了革命的原則。
我曾經與她吵過一架,那是一九八一年的聖誕夜。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忙著趕工,希望把編好的報紙版型送到印刷廠,第二天就可以擁有從容的聖誕節假期。每個人的心情都緊繃著,無意之間我與艾琳達有了口角衝突。如今已經忘記到底在爭論什麼,只覺得那晚的心情非常不愉快。工作快要結束時,我非常掙扎,到底要不要在離開前跟她說聖誕快樂。內心矛盾許久,卻說不出口。全部的工作完畢時,艾琳達向我走來。手上拿著一條小小的被子,她說,這是我自己縫製的quilt(拼布),送給你的孩子做聖誕禮物。那條小被子手工很細,是由零碎、顏色不一的小布片縫製而成。她一定耗費不少時間,一片一片銜接起來。就在那個時刻,我感到非常慚愧。這也是我第一次領教了洋人的生活態度,縱然兩人發生激烈辯論,卻不影響個人情緒。反而是我在開口之前,陷入了天人交戰的困境。
艾琳達為我做了最佳示範,可以把個人感情與理念辯論清楚區隔。她不會因為彼此感情融洽,就放棄理念上的辯論。我與她發生口角時,中文與英文同時並用,為的是讓她知道我的說法。艾琳達也是雙語並用,辯才無礙,讓我體會到作為知識份子的身段是什麼。她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極為雄辯毫不稍讓,卻不影響她與我的友誼。她說耗費了一個星期,把這條百衲被縫製出來。因為她看過我的兩個小孩,覺得應該送給他們聖誕禮物。她又從抽屜拿出一個彩紙包裝的禮物,說要給我的女兒。就在那個時刻,我非常感動,久久說不出話來。
她所教給我的,讓我這輩子受用不盡。如何在辯論與情緒之間劃清界線,如何在激烈辯論之後保持禮貌風度,都在那一次吵架中獲得了學習。我也曾經年少氣盛,喜歡與朋友辯論,最後總是不歡而散。在洛杉磯的聖誕夜,我第一次見識了什麼是進退的藝術。那個晚上要離去時,我終於跟艾琳達說Merry Christmas,她走過來輕輕與我擁抱。於我而言,那個晚上,不僅僅是聖誕夜,也是我個人修養的一個重要跨越。
在我所認識的左派人士中,真正使理念與行動能夠完美結合的人,一個是史明,一個是艾琳達。在那春天的下午,我看見艾琳達爬上那株酪梨樹。她一顆一顆採擷下來,裝進她手提的布袋裡。當時我並不那麼喜歡酪梨的滋味,無法理解為什麼她要採那麼多。在辦公桌上,她選擇比較大的酪梨放進另一個紙袋。我問她要做什麼,她說等一下你就知道。原來她選擇比較好的酪梨,走到屋外,一位墨裔的水果販賣車就在那裡。她拿著酪梨與攤販交換不同的水果。那天下午,我們在辦公室享用了香蕉與橘子,完全是她以物易物換取的。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左派知識份子的具體實踐。她從來不擺任何身段,而是在具體行動或日常生活表現出來。艾琳達最喜歡批判許信良,說他是左言右行。她也批評過史明,但是對他所投入的革命工作,保持高度敬意。
艾琳達的家在聖地牙哥,與她的母親住在一起。每個禮拜三都會開車北上,需要三小時的駕車時間,她很少缺席,週三、週四都是編輯部最忙碌的時刻,她自願加入剪貼的工作。縱然已經離開台灣,她仍密切注意著島上的政治變化,也對美麗島家屬表達高度關切。她也是人權工作者,與我同樣屬於國際特赦協會的會員,偶爾也會一起討論韓國、菲律賓的政治犯問題。對人權議題的關懷是一輩子的事,而國際人權工作者往往可以使用觀光的外籍身分去探訪台灣。這個管道,也正是艾琳達能夠接收台灣內部的第一手政治信息。春天時分的一個下午,艾琳達邀我到洛杉磯市區的咖啡店相見,原來是介紹我與兩位美國的女性人權工作者見面。她們剛從大學畢業,正要出發到遠東訪問。咖啡店看來很簡陋,座落在城市的街角。我到達時,她們正在議論著美麗島事件。
雖然我也是特赦協會的一員,卻不能直接涉入台灣的政治案件,為的是防止個人的政治信仰與人權議題混淆不清。我接受的政治犯案件,都發生在韓國、菲律賓,以及中南美洲的獨裁國家。身為會員的義務是,寫信給特定國家的外交部長,呼籲他們考量基本人權,並且釋放政治犯。做這樣的工作似乎輕而易舉,不可能看見立即的效果,但至少可以給強人統治的政權一些國際壓力。坐在咖啡店裡,我發現她們不只是討論美麗島事件,而且也正在議論稍早的一位台灣政治犯白雅燦。經過美麗島事件後,這個名字好像被淹沒了,但是兩位女性工作者並未放棄對他的關懷。白雅燦是在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時,公開散發傳單,質疑蔣經國是否有繳交遺產稅。
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對蔣經國所提的質問,為我們帶來巨大思考。我必須承認,白雅燦事件是最初促使我加入人權組織的關鍵因素。質疑蔣經國的白雅燦迅速遭到逮捕,似乎對整個社會並未造成任何漣漪,但是國際人權工作者從來沒有忘記。兩位女性準備遠赴亞洲,其中的一個行程就是要去探訪白雅燦。這使我非常感動,也許我只能關心第三世界的政治狀況,但冥冥中也換取了國際人士對台灣的關心。我問她們:可能見到白雅燦嗎?兩個人不約而同搖手說並不一定,但是願意嘗試看看。這正是國際特赦協會的精神,所有的關切或探訪並不可能得到答案,但只要受刑人在高牆內,獲知外面些微信息,他們就知道並未被孤立。那種默默進行的工作,沒有報酬,沒有褒獎,更沒有任何回饋。參加人權組織這麼久之後,我漸漸能夠理解人的生存尊嚴,絕對不是由威權統治者來定義。
坐在洛杉磯的街口,城市景象看來是那樣不真實。與兩位即將前往台灣的女性人權工作者談話之際,不免有些感傷。她們能夠進出自如,而我卻被阻斷在千頃海洋之外。在對話時,才知道她們對於韓國、台灣、菲律賓的政治現狀都瞭若指掌。那時的韓國朴正熙與菲律賓馬可仕,都是國際上惡名昭彰的統治者。台灣的蔣經國與他們並列在一起,當然也使我這樣的台灣人蒙羞。冷戰時期已經結束,而三位權力在握者卻拒絕走出歷史。縱然蔣介石已經去世那麼久,身為繼承者的蔣經國對於權力的貪婪仍然毫無節制。他一直把自己塑造成為親民的領袖,但經過美麗島事件之後,他的形象已完全崩壞。在歷史檔案裡,他就是不折不扣的特務頭子。那天在咖啡店談笑風生的記憶不時浮現,我感受到人權工作者的真摯情感,也感受到台灣歷史是多麼荒謬而荒蕪。
2
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假釋出獄的消息傳來時,是在一九八四年春天。他們的刑期不像八位領導人那麼長,其中有些人是《美麗島》雜誌的工作人員或支持者,有些人則是捲入藏匿施明德案件中的協助者。最早出獄的兩位作家是王拓與楊青矗,似乎為台灣社會帶來了騷動。他們當初被捕時,引起國際人權組織的廣泛議論,特別是作家身分受到判刑,更加暴露戒嚴體制的違背人性。對於西方先進的民主國家,作家永遠都是言論自由的象徵,也是評斷一個社會是否開放的最高準則。王拓、楊青矗的被捕,顯然釋出了非常豐富的政治意義。畢竟他們是鄉土文學運動的健筆,他們作品中形塑的社會底層人物,強烈暗示了國民黨所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便是台灣階級壓迫的根源。兩位作家入獄,如果發生在美國或歐洲,必然是受到矚目的嚴重問題。
遠在洛杉磯,聽到他們兩人被釋出獄時,我內心累積許久的壓力,似乎稍稍鬆弛下來。最初南下洛杉磯時,我曾經暗自立下誓願,只要他們被關在牢裡一天,我就繼續投入政治運動。這種祕密誓言是我對自己的承諾,也是對人權信仰的一種實踐。當他們走出牢房時,我緊繃的心彷彿也得到一點點紓解。王拓是基隆八斗子人,他筆下的雨港意象特別鮮明。尤其他的小說《金水嬸》,把現代都會的金錢政治,與鄉下母親的堅守傳統純樸精神,描繪得非常淋漓盡致。而楊青矗是高雄人,在他小說裡所刻畫長期受到剝削的工廠人。兩人的作品彰顯了台灣社會的城鄉差距與階級差距,就像我後來常常說的,鄉土文學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對抗國民黨的文藝政策。通過這樣的政策,當權者可以干涉作家的思考與書寫,也使許多活潑的藝術想像受到黨國的壓制。王拓、楊青矗的小說,彰顯了黨國文學所無法容許的底層人物形象。如果重新閱讀他們的作品,可以發現社會底層其實充滿了暗潮洶湧的憤怒情緒。
春日的洛杉磯陽光,透過玻璃窗照進辦公室,似乎帶著幾分慈悲,幾分憐憫,讓我冰凍的心也稍稍融解。縱然如此,我對於坐在高牆裡的受難人,還是相當牽掛。生存在畸形的年代,便無法避開畸形權力的氾濫。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預告了台灣民主前景的黯淡與危機。戰後以來,從未見證從下而上的民間運動。如果美麗島人士不要受到逮捕,或許一九七○年代的民主運動可以奠下基礎。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在這個基礎上還有更高、更大的空間可以期待。然而不然,戒嚴體制的當權者,無法容忍人民力量的崛起。美麗島事件的爆發,使台灣社會的民主進程至少慢了十年。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卻未看見權力在握者有任何反省的能力。
隔著海洋瞭望台灣時,我看見戰後新世代巍然站起。這種世代交替的事實,使我更加相信,民主從來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些走向街頭的年輕人,正是我的世代。如果我在現場,必然也涉身其中。一個傷感的、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面對險境時,反而湧出更強大的勇氣。在年少歲月,自己的性格未曾如此強悍。必須離開海島之後,展開生命孤獨的航行時,才開始與各種不同形式的險惡遭逢。開始放下身段,四處打工之際,才慢慢體會了人性的真實。為了生存下去,彷彿在陌生的海域搏鬥,慢慢鍛鍊暗藏內心的意志。赤裸裸的政治事件,確實給我太多的人格教育,曾經是那樣脆弱的性格,在遠洋航行時逐漸鑄造了無悔的意志。這樣的人格改造,跨過一九八○年的考驗後,一個全新的靈魂已經在我體內形塑而成。我的浪漫情懷並未喪失,只是比起從前還更勇於追求遙遠的理想。
一旦涉入冰涼的水域之後,生命已經是全盤兩樣。獲悉島上的年輕世代走上街頭時,縱然不在現場,也可感覺自己的血液正在燃燒,毫無來由地,我對自己的缺席,感到遺憾,甚至帶著一點罪惡感。捧讀台灣黨外雜誌,年輕世代的政論,我頗覺驕傲,恨不能與他們站在同一行列裡。很難想像他們的行動其實比美麗島事件的遊行者還更激進,藉由文字所呈現出來的思想狀態,與前行代比較起來毫不遜色,那是波瀾壯闊的年代,似乎沒有什麼可以抵擋,威權掌控者可以囚禁美麗島人士,卻關不住年輕世代的激進思考。一個全新時期儼然到來,尤其看見黨外雜誌開始出現兩條路線的辯論,一是選擇議會路線,一是堅持群眾路線,這種分歧意味著更成熟的政治運動即將到來。
在週報辦公室與許信良討論黨外運動的分歧時,他說兩條路線都不能偏廢。畢竟台灣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任何可以爭取民主制度的方式都應該嘗試。他這樣說時,讓我不期然想起愛爾蘭的獨立運動。一九二二年宣告獨立之前,愛爾蘭政治運動也同樣分成兩派,一是議會派,一是革命派,當時的現代詩人葉慈也捲入這個革命浪潮裡,身為詩人,他其實跟兩派的成員都保持密切聯繫。如果愛爾蘭議員在英國議會提出和平改革,而遭到否決時,愛爾蘭革命軍便開始進行各種暴力活動。議會路線與群眾路線的交互運用,終於使愛爾蘭完成了獨立的使命。我也同意許信良的說法,相信台灣黨外運動的兩條路線,應該可以並行不悖。
立法委員的改選,在一九八三年宣告恢復,美麗島受難人的家屬,方素敏、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都在選舉中獲勝。在洛杉磯接獲這個消息時,整個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都感到非常興奮。他們的夫婿與兄長身陷牢獄之際,受傷的台灣選民,決心以選票來答覆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這算美麗島事件平反運動的起點,這群代夫出征的女性,在高票當選之際,已經撫慰了多少哭泣的心靈。面對這樣的結果,許信良更加堅定主張選舉路線。他所信仰的合法改革,受到海外政治團體的批判,認為這種主張等於承認國民黨的合法統治。許多堅持革命路線的讀者,紛紛以退報的行動來杯葛這份週報。
從創刊以來,維持這份週報的經濟來源,並不純然是依賴讀者的支持。背後其實有特定人士提供金援,遠在日本的史明便是其中一位。許信良與史明結盟,成立了聯合陣線。為的是要使這份報紙的影響力可以擴張。當時史明主張革命的文字,也在這份週報連載。從報紙內容來看,似乎出現了兩條路線。一個是許信良強調的選舉策略,一個是史明所揭示的革命主張。這兩條路線並置在一起,常常引來讀者的訕笑。這不免使我覺得尷尬,畢竟我從未參加聯合陣線的組織。在週報工作,完全是為了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進行批判,而這正好彰顯了我個人的局限。我深知自己並不適合參加團體生活,總覺得自己所信奉的自由主義會受到傷害或限制。畢竟身為文學創作者與學術研究者,我傾向於獨來獨往的脾性。當這份週報成為組織性的宣傳機構時,我漸漸感到遲疑。
美麗島人士陸續出獄時,我強烈感受到緊繃的情緒逐漸弛緩下來。正如最初對自己所做的承諾,只要美麗島人士未能出獄,我便堅守在那不斷書寫的批判位置。三年來,埋在血液裡的那股憤怒,是我投入政治浪潮的原始動力。當台灣的民主運動逐漸恢復元氣,美麗島受難人家屬也次第當選民意代表。鬱積在體內的憤懣,似乎也開始分解。許多信息告訴我,台灣民主運動的生命力未嘗稍止。猶如涓涓細流從石縫中滲出,點點滴滴又慢慢匯聚,那蜿蜒的躍動,我在千里外也可感知。就在那個春天,生命又好像到達一個路口,是否繼續擔任這個週報的主編。我對這份週報寄託著太多的感情,沒有三年來的不停書寫,也許我無法走出美麗島事件的夢魘。而我知道,一個分合的路口再次隱隱出現於眼前。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深淵與火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深淵與火
時代是那樣絕情,唯一能夠信任的,是我蒼涼的靈魂。
生存在畸形的年代,無法避開畸形權力的氾濫。
美麗島之後,隔著海洋瞭望台灣,戰後新世代巍然站起。
在洛杉磯三年多的歲月,赤裸裸的政治事件,讓浪漫主義者為了生存,生命之旅完全改變航線──
他借由書寫這救贖的過程,跨過人格重塑的一道閘門。
威權掌控者可以囚禁美麗島人士,卻關不住年輕世代的激進思考。
而新生代的視野與氣度,也與前十年的黨外運動有了區隔。
這趟回鄉的旅程注定孤寂,荒涼,苦澀,
但無論多麼艱難,都必須單獨走下去。
接續《革命與詩》後,陳芳明另一抒情之作《深淵與火》,
在最苦悶的時刻裡,終結流亡,不再缺席。
作者簡介: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著作等身,包括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革命與詩》;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晚秋夜讀》、《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星遲夜讀》、《晚秋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灣新文學史》,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學者的研究典範。獲二○一六台灣文學金典獎。
TOP
章節試閱
牢門打開時
1
春天來時,洛杉磯又回到燦爛的季節。行道樹變得更綠,路邊人家的前院花圃也盛放著豔麗花朵。加州罌粟花(California poppy)開在矮矮的圍籬周邊,燦爛地反射著豔陽光線。編輯部辦公室後面的酪梨樹(avocado),已是果實纍纍。那是加州特有的產物,在西雅圖未曾見過如此碩大的果物。微風襲來,夾帶著南國的悶熱。枝葉徐徐搖晃,唯獨那果實不動如山。那天下午到達辦公室,發現艾琳達正在攀爬枝幹之間。常常來辦公室協助的艾琳達,從聖地牙哥北上夜宿在辦公室。她大概是我所見過,使用流利中國話的洋人。她那時是史丹佛大學社...
1
春天來時,洛杉磯又回到燦爛的季節。行道樹變得更綠,路邊人家的前院花圃也盛放著豔麗花朵。加州罌粟花(California poppy)開在矮矮的圍籬周邊,燦爛地反射著豔陽光線。編輯部辦公室後面的酪梨樹(avocado),已是果實纍纍。那是加州特有的產物,在西雅圖未曾見過如此碩大的果物。微風襲來,夾帶著南國的悶熱。枝葉徐徐搖晃,唯獨那果實不動如山。那天下午到達辦公室,發現艾琳達正在攀爬枝幹之間。常常來辦公室協助的艾琳達,從聖地牙哥北上夜宿在辦公室。她大概是我所見過,使用流利中國話的洋人。她那時是史丹佛大學社...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在一切被吞噬之前
每次完成一篇回憶散文,就覺得自己更接近漂浪歲月的尾聲。我希望這系列的回憶可以得到安頓,然後不用再回頭再瞭望。只要回到浮沉的一九八○年代,總會覺得死神的羽翼俯臨在我眼前。那十年的移動速度,特別遲疑而緩慢,常常浮現絕望的時刻,總覺得自己註定在遠離家鄉的海岸老死,不可能再踏上海島的土壤。那種絕望,彷彿是判刑定讞的死囚,隻身承受萬劫不復的命運。每次想到,我可能會被掩埋在陌生的土地,真的很不甘心,我果然是遭到命運刻意遺棄的人嗎?
那時並不知道島上的邪惡政治體制,終於有一天會宣告終結。每次...
每次完成一篇回憶散文,就覺得自己更接近漂浪歲月的尾聲。我希望這系列的回憶可以得到安頓,然後不用再回頭再瞭望。只要回到浮沉的一九八○年代,總會覺得死神的羽翼俯臨在我眼前。那十年的移動速度,特別遲疑而緩慢,常常浮現絕望的時刻,總覺得自己註定在遠離家鄉的海岸老死,不可能再踏上海島的土壤。那種絕望,彷彿是判刑定讞的死囚,隻身承受萬劫不復的命運。每次想到,我可能會被掩埋在陌生的土地,真的很不甘心,我果然是遭到命運刻意遺棄的人嗎?
那時並不知道島上的邪惡政治體制,終於有一天會宣告終結。每次...
»看全部
TOP
目錄
自序
在一切被吞噬之前
牢門打開時
極冷與極熱
告別洛杉磯
豔陽照在柏克萊
紐約.一九八五
城市之光
雨落在唐人街
回歸讀詩的歲月
在左翼的歷史記憶裡
旅行到遙遠仙台
東京人行道的銀杏
江南事件的陰影下
坐在後院楓樹下
卸下枷鎖的海島
沒有國籍的人
為歷史造像
史丹佛大學的教堂
哭泣的雨夜花
穿越歷史的門檻
眺望維多利亞海港
在陌生的歷史水域
與鄭南榕的相見
十五年後,鮭魚返鄉
悼亡之旅
在一切被吞噬之前
牢門打開時
極冷與極熱
告別洛杉磯
豔陽照在柏克萊
紐約.一九八五
城市之光
雨落在唐人街
回歸讀詩的歲月
在左翼的歷史記憶裡
旅行到遙遠仙台
東京人行道的銀杏
江南事件的陰影下
坐在後院楓樹下
卸下枷鎖的海島
沒有國籍的人
為歷史造像
史丹佛大學的教堂
哭泣的雨夜花
穿越歷史的門檻
眺望維多利亞海港
在陌生的歷史水域
與鄭南榕的相見
十五年後,鮭魚返鄉
悼亡之旅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芳明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10-24 ISBN/ISSN:978986387260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4頁 開數:17*23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