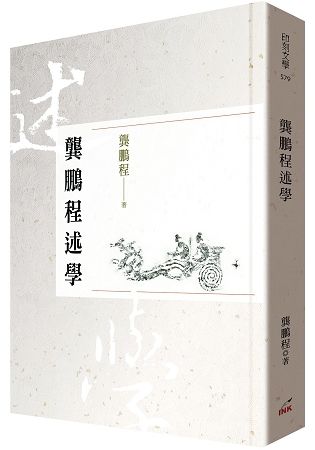緒言
一、緣起
廿年前寫《四十自述》,副題即是「鵬程問道」。預擬六十作《述學》、八十作《閱世》。若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一百歲時再來寫《寄言》。那時恩怨未了,敵友俱亡,或許會寫得更酣暢些,此時便只能述學。
更早的緣由,可追遡到宋代。紹興廿四年進士考試,問「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考官巴結秦檜,把他孫子塤擢為榜首,張孝祥第二。高宗親自改為孝祥第一、塤第三。同榜還有范成大、楊萬里、虞允文等。故事有趣,題目尤其好,值得再做一次回答。以下就算是我的答卷。
二、性質
述學,原是清代汪容甫先生的書名。但它體例不純,只是文章的雜湊,我則是真要述學的。
人生在世,既非貓狗,自當力學。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生命的歷程與內容,事實上也就是學的內容與經歷,所以值得盤點一番。這倒不是因我以學者身分謀食的緣故。夫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除了修養不好,還常亂講話之外,我大抵即是依此活著的。
生活即是為學,學習所得,便是我生命的具體存在狀況。故為學不是知識上的事,乃是關乎人之存在的。人之所以為人,且是這樣一個人,即與其學有關。學君子者為君子、學貓狗者為貓狗。我於此有些許體驗,不妨說說。故我述學,談學問,跟別人不一樣,談的是生命史。
這裡當然仍有主從、有虛實。看起來是以述學方式在講我的生命歷程,然重點在學問而不在我。
我,不過四大假合,終歸塵土;龔鵬程三字,即是假名,是偶然用著的符號,呼我為牛則為牛,呼我為馬則為馬。可是萬法皆空而業不空,人都會死,而他所造、所成、所立之業卻可能存續下去。所以說立功立德立言是三不朽。人終朽而業自有其生命,雖我造立,匪我思存。由歷程看,我主它從;由歷史看,它實我虛。故本書又是以我生命為線索來敘述的當代學術史(雖僅是它的一小片剪影)。
三、特點
一個人的學問若值得敘述,定有其特點。我的特點是什麼呢?
做學問的人,形態各異,或尊德性、或道問學,或尋理趣、或重實用,我卻是合一的。本於性氣,參酌古今中外文獻、聖哲言語以定是非,故非修行與學術之兩歧;所得所是,作用於生活中,故又是行解之互證。此古人所難,當世亦無同類者。
我寫自述,也與一般自傳不同,屬於自我反省的作業。要把馳驟的蹄痕仔細勘察一番,以便再騁逸足。故自述乃為己之學的一部分,非宣傳、非獵名、非討罵,亦不求知音。
四、體例
用來檢核我之所學的框架,是孔門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不採取逐年講故事的辦法。
過去馬一浮先生以六藝攝一切學術,不但將中國傳統學問都歸入六藝系統,就連西方學術也是。
其說有人贊、有人疑、有人嗤,但我以為是對的。中國學問均出於六經,本不需再做什麼說明;外國學問,大體亦可有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等分類,故也可以六藝之學攝之或通之。
若不用此框架,另用三教、四部、儒道佛文俠五大傳統等等,當然也可以。但這些年我在大陸重建並活化了一批孔廟與書院,杭州馬一浮紀念館即其中之一,故不妨即以這個框架述學。
何況,我的學問,根本於經學;後來的發展,漸包四部而貫九流,又與現代後現代諸思潮相激盪相參會,走向正與整個民族文化相似。我的生命,呈現著整體民族文化的內涵與發展進程,便是一大特色。採用這個論述框架,恰好可以把這一點體現出來。
同時,質疑經學不能開展出現代學術的人可多啦,我這活生生的例子恰好也可作個反證。
分由詩書禮樂易春秋六個方面說,亦有方便之處。因為道通為一,全體大用,若不分解地說,終會顯得渾淪,難以把搦,故不能不如此。但生命畢竟是整全的,所以六方面自有相通相涵之處。碰到這種情況,我輒參考史家「互著」「別裁」之法處理之。雖然如此,重重複複、囉哩八唆之病也不可免。亂世文章,無法雅潔,識者諒之。
五、內容
寫史的人,不可能什麼都寫,許多陳芝麻爛穀子也無需寫。我所寫,一是師友淵源,說明我這些學問是怎麼來的。二是發展因緣,敘述學問在學界的規範與傳統中、社會政經文化環境互動中,又怎麼變生發展,有什麼價值、可起什麼作用。
講時,雖不免感憤時世、譏訶時賢,但內中其實充滿感激。我荷師友之厚恩,自不用說(這書一大目的,即是紀念他們,頗有感懷傷逝之處);這變動且混亂的時代,更讓我學到了許多。歷劫之深,佛陀有未及知者;極世之變,老聃孔子也有所不逮,故特能激刺心魂、濬發思慮。《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此之謂也。若說將來對好學深思的青年可有什麼啟發,願望太奢,則吾豈敢?
-----------------
第一卷 詩
我出生、成長於臺灣。
祖籍江西吉安。當地文風及祖上的事,均無所知,只能由父親那裡聽受而來。謂是遠祖龔遂嘗守渤海,治績甚好,被寫進了《漢書.循吏傳》。我們這一支則是愈公所傳。愈公於唐代任金紫光祿大夫、大傅上柱國越國公,所以我們總祠彞倫堂(建於明正德年間,寬五十六米,軒敞弘闊)前面的牌坊,榜書大字曰:「上柱國第」。
到宋朝天禧年間,鍹公遷居金陵。傳十四世官德公任鳳陽指揮,遂由鳳陽遷江西吉安南街。其四世理公於明代又徙吉安值夏永樂村開基。村有永樂寺,故名。始建於天寶六年,永樂九年重建。該地有許多都是由北方遷來的,如旁邊渼陂村即自西安來,杜甫《秋興》之八:「昆吾禦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即指其地。遷來後仍名渼陂,據說祠堂跟我們村用的是同一張圖紙,故格局建式相近(南遷宗族仍用舊地名是很常見的現象,如劉勰他們家由山東莒縣東莞遷到京口。《梁書》就仍說他是東莞莒人,其實當時東莞只是僑設之地,非山東原址)。
至今我族前後八房。前三房是三畏堂傳的崇雅堂、懷德堂、五聚堂。後五房是徽猷堂傳的天恩堂、六和堂、思親堂、聚和堂、作述堂。懷德堂下則因人多,分為四支:景公、聘公、餘慶、貽德,各有祠堂。祠堂大大小小近二十座。我即屬於貽德堂。
吉安在宋元明清時期,文風鼎盛,是出歐陽修、文天祥的地方,邦人頗以此自勵,自許為「文章節義之鄉」。書院以白鷺洲最著名,建於南宋淳祐元年,與廬山的白鹿洞、鉛山的鵝湖、南昌的豫章齊名。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六賢,乃程朱學脈。詩風則尤勝,江西最早的地域性集子,就是元代廬陵鳳林書院編的《名儒草堂詩餘》,在全國是領先的。至明朝,王陽明曾任廬陵知縣,
其學問主要也在吉安這一帶發展,稱為「江右王學」。當時我鄉青原山講會之盛,震動天下。山乃禪宗七祖青原行思的道場。禪門五家,曹洞、雲門、法眼皆出於此。潙仰、臨濟雖出於南嶽懷讓,而其實也在吉安宜春這一帶發展起來,故為天下禪門宗源。陽明也在此建有書院(二○○八年我回鄉勘址,倡議重建,現已竣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晚年出家為僧,稱藥地大師,亦住在這裡。
儒家佛家的流風餘沫,到父親他們這一輩遺存不輟。宗族自辦的書塾,大小祠堂裡都有。總祠邊還有一座元升書院,後有一惜字亭。清末廢除科舉以後,原先的秀才舉人優貢拔貢雖無緣仕進,仍以教書為事,深受族人尊敬。祠祭燕享,都要先禮請這些「斯文前輩」。排序不尊尊、不親親,而重文重教。族中若有糾紛,也以斯文先生的意見為斷。
後來族兄祖亮於民國十六年由北京大學畢業回來,配合時代新潮,便把宗塾改為學校了。他自己擔任校長,推行新式教育,名為新生小學,後來又辦了同盟中學。學生讀書都免費。開了國文、算術、史地等學科,我父即是開始接受新式教育的這一批。
但新也離不開舊,仍由《三字經》、《百家姓》、《四書》讀起。許多經典,垂老仍能背誦,可見當時教育之效果,迥非今日所能比。其間詳情,他老人家寫的自傳《花甲憶舊集》可以參看,文筆活跳,遠勝於我。他還能書能畫,擅長拉二胡、唱京戲。武術方面,老家流行字門拳,他則尚有青幫的淵源(在台中做生意時,有流氓來砸場。我見他把來人打翻了,用板凳卡在陰溝裡)。
但他後來輾轉於鄉保、軍旅、商賈、遊俠之間。浮海來臺後,時世已不容他治學了,僅存一點文化嚮往,只能在開的餐館,如「六一居」「斯為美」等名稱上表現出來(六一是歐陽修的號,先王之道斯為美,見於《論語》)。故轉而期望我能繩武門風。教我讀書、寫字、打拳,開蒙遂極早。以致我竟然也能如杜甫一般:「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他深知我性躁動、好嬉耍,所以寫了「勤有功,嬉無益」一張紙條貼我桌前,作為座右銘。
但他很快就後悔了,因為我嘗到了閱讀的樂趣,即再也捨不得離開書本子。到戚友家、書店、租書間找書看,或躲進防空洞裡、爬到樹上去看。我那時不過五六歲。怕我走失,他與我媽天天要去覓我,有時氣極了,不免把我痛打一頓。
他又認為書固然要念,可是讀了書而禍國殃民者其實甚多,因此教育子女仍以忠厚傳家為要。
我友周渝,臺北紫藤廬茶館主人,尊翁周德偉是華人圈中最早提倡並譯述海耶克等自由主義思想者。我見過他請趙恆惕先生隸書一幅對聯云:「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我想先父之體會大約類似。英雄回首,固多蒼涼也。
父親去世後,我兄妹組建了「龔立逑先生教育基金會」來紀念他。希望蒼涼的人世仍存有一點希望,我輩家風,也能稍稍潤澤予世界。
我在大陸還有族人兩千餘,兩兄長,從事教育。在臺兄妹五人,也多從事教育,大妹臺紅且曾得過臺灣教育最高獎「師鐸獎」,三妹萍紅也自辦了斯為美教育機構。其實父親他們那時渡海至臺者一十三人,也以教書為多,或參與宗教宏化之事。去年我去深圳演講,大伯乾升之孫來相認,云正在大學任職,其父祖武則已由深大退休(曾任中文系主任、學校書記,著有深圳教育發展史、市志等),令我很感慨。一家人因戰亂分離,彼此甚或不通音問,而居然殊途同歸,都以教育為職事,難道家風傳承還真有冥冥中的聯繫嗎?
乾升伯是南昌中正大學畢業的。入臺後,在高中教了一陣書(後來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胡楚生等人就是他學生,對他的教導很懷念)。但因他早與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大真人義結金蘭,連袂來臺。而政府令天師奉祀道法,如山東孔家之例,以昭「道統」。故他又協助天師建設「嗣漢天師府」,任祕書長,闡揚道化。後來入仕,洊升至考試院銓敘部司長,並以詩文、堪輿、推步、易學有聲於時,可說是能融我家與張氏兩世家之學於一手的人,對我也教誨至深。
天師則是我義父。我小時不好養,或謂天緣太深,故寄在天師座下。
乾升伯登仕之後,續由族兄龔群(期縈)繼續翊助天師。
臺灣深受閩南文化濡染,傳統宗教氣氛濃厚,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幾乎全不受現代化進程斲傷。
這種宗教態勢,是佛道不分、三教合一,而以道法行事為節日宜忌的,故宮廟壇祠遍地。雖皆可算是廣義的天師道,全真系統極為寥落,但內中非常複雜,因為還有許多明清以來流傳的會道門,如齋教、先天道、羅教、瑤池金母、萬國道德會、天德教、天帝教、真空教、三一教等。民間信仰如臨水夫人、三山國王、媽祖、保生大帝、開漳聖王、玄天上帝、關帝恩主公、中壇元帥哪吒、齊天大聖孫悟空、朱熹、諸葛亮、魯班、鬼谷子等,不可勝數。天師往來弘法,遂極辛勞。一九六六年他還整合各道脈,成立了「中華道教總會」,擔任理事長。另還要抽時間去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處開壇建醮,凝聚華人。
期縈哥正是他得力的助手,教界尊稱「龔長老」而不名。他精熟道法,也曾任台灣省佛教會秘書長甚久。天師羽化後,他傳授符籙、推動成立中華道教學院、奔走兩岸,終於鞠躬盡瘁。兩岸第一次道教文化研討會就是我們倆兄弟辦的,四川大學卿希泰先生還將之寫入其《道教史》,視為歷史性大事。中華道教學院也是他和張檉先生拉我去辦的,建立迄今三十年了。
當然這許多方面以後還會談到,這裡只是稍敘家風而已。從前六朝隋唐世家,常以「累代官宦」和「經學禮法傳家」自詡。我們家,仕途並不顯達,文不過大學祭酒、宦不過司長侍郎之類,故我今生也絕了仕進之望,仍從經學上去努力吧。
但治學也非易事,半人半天。須有絕大天資,還得痛加人巧。天資不僅是多少的問題,還有偏向與厚薄,《人物志》所謂金木水火土,或畸於英、或鄰於雄,孔子所謂狂與狷。人巧則除了自己要功夫入密之外,還得借助他人。他人,大的是時世因緣,小的是家風與師友。我的家學大抵如此,不煩縷敘,師友則頭緒甚繁,須要細講。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龔鵬程述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4 |
中國文學總論 |
$ 394 |
Social Sciences |
$ 394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439 |
中文書 |
$ 439 |
中國哲學 |
$ 439 |
Others |
$ 449 |
華文文學研究 |
$ 449 |
文學史 |
$ 449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龔鵬程述學
融貫儒學活化傳統的孔孟傳人
解析孔門六藝於現今社會的必要思索
經書,本是傳統讀書人最基本的文化滋養。
優遊博涉,貫通古今,兼容東西,精深活用,以全面的生命觀照,紮實的治學方理,重新探討孔門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的當代風貌。
龔鵬程認為,治學史就是生命史,而生命是整全的,不可割裂,因此他重通貫、貴整合。從前莊子形容老聃是「古之博大真人」。他不願為某家某派、某領域某學科所限。三教、四部、九流、十家、辭章、義理、考據、經濟,俱要通貫,以生命力綜攝為一。
「生活即是為學,學習所得,便是生命的具體存在狀況。故為學不是知識上的事,乃是關乎人之存在的。人之所以為人,且是這樣一個人,即與其學有關。學君子者為君子、學貓狗者為貓狗。我於此有些體驗,不妨說說。
故我述學,談學問,跟別人不一樣,談的是生命史。
我,不過四大假合,終歸塵土;龔鵬程三字,即是假名,是偶然用著的符號,呼我為牛則為牛,呼我為馬則為馬。可是萬法皆空而業不空,人都會死,而他所造、所成、所立之業卻可能存續下去。所以說立功立德立言是三不朽。人終朽而業自有其生命,雖我造立,匪我思存。由歷程看,我主它從;由歷史看,它實我虛。故本書又是以我生命為線索來敘述的當代學術史。」
詩:學問與生命是合起來的。詩若成學,人即成詩。
書:文學書寫活動不但關連於道,關連於宇宙秩序與終極真理,也關連著歷史的開展。
禮:是近代被汙名化最嚴重的一個字。
樂:樂並不只是樂音演奏,乃是以音樂為中心,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
易:孔子引易說易,謂占人與醫生都須具有恆德。何以故?他們面對的是命運、是死生,這都是最多變化、最顯飄忽的;若無恆德,如何貞定?
春秋:歷史並未完成,須待人投入,與之交談,乃能彰顯。
作者簡介:
龔鵬程
現為北京大學教授。
祖籍江西,1956年生於台灣,博士、教授。曾任報社主筆、書局總編、政府公職人員等等,創辦過三所大學、一些研究機構。兼通三教,博涉九流。著作六十餘種,主編圖書數百種。以弘揚中華文化為職志,現在大陸講學。曾任南華大學、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創校校長;中華道教學院副院長;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等。
曾獲獎勵及榮譽稱號:
1.中山文藝獎:文學理論類(1983)
2.教材改進甲等獎(1987,教育部)
3.中興文藝獎章(1991,中興文藝協會)
4.傑出研究獎(1991,行政院)
5.淡江金鷹獎(1995)
主要學術成就及著作:
已出版論著七十餘種。
包括《文學散步》、《文學與美學》、《美學在台灣的發展》、《書藝叢談》、《讀詩隅記》、《中國文學批評史論》、《俠的精神文化史論》、《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國學入門》、《龔鵬程四十自述》、《龔鵬程年度學思報告》等。
TOP
章節試閱
緒言
一、緣起
廿年前寫《四十自述》,副題即是「鵬程問道」。預擬六十作《述學》、八十作《閱世》。若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一百歲時再來寫《寄言》。那時恩怨未了,敵友俱亡,或許會寫得更酣暢些,此時便只能述學。
更早的緣由,可追遡到宋代。紹興廿四年進士考試,問「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考官巴結秦檜,把他孫子塤擢為榜首,張孝祥第二。高宗親自改為孝祥第一、塤第三。同榜還有范成大、楊萬里、虞允文等。故事有趣,題目尤其好,值得再做一次回答。以下就算是我的答卷。
二、性質
述學,原是清代...
一、緣起
廿年前寫《四十自述》,副題即是「鵬程問道」。預擬六十作《述學》、八十作《閱世》。若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一百歲時再來寫《寄言》。那時恩怨未了,敵友俱亡,或許會寫得更酣暢些,此時便只能述學。
更早的緣由,可追遡到宋代。紹興廿四年進士考試,問「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考官巴結秦檜,把他孫子塤擢為榜首,張孝祥第二。高宗親自改為孝祥第一、塤第三。同榜還有范成大、楊萬里、虞允文等。故事有趣,題目尤其好,值得再做一次回答。以下就算是我的答卷。
二、性質
述學,原是清代...
»看全部
TOP
目錄
緒言
行年
第一卷、詩
第一章 學詩紀事
第二章 詩學述要
第二卷、書
第一章 文字逸旅
第二章 書文書藝
第三卷、禮
第四卷、樂
第一章 復興樂教
第二章 人文美學
第五卷、易
第六卷、春秋
第一章 史學
第二章 詮釋
第三章 正名
第四章 經世
第五章 未來
行年
第一卷、詩
第一章 學詩紀事
第二章 詩學述要
第二卷、書
第一章 文字逸旅
第二章 書文書藝
第三卷、禮
第四卷、樂
第一章 復興樂教
第二章 人文美學
第五卷、易
第六卷、春秋
第一章 史學
第二章 詮釋
第三章 正名
第四章 經世
第五章 未來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龔鵬程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11-02 ISBN/ISSN:978986387269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72頁 開數:17*23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