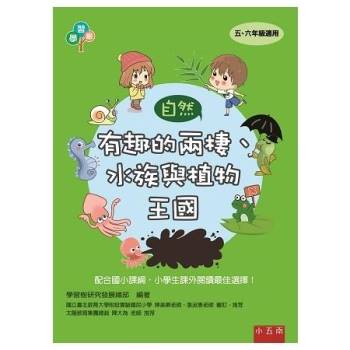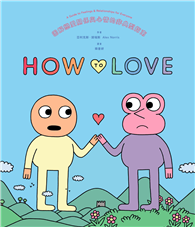不容錯過的王氏散文經典,
王鼎鈞文學夢幻逸品一次典藏!
烽火遍布的大地上,
彌漫蓋天的煙硝裡,
曾經有我們斑斕的青春顏色……
本書內容時序上銜接在《碎琉璃》之後,描寫鼎公離家前往大後方流亡學校求學時的經歷,校園生活的往事,以及遷校流屣路途中的所見所聞。
在文武合一的流亡學校裡,既是求學,也像從軍。鼎公留心地觀察生活裡所遇見各式各樣的人物;號兵、教官、難民、壯丁、保長、山村鄉民……並一一將其凝鑄成一篇篇帶有傳奇色彩的生動篇章。本書恰是藉由鮮活的人物,讓讀者對於那動盪時代下的校園與社會,能更加感同身受。
王鼎鈞散文經典復刻出版
王氏文學夢幻逸品一次典藏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山裡山外的圖書 |
 |
山裡山外【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出版日期:2019-06-2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00 |
中文現代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現代散文 |
$ 342 |
現代散文 |
$ 342 |
文學作品 |
$ 342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山裡山外
內容簡介
序
自序
這本書本來沒有序,現在發現序言必不可少。
書前有序,等於一個陌生人來到你家先拿出一封介紹信。
●
《山裡山外》的主要人物,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
時至今日,「流亡學生」這個名詞需要解釋一下。當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軍隊大舉侵華,占領中國廣大的土地。在日軍占領區(當時稱為淪陷區),日本改變了教育的精神和課程內容以配合侵略,許多青年不肯進入這樣的學校,冒險穿過封鎖線到後方流亡,即所謂流亡學生。在廣大的後方有很多專設的學校收容他們,這種學校常為了戰局變化而游動遷移,被稱為流亡學校。
《山裡山外》就是以這樣的時代和環境為背景寫成的。
●
筆者是因為做「流亡學生」而少小離家的,流亡期間,歷經匱乏殘破的種種場景。後來年齡增長,閱世漸深,回首前塵,發現了畫面之瑰麗奇偉。
那些流亡學生,最小的只有十五、六歲,腋毛初生,夜間尿床的習慣未改,竟也辭枝離柯,飄泊在兵凶戰危的邊緣。他們的父母是怎樣下了這麼大的決心呢?
那些流亡學生,有些來自富商巨紳之家,既來之後,蒼白慘綠的青年,立刻剃光頭髮,穿上有蝨子帶汗臭的軍裝,血色豔麗的大姑娘,立刻脫下絲襪,換上能磨出血泡來的草鞋。他們又是怎樣下了這麼大的決心呢?
當時,整個大後方的門戶為流亡學生打開,任何機關都會為你提供你需要的消息,任何家庭都可以接待你一宿一餐,從沒有人向你要證件,沒有人卑視你是乞丐,懷疑你是間諜。
那時,社會又怎會有如此的坦蕩寬容呢!
●
據我所知,流亡學生是一群夢遊的人,殺風景的是,周圍有許多精於測算長於透視的眼睛注視他們。有人設想流亡學生很浪漫,在半飢半寒中行吟大地,那是只看到(或說出)一個層面。
八年抗戰有似一條彈道,有升弧、降弧,最後彈頭落地開花,炸醒了各式各樣的夢,包括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和流亡學生的。身為大氣流中的一塵,流亡學生也走過升弧和降弧。
無論如何,對日抗戰,世界第二次大戰,我們總算躬逢其盛。日軍侵華是中國的大災難,青年人及時接受了這場災難的磨練,卻可以視之為得天獨厚,不管後來造化怎樣弄人,都不能奪去我們的收穫。
彈頭落地也能成為跳彈,重新創造一個升弧。
●
我中年以前崇拜英雄,中年以後把感情交給無名的蒼頭眾生。所以致此,是因為我發現了「英雄不仁,以群眾為芻狗」。我不能控制情感的轉移,我的機遇、處境、文學旨趣都起了變化。
我們那群流亡學生都是天地預設的小人物。「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靈數十年。」數十年音訊斷絕,他們的遭際常使我驚疑憂念。如果一顆隕星沉落了使人震撼,那麼滿河繁星流瀉一空又何以堪?
不僅此也,我雖在鄉鎮生長,對農村農人卻甚陌生,對土地亦不親切。戰時流亡,深入農村,住在農家,偶爾也接觸農事,受農人的啟發、感動,鑄印了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抗戰八年,實在是農民犧牲最大,貢獻最多,軍人是血肉長城,其兵源也大半是農家子弟。他們的形象和我的意念永遠連結。流亡期間,跋山涉水,風塵僕僕,和大地有了親密的關係,祖國大地,我一寸一寸的看過,一縷一縷的數過,相逢不易,再見為難,連牛蹄坑印裡的積水都美麗,地上飄過的一片雲影都是永恆的。我的家國情懷這才牢不可破。
做流亡學生擴大了我關懷的層面,這份關懷,多年以來是我精神上的鬱結,紓解之道,對我來說只有寫作。有一次(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和一位電影導演同赴基隆演講,事後又同乘一輛吉普回台北,路上談天,才知道彼此都曾是流亡學生。我們在車中同唱當年的歌曲,淚眼相看,彼此都說要用流亡學生做題材完成一部作品。那時已有人聽不懂我們唱的歌。那時已有人說,這一代年輕人沒有抗戰經驗,對抗戰的題材沒有興趣。那時我就說,如果欣賞作品以重溫自己的生活經驗為限,世上將沒有幾本小說幾部電影可看。我們正要從作品中看到別人的生活,看那些與自己不同的生活,以增進我們對人的了解與諒解,擴大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的境界。時至今日,又是多少年過去,我的意見沒有改變―別人的意見似乎也沒有改變。
●
《山裡山外》在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由台北的洪範書店出版,最後一章寫得很差,常引以為憾。今日海峽兩岸已打破隔絕,故人的消息陸續傳來,得以重新回顧當年的甘苦,當年懵然不知或知而未詳的事件也得以補充。現在把原書最後一章刪去,另寫三章增入,少一缺陷,了一心願。書成,商得洪範同意,由我自己繼續印行。
無論如何我得感謝當年創辦流亡中學的人,他提供機會使我們有書可讀。事無全美,讀書便佳。經師易得,人師難求,經中自有人師。估計沿著淪陷區邊緣設立的數十所中學,吸納造就了大約二十萬青年。在非常時期、非常地區創辦這樣非常的學校,定非尋常人物,事到如今,那些人一世勛業皆成鏡花水月,惟有「偶爾」辦了這麼個學校,是不可磨滅的一大功德。
俱往矣,但是你做的好事,人們永遠記得;你做的壞事,人們也會永遠記得。然而本書並不是某人某人的傳記,也不是某一學校的實錄,它的內容有許多來源,作者再加以綜合變奏,以納入文學的形式。它努力擴大了現實,也隱藏了現實。書中人物只能作「甄士隱」看。來,我們何必穿鑿附會?我們一同激濁揚清。
這本書本來沒有序,現在發現序言必不可少。
書前有序,等於一個陌生人來到你家先拿出一封介紹信。
●
《山裡山外》的主要人物,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
時至今日,「流亡學生」這個名詞需要解釋一下。當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軍隊大舉侵華,占領中國廣大的土地。在日軍占領區(當時稱為淪陷區),日本改變了教育的精神和課程內容以配合侵略,許多青年不肯進入這樣的學校,冒險穿過封鎖線到後方流亡,即所謂流亡學生。在廣大的後方有很多專設的學校收容他們,這種學校常為了戰局變化而游動遷移,被稱為流亡學校。
《山裡山外》就是以這樣的時代和環境為背景寫成的。
●
筆者是因為做「流亡學生」而少小離家的,流亡期間,歷經匱乏殘破的種種場景。後來年齡增長,閱世漸深,回首前塵,發現了畫面之瑰麗奇偉。
那些流亡學生,最小的只有十五、六歲,腋毛初生,夜間尿床的習慣未改,竟也辭枝離柯,飄泊在兵凶戰危的邊緣。他們的父母是怎樣下了這麼大的決心呢?
那些流亡學生,有些來自富商巨紳之家,既來之後,蒼白慘綠的青年,立刻剃光頭髮,穿上有蝨子帶汗臭的軍裝,血色豔麗的大姑娘,立刻脫下絲襪,換上能磨出血泡來的草鞋。他們又是怎樣下了這麼大的決心呢?
當時,整個大後方的門戶為流亡學生打開,任何機關都會為你提供你需要的消息,任何家庭都可以接待你一宿一餐,從沒有人向你要證件,沒有人卑視你是乞丐,懷疑你是間諜。
那時,社會又怎會有如此的坦蕩寬容呢!
●
據我所知,流亡學生是一群夢遊的人,殺風景的是,周圍有許多精於測算長於透視的眼睛注視他們。有人設想流亡學生很浪漫,在半飢半寒中行吟大地,那是只看到(或說出)一個層面。
八年抗戰有似一條彈道,有升弧、降弧,最後彈頭落地開花,炸醒了各式各樣的夢,包括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和流亡學生的。身為大氣流中的一塵,流亡學生也走過升弧和降弧。
無論如何,對日抗戰,世界第二次大戰,我們總算躬逢其盛。日軍侵華是中國的大災難,青年人及時接受了這場災難的磨練,卻可以視之為得天獨厚,不管後來造化怎樣弄人,都不能奪去我們的收穫。
彈頭落地也能成為跳彈,重新創造一個升弧。
●
我中年以前崇拜英雄,中年以後把感情交給無名的蒼頭眾生。所以致此,是因為我發現了「英雄不仁,以群眾為芻狗」。我不能控制情感的轉移,我的機遇、處境、文學旨趣都起了變化。
我們那群流亡學生都是天地預設的小人物。「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靈數十年。」數十年音訊斷絕,他們的遭際常使我驚疑憂念。如果一顆隕星沉落了使人震撼,那麼滿河繁星流瀉一空又何以堪?
不僅此也,我雖在鄉鎮生長,對農村農人卻甚陌生,對土地亦不親切。戰時流亡,深入農村,住在農家,偶爾也接觸農事,受農人的啟發、感動,鑄印了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抗戰八年,實在是農民犧牲最大,貢獻最多,軍人是血肉長城,其兵源也大半是農家子弟。他們的形象和我的意念永遠連結。流亡期間,跋山涉水,風塵僕僕,和大地有了親密的關係,祖國大地,我一寸一寸的看過,一縷一縷的數過,相逢不易,再見為難,連牛蹄坑印裡的積水都美麗,地上飄過的一片雲影都是永恆的。我的家國情懷這才牢不可破。
做流亡學生擴大了我關懷的層面,這份關懷,多年以來是我精神上的鬱結,紓解之道,對我來說只有寫作。有一次(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和一位電影導演同赴基隆演講,事後又同乘一輛吉普回台北,路上談天,才知道彼此都曾是流亡學生。我們在車中同唱當年的歌曲,淚眼相看,彼此都說要用流亡學生做題材完成一部作品。那時已有人聽不懂我們唱的歌。那時已有人說,這一代年輕人沒有抗戰經驗,對抗戰的題材沒有興趣。那時我就說,如果欣賞作品以重溫自己的生活經驗為限,世上將沒有幾本小說幾部電影可看。我們正要從作品中看到別人的生活,看那些與自己不同的生活,以增進我們對人的了解與諒解,擴大自己的視野,提高自己的境界。時至今日,又是多少年過去,我的意見沒有改變―別人的意見似乎也沒有改變。
●
《山裡山外》在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由台北的洪範書店出版,最後一章寫得很差,常引以為憾。今日海峽兩岸已打破隔絕,故人的消息陸續傳來,得以重新回顧當年的甘苦,當年懵然不知或知而未詳的事件也得以補充。現在把原書最後一章刪去,另寫三章增入,少一缺陷,了一心願。書成,商得洪範同意,由我自己繼續印行。
無論如何我得感謝當年創辦流亡中學的人,他提供機會使我們有書可讀。事無全美,讀書便佳。經師易得,人師難求,經中自有人師。估計沿著淪陷區邊緣設立的數十所中學,吸納造就了大約二十萬青年。在非常時期、非常地區創辦這樣非常的學校,定非尋常人物,事到如今,那些人一世勛業皆成鏡花水月,惟有「偶爾」辦了這麼個學校,是不可磨滅的一大功德。
俱往矣,但是你做的好事,人們永遠記得;你做的壞事,人們也會永遠記得。然而本書並不是某人某人的傳記,也不是某一學校的實錄,它的內容有許多來源,作者再加以綜合變奏,以納入文學的形式。它努力擴大了現實,也隱藏了現實。書中人物只能作「甄士隱」看。來,我們何必穿鑿附會?我們一同激濁揚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