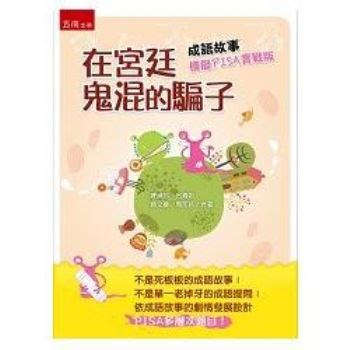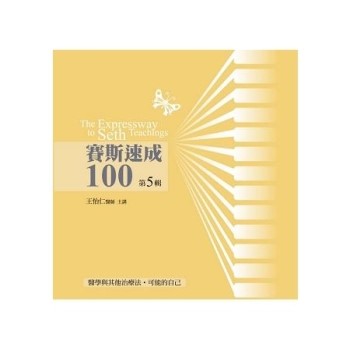致敬 七等生
超越時代的前行者
他的創作歷程示現了幻譎奇偉的生命之歌
「當他離開她時,才開始瞭解生活的重要和肉體的苦痛,迫不得已把一切理想世界棄置,自動地套上鎖鍊,壓抑原始與寶貴的自由。」--〈初見曙光〉
一九六二至六五年七等生最早期創作的二十一篇小說,包括首篇發表於《聯合報》副刊的〈失業、撲克、炸魷魚〉,和〈橋〉、〈圍獵〉、〈白馬〉等半年內陸續刊登於聯副的十則短篇。以及〈隱遁的小角色〉、〈讚賞〉、〈來到小鎮的亞茲別〉、〈初見曙光〉等一九六四至六五年發表於《現代文學》的作品。
七等生以獨特新穎的語言節奏,寓言象徵式的美學筆法,揭露現實的虛妄與心靈的困局,他自述:「把文學視為生命求知探討的手段,透過它瞭解人類歷史和世界環境,更真確的是使我們窺見內在的世界。」
失業男子夜間散步去買炸魷魚;高架鐵橋上兩個高中生的比試;獵捕山豬前的爭論;白馬的寓言;黃昏海濱無法挽回的生命……。七等生文學世界中的經典人物,透西、杜黑、劉教員、亞茲別、土給色登場了,徘徊於悲劇的邊緣,正準備進入中心。
作者簡介:
七等生
本名劉武雄,1939-2020。生於苗栗通霄,台北師範藝術科畢業。自1962年首次在《聯合報》發表短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起,共發表124篇小說、137篇散文(含雜記、序文),及56首新詩。1989年重拾畫筆,將創作重心轉向繪畫,於1991、92年舉辦過兩次個展。
1966、67年連獲第一和第二屆台灣文學獎。1976年獲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1983年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約訪美。1985年獲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和吳三連文藝獎。小說作品《沙河悲歌》、〈結婚〉亦曾改拍同名電影、電視劇等。2010年獲頒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
國內外學者和研究生論文超過百餘篇,允為台灣當代文學最重要作家之一。
章節試閱
失業、撲克、炸魷魚
已經退役半年的透西晚上八句鐘來我的屋宇時我和音樂家正靠在燈盞下的小木方桌玩撲克。我拉一張椅子請他坐下。他說他想到路尾去散步。假如你願意參加打撲克九點鐘我和你到路尾去,我說。透西輸了二十隻火柴根,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再數二十隻火柴根堆到他的面前並且拉他坐下來,他起先拒絕我這樣做,我再三的拉住他,然後他又坐下來。九點半時他又把二十隻輸掉了。他一共輸了四十隻火柴根。
「透西你輸了四十隻火柴根。」我說。
「我知道,八塊錢。為了消遣八塊錢不算多,我現在付給你。」
他和音樂家都是矮身材的男人,但透西有好看的笑容,他斜著肩膀把手伸進褲子袋裡拿錢出來,音樂家說:
「我不願拿你輸給我的兩塊錢。」
「音樂家寧願吃兩個炸魷魚。」我說。
「我寧願吃兩個炸魷魚,我可不必拿你的兩塊錢。」音樂家笑著說。
「好,一起出去吃炸魷魚。」透西說。
「走,音樂家,吃完炸魷魚一起到路尾去。」我說。
「我留在屋子裡,我要彈吉他,回來就帶兩個炸魷魚。」
「音樂家不是合的人。」我說。
「你說什麼?」
「我說音樂家是人類的貴族。」
透西笑出聲來。音樂家有點不高興,他知道我第一次說的不是這樣,他走向壁上掛著的吉他。當他坐下來調琴弦時我和透西從後門走出去。
外面寒風凜冽,海上呈灰黑的顏色,沒有捕魚的好船,海看起來寂寞淒涼,周圍的黑山丘像抱住小市鎮的城牆,這樣的天氣看山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從戲院前面經過,透西表情很沉鬱。
「令人沮喪的電影,只放映一小時又十分鐘的沮喪電影,」他搖著頭說。
我們在炸魷魚攤停住,他問我現在吃還是散步回來再吃,我說散步回來比較好一點。
「這種沮喪破損的電影只有傻子買票進去,臉色灰白的人才建這種沮喪模樣的戲院,這種沮喪的戲院放映沮喪的電影。」
「透西你在說巴巴剌*式的三段論法。」
「這誰都知道,什麼樣的有錢人請什麼樣的建築師,建築什麼樣的戲院。什麼樣的國家產生什麼樣的藝術。只有惠特曼才配寫《草葉集》,只有勞倫斯才能寫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只有奧遜‧威爾斯**才能導演出《大國民》來,你能嗎?你說我們有人能寫出像希梅涅茲的《普拉特羅與我》的這種誠摯文章嗎?我們不能嗎?我們為什麼被教育得這樣空虛呢?誰在阻塞我們心裡的慾望?魔鬼來壟斷一切的進步。還有我們為什麼失業?我們到那裡去籌一筆三千塊錢用信封袋裝著送到人事組長面前,然後當一名臨時雇員,三千塊還未賺回又失業了。這是一種欺詐」
「不要談這些,許多人和你一樣失業,山沒有人開墾,山也失業了;晚上海也失業了。」
「妓女沒有男人來嫖,妓女失業了。」我看著他,他在苦笑。
我們走進一條比較熱鬧的街道,透西姨母的女兒站在門前,她微塗著胭脂在小唇上,樣子很可愛。以前我就認識她,但沒有和她談愛。她的日本名字叫阿薩幾,意思是說小東西。我們在她面前停住,她對我們微笑。
「阿薩幾,到路尾去散步,」我說。
「這樣凜冽的寒風,我正出來但不敢向前。」她說。
「到路尾去,然後去吃炸魷魚。」透西說。
「失業的人才到路尾去乾站,喝西北風。」
「去吧,我們雖然失業但是規矩的男人。」我說。
「規矩的男人常失業,規矩的男人常失去女朋友。」
「要走了嗎?阿薩幾,」透西說。
「你有幾塊錢吃炸魷魚?」
「八塊錢,剛才我輸了八塊錢,吃炸魷魚就用這八塊錢。」
路尾在一條黑巷的盡頭,有一處高起的土堆讓失業的人眺望深澳一帶的海洋。有職業黃昏出來散步的人也站在這裡,遊覽的人也站在這裡。現在我和透西和小東西站在這裡。透西注視著煤場一帶的孤零房屋,樣子很沉鬱。小東西顯得很不耐煩,她頻頻地轉動身軀來躲避迎面吹來的強烈寒風。我心想,和她談愛不知是什麼感覺。我從來也沒動過腦筋想跟她談愛。不過我知道和有些女人談愛很令人沮喪的,主要的是她們的脾氣不像一個女人的脾氣。再凶惡的女人我卻不覺討厭,只要她看起來是個十足的女人就好。阿薩幾是個十足的女人,但是屬於小氣脾氣的少女。職業假如能像女人一樣令人產生慾望就完美了。她發覺我在看她。她微笑著然後擺頭去看看透西,她再轉身過來時,我瞪住她的眼睛,她再微笑一次,於是低頭去看自己的腳。
「透西告訴我們兵營的事,」我說。
「他心裡有事時外表像一個詩人。」阿薩幾說。
「我不會作詩,我不是詩人,我也不是個墾山的農夫,上帝也不會承認我是農夫,我沒有多肌肉的手臂來捉緊鋤頭。但假如我能夠作詩,雜誌的編輯肯買我的詩稿我意願當一個詩人。可是他們不會買我的詩稿。在兵營時我是個士兵,現在什麼都不是。」
「不能再在這裡待了,這些風實在夠冷酷。」
「阿薩幾只想吃炸魷魚。」
「男人只想女人。」
「好,現在我們帶小東西去吃炸魷魚。」透西說。
「我不是為了吃炸魷魚才跟你們來的,要吃炸魷魚我自己也能夠去。」
「當然,不過現在我們應該去吃炸魷魚了。」
我們離開那小土堆,走進巷子裡,從剛才來的路走回去。
「阿薩幾妳想嫁給一個怎麼樣的男人?」透西說。
「我還不知道。」
「你想娶怎樣的女人,透西?」我說。
「像阿薩幾這樣的。」
「不要開玩笑,透西。」
「我當然不能娶妳,我們是親戚。不過我要娶像妳這樣的女人。」透西說。「妳會嫁給一個失業的男人嗎?」
「我不知道。」她說。
「一個失業的男人帶女伴去跳舞會遭別人批評。失業的人什麼都必須檢點。撞球場我不能去,醫院開家庭舞會我也不願去,香煙我只吸舊樂園。」
到了炸魷魚攤,透西吩咐小童要六塊炸魷魚,另外用紙包兩塊。我們一起圍著一張小四方桌坐下。
夜色更深了,戲院第三場戲已散場很久,炸魷魚生意很好。我常常去注視阿薩幾,她的小嘴巴嚼魷魚很引起我的注意。透西看到我認真地看她,臉上現著微笑。
「吃完炸魷魚我們去玩橋牌。」透西說。
「很晚了,我不應該還待在外面。」阿薩幾說。
「橋牌是在屋子裡打,和音樂家恰好四個人。」透西說。
「反正大家第二天都沒事做。」我說。
「媽媽知道要罵的。」她說。
「剛才我們帶妳到路尾時,姨母看到是我帶妳出來。」
阿薩幾首先裝著苦笑,然後含情脈脈地望著我。
當我們三個人從後門走進客廳時,音樂家在裡面很惱怒地踱方步。
「音樂家你又調斷了最細的第一弦了嗎?」我說。
「總是那E弦。」他疑惑地望著阿薩幾。
「我不是已經警告你勿把弦調得太高嗎?」我說。
「我照著絕對音高調弦是我的錯嗎?」
「當然,你沒有錯,不過下次要買還是買外國貨好。」
「音樂家這是你的炸魷魚。」透西說。
「謝謝,這位是誰?」
「阿薩幾,她來參加打橋牌。」我說。
失業、撲克、炸魷魚
已經退役半年的透西晚上八句鐘來我的屋宇時我和音樂家正靠在燈盞下的小木方桌玩撲克。我拉一張椅子請他坐下。他說他想到路尾去散步。假如你願意參加打撲克九點鐘我和你到路尾去,我說。透西輸了二十隻火柴根,他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再數二十隻火柴根堆到他的面前並且拉他坐下來,他起先拒絕我這樣做,我再三的拉住他,然後他又坐下來。九點半時他又把二十隻輸掉了。他一共輸了四十隻火柴根。
「透西你輸了四十隻火柴根。」我說。
「我知道,八塊錢。為了消遣八塊錢不算多,我現在付給你。」
他和音樂家都是矮身材的男人...
作者序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以從其投身創作的時空窺知一二。在他首度發表作品的一九六二年,正是總體社會一意呼應來自威權的集體意識,甚且連文藝創作都被指導必須帶有「戰鬥意味」的滯悶年代。而七等生初登文壇即以刻意違拗的語法,和一個個讓人眩惑、迷離的故事,展現出強烈的個人色彩與自我內在精神。成為當時一片同調的呼聲中,唯一與眾聲迥異的孤鳴者。
也或許因為這樣,讓七等生的作品一直背負著兩極化的評價;好之者稱其拆穿了當時社會表象的虛偽和黑暗面,凸顯出人們在現代文明中的生存困境。惡之者則謂其作品充斥著虛無頹廢的個人主義,乃至於「墮落」、「悖德」云云。然而無論是他故事裡那些孤獨、離群的邊緣人物,甚或小說語言上對傳統中文書寫的乖違與變造,其實都是意欲脫出既有的社會規範和框架,並且有意識地主動選擇對世界疏離。在那個時代發出這樣的鳴聲,毋寧是一種挑釁,也無怪乎有的人視之為某種異端。另一方面,七等生和他的小說所具備的特殊音色,也不斷在更多後來的讀者之間傳遞、蔓延;那些當時不被接受和瞭解的,後來都成為他超越時代的證明。
儘管小說家此刻已然遠行,但是透過他的文字,我們或許終於能夠再更接近他一點。印刻文學極其有幸承往者意志,進行「七等生全集」的編輯工作,為七等生的小說、詩、散文等畢生創作做最完整的彙集與整理;作品按其寫作年代加以排列,以凸顯其思維與創作軌跡。同時輯錄作者生平重要事件年表,期望藉由作品與生平的並置,讓未來的讀者能瞭解台灣曾經有像七等生如此前衛的小說家,並藉此銘記台灣文學史上最秀異特出的一道風景。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
目錄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失業、撲克、炸魷魚
橋
圍獵
午後的男孩
會議
白馬
黑夜的屏息
早晨
賊星
黃昏,再見
阿里鎊的連金發
囂浮
狄克、平凡的女人、漁夫
隱遁的小角色
讚賞
綢絲綠巾
獵槍
來到小鎮的亞茲別
九月孩子們的帽子
回鄉的人
初見曙光
後記:情與思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失業、撲克、炸魷魚
橋
圍獵
午後的男孩
會議
白馬
黑夜的屏息
早晨
賊星
黃昏,再見
阿里鎊的連金發
囂浮
狄克、平凡的女人、漁夫
隱遁的小角色
讚賞
綢絲綠巾
獵槍
來到小鎮的亞茲別
九月孩子們的帽子
回鄉的人
初見曙光
後記:情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