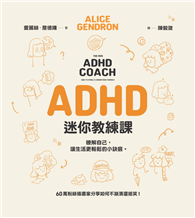削廋的靈魂
只有藝術才能告訴我們,有一些表達方式是完全屬於自然的。
--朗介納斯
一
我正坐在寢室門外曬衣場的草地上,有幾秒幾分幾時幾日幾月幾年了,靠著一棵油加里樹彈唱吉他,因為我心裡實在窩囊得很。整排寢室,你看不到一個樣子悠閑的人;這一排寢室,都住著畢業班的三年級生,包括普通科、藝術科、音樂科和體育科。無論你看到他們是在那裡,都他媽的把頭部和書本連在一起;好像頭是書本,書本也是頭,真叫你很不舒服。除掉你之外,三百多個畢業生,個個都像個大混蛋。這種情形,像是一個高一個低的天秤的兩端,不能平衡,叫你心裡覺得難受。你可以想像,我是怎樣地看不起他們,而你也可以想像,他們又是怎樣地看不起你。可是,奇怪得很,你會聽到幾個多嘴的體育科傢伙,穿著小三角褲,赤裸著上身,把胸部挺得像塊大石板,當他們經過走廊到廁所去時,會轉過頭來對你叫一聲,比著大拇指說:
「好棒,武雄。」
我瞧著他,但我的嘴巴正在唱「大衛,寇克」,《邊城英雄傳》的主題曲。假使碰巧,我正唱到曲子的末尾,你便放大聲唱:
「大衛,大衛寇克……」
「好棒,再來一遍。」他們叫著。
那麼就會有人從窗口伸出頭來,看看你;有幾個(心裡總是期待著周圍會發生什麼事)會走出寢室,然後對你笑笑;坐在窗口的傢伙,也會被擠跌到走廊來,然後你會聽到罵著:「×你×」,發出一陣混蛋的哈哈笑聲。我真瞧不起那些體育科的笨傢伙。說真的,並不是你體格差嫉妒,他們個個真有那種硬裝出來的蠢相,叫你看到時好笑。譬如,他們每一個傢伙都喜歡穿三角褲,把小鳥兒綁得緊緊地,可是一面走又會一面從三角褲斜邊,伸進一根指頭。有的喜歡用食指,有的喜歡用中指,有的喜歡用無名指,有的喜歡用小指,但我沒有看過用大拇指的。他們把指頭伸進去調整一下;在那種動作裡,就有一隻腿,有的是左腿,有的是右腿,像馬的前腿一樣地收動一下。但當他們穿著一身整齊的卡其制服時,看起來一點也不蠢。女老師和女教官真喜歡看他們英挺的姿態。他們站在操場上,總比其他科系的傢伙高出一個頭,實在是他媽的英俊和神氣。可是,一旦行進時,你會瞥望到某一個傢伙,會突然地跨了一個大步,假使你是第一次看到,一定覺得是無緣無故;好像他的腿在空中停頓了那麼幾分之幾秒,而比正常的步伐慢下來,所以跨大步趕上;但那一步的聲音會很響亮,聽起來很驚慌匆忙;那時,你會聽到值星教官常德的蹩腳的廣東口音,大聲地斥罵著:
「怎麼搞的!」
我們藝術科的隊伍,就在他們體育科的傢伙後面;你當然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我會忍不住地笑出來,有時馬步良也會跟著笑;我和馬步良是排在一起,我們同樣高度;有時他在前,我在後;有時我在前,他在後。聽到有人笑,常德教官馬上又斥了一聲:
「笑什麼笑!」
他的廣東音真使人笑死。假如碰巧,前面體育科的某一個傢伙,又響出一個匆忙的跨步,那麼,你會連笑下去。那麼,這一笑,就像堤潰,實在叫人忍不住,把其他的人也帶笑出來。那麼,常德教官便不得不再斥罵一聲:
「莫名其妙!」
可是,操蹩腳的廣東音的常德教官,脾氣實在好得很。他把「其」音說成「ㄍㄧ」音,引起全場都嘩笑出來。那些走步怪模怪樣的體育科傢伙,真他媽的條條都是好漢,人笑他不笑,把胸部挺得更高,走在全體隊伍的最前面,好像那好笑的芝麻事,與他們沒有半點關係。說起來還真奇怪,他們個子高的很高,但排在隊伍尾端的矮子,可真他媽的矮;所以你從後面望過去,那幾個矮子,穿著瘦腿褲,上半身卻鼓得像個青蛙,個個看起來,都是那麼假正經,人笑他不笑,故意扭著屁股,像馬的前蹄一樣的縮腿,引人發笑。而常德教官,脾氣可實在好得很,你永遠不會再遇到那樣好的軍人,因為最後他也笑了。他實在好得很。說真的,我和體育科的傢伙很熟識,他們認為你是個「寶」。要叫體育科的傢伙對你好感,除掉是漂亮的鬼女生之外,就只有「寶」能讓他們看得起。他們雖然個個都滑稽得很,卻很爽朗愉快,從不耍心計和奸詐,可是他們卻都是怯懦的太保混蛋。就是這一點使我看不起他們。他們的體格看起來很結實,但大部份都是混蛋草包。
我沒有去注意,我已經把大衛.寇克唱了有一百遍,我已經不再唱了,只是坐在草地上,背靠著油加里樹,望著連成一列的一間一間狗窩寢室。不知道誰把消息傳回來,但你可以相信,一定是那些嘴巴不停「阿每阿每」的客家人傢伙中的一個;因為只有客家人,才會去注意學校的動靜,去斤斤計較考試和分數;只有客家人才會關懷那些芝麻事;任何的芝麻事,總有客家人的嘴巴在那裡「阿每阿每」。消息傳回來,然後,一窩蜂地人從寢室湧出來,有的用走的,有的用競走的步姿,有的用小跑,有的大步奔跑,沿走廊浩浩蕩蕩地朝向紅磚大樓樓下教務處的走廊。那些穿三角褲,像猩猩在走廊走來走去的體育科傢伙,趕快回到寢室,穿上長褲和背心,然後像狼虎般地又奔出來。整條通往大樓的走廊,都是畢業生的大行列,在木工教室轉角的地方,和那些鬼女生(她們已經都像女人)會合,成為更大的人羣。說出來真遺憾,只是去觀看自己考試時的座位號碼,你可以想像,他們那種擁擠的蠢相。那條大樓走廊,我是說辦公室各處門前的走廊,兩個人相向走過,都要擦到肩膀,那時,卻在那個只有四開大的公佈欄前面,擁擠了三百多位大男大女,而且,你會相信,男和女又會有個像溝或像牆般的距離,否則又會發出尖叫。幾刻鐘後,才有一個人蹣跚地走回來。然後是聽到吃晚飯的吹號聲。要不是那個時候,就是吃晚飯的時間,保險要等一千年,那些去看座號的傢伙才會回來乾淨。你可以想像,尤其那些鬼女生,也許要等一萬年。像這樣的芝麻事,你不能想像,一旦想像了,就真不可思議,叫人沒法相信。而一切芝麻事,又都是過來人都知道,是一點也不假的。聽到那吃晚飯的號音,你又可以想像,他們又一窩蜂地、爭先恐後地、從原條走廊,鬧哄地急奔回來。而客家人,尤其是體育科的,又會是跑在最前面。我對客家人沒有好印象,雖然我的母親的父親也是客家人,我還是要罵他們,因為他們幾個都是自私自利的傢伙。
我實在懶得從草地上站起來,但我還是站起來。突然從走廊上混亂的人羣中,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
「劉武雄,你的名字被劃掉了。」
這個叫聲,真像一把銳利的大刀,又把你砍倒在草地上。我跌坐在草地上,想看清楚那個混蛋對你這麼說。但你實在分不清誰是誰;走廊上,寢室門口,萬八擁擠;有的要進去拿飯碗進不去,有的已經拿著飯碗出不來;真像一團窩囊。你可以想像,開向走廊的兩個窗戶,有人跳進跳出,那是睡在靠窗鋪位的傢伙。但有一個混蛋真自私,他跳出來後,快速地想把窗戶拉下來,竟把後面跟著要跳出來的傢伙的頭夾住了。有一個笨傢伙,來不及關下窗門,已經湧上去幾個傢伙;你可以想像,他的鋪位一定踏滿了濕腳印,你可以聽到滿走廊「×你×」的聲音,我慢僈才想起來,通知你的聲音是簡富山的沙喉聲;那時人聲嘈雜,你想在一羣鴨子中去分辨出是誰叫是不可能的。老簡是個很好的同班同學,他住在新店,他的家在碧潭岩石上開了一家茶亭,只有他有一種正義感,你可以感覺出來。同學三年,你幾乎什麼芝麻都能感覺出來。別人才不會管你這芝麻,只有他,沒有別人。老實說,我望著眼前那一陣騷亂;事實上,我的眼睛只注視腳邊的一株草葉;我開始在想著,回憶著,然後你的嘴巴唸著:
「你被犧牲了。」
我到底用走,或用跑的,我記不清楚了。總之,你到了教務處門前的公佈欄,那時,那裡連一個鬼也沒有。你親眼看到,三年來用鉛字打出來的名字,被一條紅線劃掉了。
二
我知道那是葛文俊老師搗的蛋。你到底有沒有到飯廳去吃晚飯,我已經記不得了。你不但感覺羞恥,也覺得葛文俊老師十分的卑鄙。我回憶著午後在實習處會見葛文俊老師的情形。午後二點鐘左右時刻,他寫了一張字條叫女校工送到寢室給你。從上星期六開始,畢業班已經停課,準備在這個星期三畢業考試,所以大家的生活不受到約束,除掉吃飯以外。葛文俊老師的字條,簡單地叫你馬上到實習處去見他。
你站在實習處辦公室門口張望了一下,看到葛文俊老師的側面。你不喜歡看到他的右側面,左側面你也不喜歡,因為看到他的側面,你就會被他的鷹勾鼻子嚇壞。一個人生了那樣的鷹勾鼻子,自己也許不覺得,可是別人並不能不覺得。我的速寫工夫很好,曾經憑記憶畫過葛文俊老師的右側面,也畫過左側面。我把它拿給同班的傢伙看,他們覺得十分有趣,他們也照樣畫,可是不會像我畫的那麼逼真。但是你不能當葛文俊老師的面,畫葛文俊老師的像,又讓葛文俊老師看到。讓他知道,你把他畫得那麼逼真,那是罪過。他知道我們是藝術科的學生,隨身帶著速寫簿,隨時去實習或做什麼芝麻事。他會笑嘻嘻地走過來,看你剛才畫了什麼;他幾乎對每個同學的速寫簿,都要細心地檢查過,看看有沒有畫他的像。有一次,他走到我身邊來,「你這個繪畫天才,我看你畫了些什麼。」他說。我還未把速寫簿遞給他,他已經用那瘦長多節的手爪捉緊了簿子,因此你只好放手給他。他說:「你的本子倒是相當的薄呀!」他以為像我這樣的、受人稱讚的繪畫天才,一定用一個大厚本子。老實說,蠢材才用那種價錢昂貴的厚本子。他一張一張的翻著看,臉色頗覺失望,「你倒真畫得不錯,都是人像,畫得滿像,可惜這個本子的紙太粗劣了。」他說的沒錯,我用的是便宜貨,紙色黑黃而又粗糙,那些蠢材才用光面的好貨。你可以知道他不懂假懂,所以也不必跟他去爭論。
「可是我問你,」他笑笑地看我。
「好,」我裝得很有興趣。
「你幾乎什麼人都畫到了,為什麼沒畫到我?」
「我沒有嗎?」我感到驚訝地說。
「沒有,我找不到。」他又說。
「我記不得了,我高興畫誰就畫誰。」
「你不喜歡我嗎?」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高興畫就畫,不是那種喜歡不喜歡。」
「好。我知道你把它藏起來了。」
「沒有,我把它撕掉了。」
「為什麼?」
「我畫壞了。」
「怎樣壞法?」
「我把你畫得真難看。」
「有什麼關係呢?」
「我把你畫醜了,心裡覺得很難受。」
「好傢伙。」他還是笑笑地說:「我知道你畫得好,是不是我長得太難看?」
「那裡,葛老師很年輕英俊呢。」
「你別誇獎我,不過你答應為我畫一張像如何?」
「敢不從命,葛老師。」
「什麼時候?」
「我有靈感的時候。」
「現在有嗎?」
「還沒有,葛老師。」
「好,你要記住呀。」
「是的,葛老師。」每一次他遇到我,他總提起這件芝麻,說為什麼還不能為他畫好一張像,而我始終拖延著沒有給他。說真的,天殺也不能給他。坦白說,我畫他不止有一萬張了,張張都是傑作,可以比美保羅.畢匹卡索,有幾張還特別上了顏色。為這件芝麻,我處處要躲避他,甚至稱病不上他的課。不知怎樣,看到他的右側面,總會心驚膽跳,所以你不得不隨畫隨撕,片甲不留。有時畫他時,突然感到心懼,但又不知道為什麼動手畫他。越畫他越怕,越怕又越想畫他。你真不能明白清楚。
「進來呀,進來,武雄。」
他轉過臉來時,看到你。葛文俊老師的正面,你會覺得很親切或什麼的。但這不包括他的「剋學生」的兩邊顴骨。而一個人的正面,說起來只不過是一個全體的一面而已。我走進去,周圍看看,整個四方形的房間,整齊地排列著四、五張辦公桌,間隔相當地相等,好像誰也不會碰到誰,而誰也都能監視到誰。真絕。那時,整個辦公室只有葛老師一個人在裡面,他不像帶你們到市區國民小學去實習時那種打扮,他顯得很隨便,好像午睡失眠了或什麼的,眼睛裡有紅血絲,看起來有點不善,好像才從家裡吵架出來。我站在他的辦公桌邊俯視他,他卻抬頭看我。
「怎麼搞的?武雄。」
他煩躁地說,我覺得很不對勁。
「你真使我頭痛。」他又說。
「你現在能馬上提出一本完整的筆記本嗎?」
他抬頭看我,你有點莫名其妙。
「什麼筆記?葛老師。」
「什麼筆記?當然是教材教法的,我看你滿聰明的,其實你卻那麼笨。」
「教材教法的筆記?」
「是的,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我問你,你只能馬上回答我。你真是一個我所見到的最糟糕的學生。」
「沒有,葛老師。」
「那麼你的筆記本呢?」
「賣掉了。」
「賣掉了?!」
你想,葛老師那裡會不知道這件事。把寫過的筆記本論斤賣給收破爛的古物商,古物商再論斤賣給雜貨店,雜貨店拆開零紙包糖果或什麼的。上星期六下午,知情的古物商推了一部便車來,把畢業班學生的筆記統統收買,滿載而去。你的總共賣了五元六角,意思是你有五斤十兩的筆記(包含一些雜紙);一斤一元,半斤是五角,二兩是一角多,像這種情形,只有讓那個可憐的窩囊傢伙佔點便宜,沒有人會去計較。
「你怎能把自己寫的筆記賣掉了呢?真該死,武雄。」他一抬頭看我,你便看到他的顴骨。你聽他假惺惺地賣關子,可真令人感到無比的恐慌。而你也會站在那裡冒氣。如果能夠揍他的話,那時倒是居高臨下,方便得很,可是那樣做是大逆不道。他也知道這點,所以老坐在那裡。真該死,你沒有冒出氣來。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削廋的靈魂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削廋的靈魂
致敬 七等生
超越時代的前行者
他的創作歷程示現了幻譎奇偉的生命之歌
「我是一個驕傲的謙卑者,我失落了一座城,請想想,我有一座城可喪失,損失雖大畢竟能使人誇耀和歡娛。」--〈離城記〉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發表的十一篇小說,包括〈離城記〉、〈無葉之樹集〉兩部中篇、第一部長篇小說〈削廋的靈魂〉,以及〈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自喪者〉、〈蘇君夢鳳〉等八則短篇。
七等生於〈離城記後記〉自呈創作意志:「在一個沒有人注意或有意疏忽的角落固執地來種植我的花朵。」他回通霄定居兩年後發表〈離城記〉,為了離城而四處追尋的詹生,反覆等著一個未知的約見。生命唯有在追求中才被覺知存在,「當我擁抱住它時,猶如向存在的時光告辭。」
〈削廋的靈魂〉直接以本名「劉武雄」為小說主角,畢業考前一天被老師惡整喪失考試資格的青年,展開二十四小時的獨白與求生。
從山谷帶回不同男人的女人;與嬰孩獨處的男人;等不到情人的蘇君;無人哭泣的瘋女的喪禮。在現世生存的乖謬和變態中,向陰影般的巨人提出挑戰。
作者簡介:
七等生
本名劉武雄,1939-2020。生於苗栗通霄,台北師範藝術科畢業。自1962年首次在《聯合報》發表短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起,共發表124篇小說、137篇散文(含雜記、序文),及56首新詩。1989年重拾畫筆,將創作重心轉向繪畫,於1991、92年舉辦過兩次個展。
1966、67年連獲第一和第二屆台灣文學獎。1976年獲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1983年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約訪美。1985年獲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和吳三連文藝獎。小說作品《沙河悲歌》、〈結婚〉亦曾改拍同名電影、電視劇等。2010年獲頒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
國內外學者和研究生論文超過百餘篇,允為台灣當代文學最重要作家之一。
章節試閱
削廋的靈魂
只有藝術才能告訴我們,有一些表達方式是完全屬於自然的。
--朗介納斯
一
我正坐在寢室門外曬衣場的草地上,有幾秒幾分幾時幾日幾月幾年了,靠著一棵油加里樹彈唱吉他,因為我心裡實在窩囊得很。整排寢室,你看不到一個樣子悠閑的人;這一排寢室,都住著畢業班的三年級生,包括普通科、藝術科、音樂科和體育科。無論你看到他們是在那裡,都他媽的把頭部和書本連在一起;好像頭是書本,書本也是頭,真叫你很不舒服。除掉你之外,三百多個畢業生,個個都像個大混蛋。這種情形,像...
只有藝術才能告訴我們,有一些表達方式是完全屬於自然的。
--朗介納斯
一
我正坐在寢室門外曬衣場的草地上,有幾秒幾分幾時幾日幾月幾年了,靠著一棵油加里樹彈唱吉他,因為我心裡實在窩囊得很。整排寢室,你看不到一個樣子悠閑的人;這一排寢室,都住著畢業班的三年級生,包括普通科、藝術科、音樂科和體育科。無論你看到他們是在那裡,都他媽的把頭部和書本連在一起;好像頭是書本,書本也是頭,真叫你很不舒服。除掉你之外,三百多個畢業生,個個都像個大混蛋。這種情形,像...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序
離城記
離城記後記
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
自喪者
在山谷
聖月芬
在霧社
無葉之樹集
餐桌
是非而是
在蘭雅
滑動
難堪
禪的學徒
絕望
無葉之樹
睡衣
年輕博士的劍法
蘇君夢鳳
削廋的靈魂
後記
序
離城記
離城記後記
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
自喪者
在山谷
聖月芬
在霧社
無葉之樹集
餐桌
是非而是
在蘭雅
滑動
難堪
禪的學徒
絕望
無葉之樹
睡衣
年輕博士的劍法
蘇君夢鳳
削廋的靈魂
後記
|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