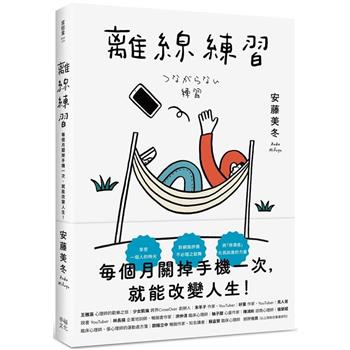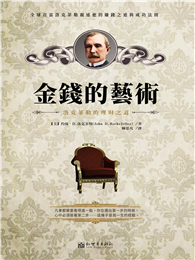沙河悲歌
一
晚上約莫九點鐘左右李文龍從座落在街尾的一間低矮的瓦房走出來,從外表看不出而事實上是一隻半殘廢的左手臂在腋下夾著樂器克拉里內德。他是外表不壞的中年男子,中等身材有些瘦,穿著白色襯衫和一條舊的黃卡其色褲子。他朝街頭走了約五十公尺,然後左轉入一條黑漆的小巷,那條巷事實上是一條大圳溝,除了在馬路的一部份外這條水泥溝渠在巷子裡並沒有加蓋。李文龍走的是溝緣的狹道,他的腳步並不太穩當,有點左右搖擺,好像一個走索者,但他已經走慣了這條路絕不會掉進圳溝裡,這像是一條黑暗的隧道,在盡頭的兩端都可以看到街燈照下的光亮,他走出來筆直地橫過昏黃光的街道,習慣地朝著兩排樓房走廊上站立的人們掃視一眼,要是那些閒散的鎮民同時也看到李文龍從巷子走出來,他們雖不說出來或和他打招呼,但他們心裡卻有一個印象,像互屬於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蔑視,經過了最初的好奇和猜疑之後,互相間都有那種冷淡的和平。他又走進另一段黑漆的小巷,同樣是那條沒有加蓋的大圳溝。然後這條溝圳直角向北,李文龍來到另一條橫街,在西面盡頭接住縱貫公路,那裡有兩家相對面的酒家,都掛著紅綠色的燈光招牌,街路上顯得很冷清,但屋子裡面卻很熱鬧。他在樂天地和圓滿兩酒家奏唱了一夜,約莫凌晨一點鐘回到家門,木門已經關上了,他輕叩了幾聲,靜等了一會兒,他想玉秀和孩子已經睡熟了,於是他轉身走開回到街上。他到火旺後樓的祕密賭場轉了一圈,那些人賭興方酣,他只站了幾分鐘又回到街上。當他走出來時覺得一陣眼花,頭頂像壓著沉重的石塊。樂器克拉里內德分成兩節捲在布巾裡,依然夾在那喪失筋力的左手臂腋下,這隻手臂每當他在惡夢中驚醒過來,常常發現它纏在弄亂的蚊帳裡。在酒家奏唱時好女色的昌德和明煌曾來找他,他們互相喝了幾杯酒。但他沒有半點睡意,醉意和瘋狂,他已經習慣午睡到黃昏,吃過晚飯後為生活到酒家奏唱賺幾十塊錢。他抬頭望望彎月,也許是魔神附他,使他離開鎮街,昏迷般地步向郊外的沙河。他咳嗽得很厲害,好像急迫地想要叩開頭頂上幽黑的天門。從胃部湧到喉頭許多帶酸的水液,吐掉後又從胃部裡湧上來。他想:有一天要是從肺部裡咳出大量的血液來,那會結束了這條生命。
來到沙河已夜深幽寂,除了淺流潺潺細訴。他想到他的弟弟二郎,他對他寄以厚望。來到沙河晨霧已經瀰漫。這條河有兩個發源:一條由坪頂山下來,細流經過土城梅樹腳;一條自北勢窩流經番社在南勢與那一條水流匯成三角洲,然後通過沙河橋流向海峽的海洋。沙河以沙多石多而名,經常呈枯旱狀態,只有一條淺流在河床的一邊潺潺鳴訴,當六七月的大水過後,這條細流常因變更的河床地勢而改道,幾年在南邊岸,幾年在北邊岸。幾百年前沙河河床甚低,海水在潮漲時能駛進福建來的帆船,這件事已被先祖的死亡而遺忘了,現代的人根本不知道這樣的事。但李文龍曾在小時候聽過他的祖父說到這件事,當他要到沙河來游泳時他的祖父會警告他勿游向深水處,不要靠近跳水谷,只許在橋下淺流裡。李文龍坐在石頭上臨著水邊注視水流,從褲子後袋掏出一瓶酒,向河水倒下一些敬敬沙河河神,然後自己也呷一口。
沙河淺流潺潺細唱。
他試吹著幾聲樂器克拉里內德,吹嘴的簧片在酒家已經吹裂,他用破裂而沙啞的聲音吹奏著夜曲。他常獨自吹奏名曲,那是他的弟弟二郎到城市求學後陸續為他寄來的,但在酒家他和彈吉他琴的金木依然奏著他們熟悉的「望春風」或「補破網」這類民謠。
那年,他決意追隨葉德星的歌劇團當一名職業樂師時,李文龍跪著向母親請求說是為藝術;今天,他才懂得什麼是生活和賦格。他沒有辱沒他心中的願望,可是並不是他想追求時就獲得它,它來時卻是當他萬念俱灰之時。
他這樣想:城市大轟炸的第二年如果父親不禁止他到台北進高等學府就學的話,現在李文龍可能是位有成就受人崇仰的音樂家或是什麼實業界的經理。而不是像今天為賺取生活在酒家奏唱受人輕卑的落水狗。他又想:到頭來可能都一樣,哲學的重要課題雖是認識論的問題,但所有可能的人生必須付於實踐;對他來說,音樂家和奏唱者之間唯一的識別不是氣質而是環境和使命的選擇。
有趣,李文龍曾經希望在沙河鎮公所當一名雇員,當他的肺病嚴重已到迫使他放棄吹奏樂器傳佩脫時。他放棄了樂器傳佩脫改吹樂器薩克斯風,幾年之後他能夠熟練地吹奏任何種類的薩克斯風樂器。但是時光前進,他的健康又迫使他放棄樂器薩克斯風,或者寧可說李文龍的精神已厭煩薩克斯風樂器的悲鳴,最後樂器克拉里內德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好工具,高傲而飲泣般的樂器克拉里內德才是他的生命哲學。
二
李文龍想他應該寫信給二郎。他不知道有多久沒有寫信給他,也許有半年或整整一年,他不是一個善於用文字或語言表達情感的人,但他是一個內心充滿熱情的人,除了有某些例行的事需通知二郎外,譬如戶口校正或回信說收到了歌本,他無法去訴說情感的問題。他想二郎就是自己的親弟弟,這件事實已足夠證明他們間的互愛,而無需再用言語說什麼,就是他和二郎在一起同住家裡時,也甚少用語言來互相阿諛表示親愛,可是他們之間卻能用心去感覺,就是現在二郎遠在城市和他相距幾百里,他和二郎之間亦能互相感覺。但是有一件事他應該寫信給他,或者假如現在他能和他見面,他必定要當面告訴他。
這件事是當他跪求母親讓他去追隨葉德星歌劇團時,母親不明白李文龍所說的藝術是什麼意思。母親只知道人人要照顧日日的生活,人人必須做不為習俗所輕卑的工作。母親說:你要開始工作賺錢使生活改善點。母親那時不瞭解李文龍正熱心於樂器傳佩脫的技藝,他的確吹奏的不壞,他想要出人頭地必須使樂器傳佩脫的音色異於他人,有時必須達於他人所難以吹奏的高音,他必須離開沙河鎮到外面的世界去吸收經驗,也應該到外面的世界去表現他的才能。土生土長的樂師都不懂得看五線譜,他們用的都是印成簡譜的本子,但李文龍不然,從開始他便揚棄簡譜而在五線譜上下工夫,這個理由不單是樂曲有時要移調去適合給歌劇團的女演員唱,另一個理由是為了知識,接受外國曲調豐富的大曲子,它也許在歌劇團派不上用場,卻可以在工作時間外吹奏滿足自己。
「跟隨歌劇團和那些不三不四的流浪人混在一起能夠出人頭地嗎?」母親說。
李文龍第一次察覺他和母親有觀念上的差異。母親傳統上的觀念無法瞭解他的需要和他血脈的跳動。他感到他在家已經無法再待下去。戰爭的最後一年,事實上那時誰也不知道戰爭要延長到什麼時候,父親知道他在家無事可做,卻並不知道他偷偷地瞞著他練習吹奏傳佩脫樂器。父親留李文龍在家裡是為了安全的問題,不讓他到正遭受轟炸的城市繼續讀書;父親說只要戰爭結束馬上送他到城市進高等學府,父親那時也自恃自己有一份公家的事做,生活一切沒有問題,但一日經過一日,拖延了好幾年,生活隨戰爭日漸窮苦。母親要李文龍在沙河鎮學做木匠,他順從她的意思做了二個星期,他帶著沮喪的感想回家時,母親不斷地搖頭嘆息,說她看不出他將來能做出什麼來。
他和昌德每日約好到沙河橋下勤奮地練習,李文龍吹奏樂器傳佩脫,昌德吹奏樂器斯賴,樂器屬於沙河鎮公所的保管財產,向鼓勵青少年吹奏樂器預備組成樂隊的管理員借來的。直到那一天,他終於向母親偷偷地宣佈當晚深夜要隨葉德星的歌劇團遷徙離開沙河鎮時,母親才真正傷心地哭泣了。她始終不瞭解他為何要去當一名歌劇團的樂師來羞辱她;她的觀念無法明瞭有成就的藝人也是一種出人頭地;她不懂什麼是藝術,她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她所不知道的正是年青的李文龍所知道的。父親是讀書人,卻是舊時代的讀書人,在鎮公所當一名職員,生活在沙河鎮使他必須謹慎地顧全他的面子,李文龍不能事先告訴他,他要離開家去從事樂師的職業,他知道他的決定會大大地刺傷父親的尊嚴,父親會承受不住他內心的愧疚,父親事先知道了他一定走不成。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告訴母親,李文龍為情勢所逼雙膝跪下懇求母親讓他走。
現在他必須告訴二郎首先追求的技藝藝術到最後會轉來發現自我。李文龍在沙河鎮樂天地和圓滿兩酒家來回奏唱,為那些議員和鎮民代表,為那些農會職工或學校的教師,甚至是為那些過去是可憐的佃農現在已擁有土地的驕蠻的農夫和唯利是圖的商賈吹奏助興的流行歌,他們頗神氣地以為李文龍是為他們而非為自己的存在吹奏,他們並不知道這其中的奧妙,一個藝人的生命乃在於他真正的表演中,他們輕卑地賞給他幾塊錢,以為是他助長他們的豪情和享樂,而不知道他更重要的是做了情感會合的媒介,他們平時雖然貪圖錢財愛好名位,可是在李文龍看來,生命的憂患其本質都是相同的,藉樂忘憂事實上是探詢憂患的真正價值,像土人們在狂歡節後而能溫馴地回到生活辛勞的狩獵;當他們和那些酒女一起混聲合唱「望春風」時,情感會合而生命的意志融會在一起。李文龍不知道他的弟弟二郎是否會欣然喜悅或接受這種盡情的胡鬧。二郎的天質聰慧,年幼時李文龍便以他為榮,他想二郎也許將會明瞭自憐是寬恕和淡忘社會的變遷所帶來的逆境的一個主要的情愫。
李文龍漸漸地認識了他所事的職業的生活形態,許多例行反覆不已的事物,造成他在厭煩後逃避去關注它。他跟隨葉德星歌劇團離開沙河鎮,每十天必須轉換一個地方,常常是由這一縣到另一縣,途程是數十里或數百里的長征,劇團的演出非常不可能此鎮演完就到鄰鎮去,開始時給他很大的迷惑和新奇的感覺,後來他明白了,這種辛勤的勞頓完全是為了觀眾的心理,觀眾是喜愛好奇的動物,他們會厭膩相同的形式或久知的事物,他們需要新奇的東西來調合呆板式的日常生活,他們有渴欲觀睹新面孔來刺激想像力,但劇團改變戲碼變換形式十分不易,劇團的遷徙等於在逃避熟識他們的觀眾,劇團的生存只能選擇陌生的異地,最後一天晚場戲演完後,隨即捆綁行李,拆下佈景,工作在疲勞中進行,任何人都需要配合這種工作,常常可以看出感人的團體精神,卡車在戲院門前等候,搬運的工作在寒冷的深夜中進行,在暴風雨中進行,有時在夏季的涼夜裡,或有圓圓的月先照耀下進行,然後告別那家劇院,劇團的經理和劇院的老闆結清了帳款,最後是每個人的私人行李拋上卡車自己要坐的位置去,可以看到離開而沒有送行的人,十天裡在劇院內一同歡笑憂患的觀眾已經把他們遺忘,觀眾在睡夢中根本不知道劇團正在離開,因為第二天在戲院上演的是另一個劇團,清晨在菜市場或街道有新來劇團的廣告人員出來宣佈精彩的戲碼,在主要的街道旁有新劇團的旗幟,牆壁上貼有新的佈告,所以觀眾沒有感覺,一切有別人來迎合他們的胃口,他們望不進一切事物的充滿傳奇的內部。這劇團演完最後一幕戲的夜裡,睡眠是在卡車的風馳電掣中度過,沒有人會在那個時刻交談,每個人都萎縮在自己安插的角落睡去,沒有小孩哭號,他們摟著母親的腰懷或母親摟抱他們在胸前,任何人,無論男女或大小都低首和沉默在他們共同的命運裡。那一夜的睡眠彷彿只有半分鐘,雖然長馳百里亦感覺短短的半刻時辰,卡車停在戲院門前,每一個人都得跳下卡車,他們站立著注視戲院,這戲院同那剛離開的戲院何其相似,彷彿他們沒有離開,而只是自己在矇騙自己扮演搬運的勞動,把剛才拆下的佈景重新再佈置起來,這一切繁重而式樣不變的工作自深夜開始直到太陽上升才結束,而每個人在戲中扮演的角色所象徵的油彩臉孔依然留在臉上沒有擦去,有些人甚至讓油彩留住十天或一月或一年。當太陽上升這一日開始,在這第一天的早晨有更繁重的工作要做,樂隊前導,全班人馬遊街宣佈劇團的來到,小丑拿著喇叭向羣眾宣佈驚人的消息,說笑和自誇,當全班人馬遊行完畢回到戲院吃午飯便需準備第一個午場戲,一切重新開始,十天一循環,像星星像季節像自然宇宙。
沙河淺流潺潺細唱。
他站立起來,解開褲子的鈕釦,向河水灑下一泡尿。潺潺水流自坪頂山經土城梅樹腳而來,與來自北勢窩經番社的另一條細流會合,他注視著珠粒的尿水落在水裡,迅速無踪地成為水流的部份流向海口而去,這水流在微薄的月光下富有蜿蜒的妙姿,那水潔白如少女隱祕的肌膚,形貌如蛇之身滑浮動在石間,聲音如情話之細訴,水流自灰茫茫的霧中流來隱沒在灰茫茫的霧中,只在他的眼前展現它的潔淨的容姿,但他覺得口腔有一股腥味,自胃部和腐敗的肺部湧上來,他坐下來吞了一口酒,壓服那可憎的氣味。
他的童年友好中的昌德,秋雄和他都因家庭的反對沒有繼續到城市去求學,良珍和德育到城市進高等學府,良珍學化工,現在在一家牙膏公司當技師,德育進了淡水英專,現在在中學當教師,照母親的觀念,良珍和德育都有正當而體面的職業,算是出人頭地了。有一次,李文龍和昌德從彰化搭火車回沙河鎮,他們跟隨的葉德星歌劇團在彰化演出,那是一個炎夏的早晨,當他們跳下火車時,李文龍看見月台上一位婦人背著一位穿藍衣的小女孩走在前面,他望到那片藍色突然覺得一陣昏暈和心跳,以為是看到了幼妹敏子,他站住像一個不著魂的呆子疑惑地望著,走在前面的昌德回頭奇怪地叫他:
「怎麼樣,一郎?!」一郎是他的父親日據時代為他取的名字,光復後,名字改為文龍。
然後他恢復了清醒,想到幼妹敏子不會永遠長不大。
「沒什麼。」他跟上昌德回答說。
然後他們瞥望到鐵路倉庫那邊站著一個臉面蓋滿黑炭粉末的瘦弱男人,他對昌德說:
「那不是秋雄嗎?」
「正是他,他在看什麼?」
「根本沒有什麼可看。」
「他或許在找人。」
「沒有,他只是癡望著火車。」
「也許是,我們去看他。」
他和昌德直接由月台跳下來,朝著倉庫跑去,一面叫著呆望著開走的火車的瘦弱青年。
「喂,秋雄。」
那人像從夢中醒來,聽到叫聲向四處望望,然後看到文龍和昌德,臉上顯得有些驚訝,不好意思地露出笑容來,他回叫一聲:「喂,昌德,一郎,你們回來了。」他那蒼黃有肝病模樣的臉孔逐漸笑得很可愛,而滿頭滿臉的黑炭粉末使他像是一隻可憐的鑽洞老鼠,他們靠近在一起,互相注視著對方,雙手握在一起,閃著銳利而喜悅的眼光。
「現在如何?」
「就是這樣。」
「你們在那裡?」
「彰化。」
「在劇團好嗎?」
「不錯。」
「假如我能吹奏什麼,我也跟你們去。」
他們一同走進一間大倉庫,裡面堆積著一籮一籮的黑木炭,留下的空地上有一張單人木床,床下放著一隻臉盆。秋雄說:「這是我的世界,木炭是我的兄弟。」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沙河悲歌的圖書 |
 |
沙河悲歌 作者:七等生 出版社: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2-1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6 |
中文現代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小說 |
$ 252 |
現代小說 |
$ 280 |
文學作品 |
$ 280 |
Others |
$ 28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8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沙河悲歌
致敬 七等生
超越時代的前行者
他的創作歷程示現了幻譎奇偉的生命之歌
「生命的憂患其本質都是相同的,藉樂忘憂事實上是探詢憂患的真正價值,像土人們在狂歡節後而能溫馴地回到生活辛勞的狩獵。」--〈沙河悲歌〉
一九七五至七六年七等生中期創作的六篇小說,包括連載於《聯合報》副刊的〈沙河悲歌〉、〈余索式怪誕〉、〈貓〉、〈大榕樹〉、〈德次郎〉、〈隱遁者〉,以及〈沙河悲歌〉出版前言〈寫作者的職責〉。
七等生自述:「小說從未脫離寫實的廣義範圍,形式取決於內容的需要。……有許多事物只能讓人意識到而看不到,甚至有某些事物具有繁複的關係,是紀實的文字所不能做到,那麼它必要以一象徵或另一假象來呈現它。寫作者無疑這是他不能推卻的職責。」
醉心於追求吹奏樂器技藝的男人;因誤闖山林而得的奇遇;離群索居的李德與貓的心靈對話;看顧著一家老小的大榕樹;重回家鄉的隱遁者……七等生以獨特的美學筆法,寫實主義的創作態度,象徵或假象,步步揭露主題隱含性,重新邁向自由人。
作者簡介:
七等生
本名劉武雄,1939-2020。生於苗栗通霄,台北師範藝術科畢業。自1962年首次在《聯合報》發表短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起,共發表124篇小說、137篇散文(含雜記、序文),及56首新詩。1989年重拾畫筆,將創作重心轉向繪畫,於1991、92年舉辦過兩次個展。
1966、67年連獲第一和第二屆台灣文學獎。1976年獲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1983年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約訪美。1985年獲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和吳三連文藝獎。小說作品《沙河悲歌》、〈結婚〉亦曾改拍同名電影、電視劇等。2010年獲頒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
國內外學者和研究生論文超過百餘篇,允為台灣當代文學最重要作家之一。
章節試閱
沙河悲歌
一
晚上約莫九點鐘左右李文龍從座落在街尾的一間低矮的瓦房走出來,從外表看不出而事實上是一隻半殘廢的左手臂在腋下夾著樂器克拉里內德。他是外表不壞的中年男子,中等身材有些瘦,穿著白色襯衫和一條舊的黃卡其色褲子。他朝街頭走了約五十公尺,然後左轉入一條黑漆的小巷,那條巷事實上是一條大圳溝,除了在馬路的一部份外這條水泥溝渠在巷子裡並沒有加蓋。李文龍走的是溝緣的狹道,他的腳步並不太穩當,有點左右搖擺,好像一個走索者,但他已經走慣了這條路絕不會掉進圳溝裡,這像是一條黑暗的隧道,在盡頭的兩端都可以看到街...
一
晚上約莫九點鐘左右李文龍從座落在街尾的一間低矮的瓦房走出來,從外表看不出而事實上是一隻半殘廢的左手臂在腋下夾著樂器克拉里內德。他是外表不壞的中年男子,中等身材有些瘦,穿著白色襯衫和一條舊的黃卡其色褲子。他朝街頭走了約五十公尺,然後左轉入一條黑漆的小巷,那條巷事實上是一條大圳溝,除了在馬路的一部份外這條水泥溝渠在巷子裡並沒有加蓋。李文龍走的是溝緣的狹道,他的腳步並不太穩當,有點左右搖擺,好像一個走索者,但他已經走慣了這條路絕不會掉進圳溝裡,這像是一條黑暗的隧道,在盡頭的兩端都可以看到街...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寫作者的職責
沙河悲歌
余索式怪誕
貓
大榕樹
德次郎
隱遁者
寫作者的職責
沙河悲歌
余索式怪誕
貓
大榕樹
德次郎
隱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