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波翅膀
一個有霧的午後,盧生遽然自生地看到一個友人的形象走來,他的外表閒散,但面目卻帶著詭譎的探索。這是盧生自去年來到海濱的小學校任教以來首次有訪客前來。盧生原是城市裡的一所中學的資深教師,他的妻子發現他與一位年輕的女教師產生戀情,將此事告到校長那裡去,當校長將那位女教師解聘時,盧生憤慨地同時辭職,但幾經另謀職業的奔波後,他疲倦而心灰意冷,斷然獨自到這個偏遠的海濱的小學校權充一名教員,暫時擺脫了和妻子在家裡的不愉快。這個前來的人是盧生久遠前的好朋友,曾在城市結伴交遊過一段頗長的時光,那是在他們年輕又富幻想的時代,另外還有一些人,形成一種好酒消沉而喜樂忘憂的小團體,然後生活把他們衝散了,各奔前程成家立業去了。這時是春天,陰雨而潮濕。當他出現在操場的一端向校舍這邊走過來時,彷彿他是在灰霧中從天空降下的;那天的確在中午過後,柔軟的陽光開始被陣陣移動而來的灰雲遮住了,然後下著一會兒沒有聲響的毛毛細雨,雲霧從右鄰堤防外的海洋自由地翻捲上升,佈滿在海岸和村舍的空際,木麻黃樹林和這漁村的屋瓦都變灰了,更遠的景物就看不見了,而他突然降臨。
盧生原在教室裡,午後的教學已使他感到倦煩,他轉頭從敞開的窗戶看到他走來。於是他走出站在走廊上等著他。盧生英俊的臉上展著笑容,他的頭習慣性地低傾著,但眼睛卻瞪著那人走近。
「我就知道,除了你,還能是誰?」
他們面對面時,盧生笑容可掬的高興說。
「你好嗎?盧生。」那個人望著他說。
「我告訴你,我是自由了。」盧生說。
「那是再好不過的事。」他讚同地說。
「我們多久不見了?」盧生問道。
「好久好久了,你應該記得我們分手的情形。」
「我當然記得,那時我們都醉了。」
「你為何有時間來?」盧生又說。
「靈感,我們都有互通的靈犀。」
「是的,我們自來總憑著靈感交往著。」
「那就對了,我現在就在你的面前,你需要時,我就來了,不是嗎?」那人說。
「是的,你看這是一個優美的地方,我沒有想到我會在這樣的地方一個人生活著。」盧生說。
「你說優美?」
「當然,我這樣認為,你不以為然嗎?」
「這種地方我熟悉透了,海水,新鮮空氣,鄉下人雜亂的屋舍,骯髒的小道,還有你會說他們誠實的面孔,其實是腐蝕性的魯鈍,多疑的心地。這是使你喜愛的理由嗎?」
「即使不是這種理由,你知道,我有我私自的理由。」盧生仍然愉快地說。
他們相見心情頗為快慰,但不免像昔日一樣展開一場爭論。他們大致意見相同但仍有少處差異的對所謂鄉間的一切的感想。他在探試盧生在此地的生活是否快樂和滿意,而他發覺盧生對鄉間的讚美無非是對自己的一番遭遇的嘲諷。他知道盧生會把它當作暫時的退避之地,他會再找機會回到城市去,在那裡不止是他應付出的責任所在,而且可以靠勤勞得到優厚的薪酬,以供他排遣他猶健壯的生命所發放的熱情。而熱情和慾望是一個人生命的詩章。一刻鐘後,小學生列隊離開學校回家,盧生準備將他的這位朋友帶往他在附近租居的房子。
盧生從辦公室走出來和他並排地走到此時空曠無人的操場,他們在雲霧的覆蓋下親密地交談著。
「我真的高興你此刻來。」盧生說。
「你這一切的感覺如何?」那人問道。
「很好,真的很好,」盧生停頓一下。他繼續說:「你知道,我說很好,是真的很好。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這是指婚後而言;我的婚姻,還有那三個孩子……你知道,我現在單獨獲得了幾近完全的寂靜,慾望離我而去,我最近寫了幾首詩,並且每天札記一些生活感觸……很美,我感覺這是極恬靜的生活,對我而言是最佳的生活,我的意思是對一個一生勞碌又沒有專志成就的人而言,有一個能夠暫脫形式生活的束縛是彌足珍貴的事。你知道,我原可找到其他中等學校任教,但那些繁瑣的枝節我厭煩了;但我現在覺得我的判斷沒有錯,我來這裡是對的,對我的身心獲益不少……我想到我現在能一個人單獨地生活在偏遠的一隅,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感到一股解脫的自由和快樂……我明白你來看我的意思,我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糟糕,我不是會誇飾的人,我完完全全能適應這種單調乏味的生活,除非情勢使然不得不被迫回到城市,我想我會一直留住在這樣的地方。」
這是盧生的肺腑之言,但他的傾出使他突然停頓沉默了;他對自己的吐露感到驚疑之至。於是在他的臉上現出慘淡悽苦的笑容,羞赧地把身體轉來轉去。這時,他們的肩膀由於靠近,相互撞擊摩擦著,首先像是輕微而無意的,漸漸地像是有意而變為猛烈,彷彿一個軀體蓄意地要擠進另一個軀體,情勢變得越來越為急迫。此時已是黃昏,霧靄的空際中響起像潮水般澎湃的音樂聲響,原本隱形於宇宙的透明的幽魂舞踊般地現形了,直到他們兩體的撞擊合併完成,一切又恢復為寂靜。
這時盧生因窒悶而困難地喘息著,每當一日的工作完畢邁步回巢時,這種急喘的掙扎便會發生。他孤獨地橫過操場的草地,斜斜地轉頭向堤岸那邊的廣大天邊做了一個驚疑的瞥視,彷彿害怕天會低陷蓋在他的頭上。這是他在城市生活裡所沒有的警覺,因為在城市永沒有天空的知覺,而他依然還未掙脫城市生活的昏噩。當他步上操場邊陲新建的籃球場時,他站在籃球架下面,擧頭望著突出板外的鐵質環圈,像是在等候下墜的一個籃板球。他曾是運動的健將,在大學他是系裡的籃球隊員,他的一位同父異母的妹妹在幾年前還是國內最好的籃球隊的前鋒球員,自她退休後,他在電視轉播的籃球賽中再也看不到她。那時每次看到她出賽的情形,他就熱淚滿盈。他的父親逝世之前曾約談過盧生,他的記憶中,他只見過父親兩次,而在這最後的一次交談中,他放棄了他做為長子所有應得的權益。他的母親沒有生下女孩子,所以他對那位同父異母的妹妹具有特殊的好感。
然後盧生從圍牆的缺口走到鄉村的石子路,他低垂著頭,對路旁的幾家新建的水泥樓房,和那敞露的俗豔的客廳佈置,連看都不看一眼。他轉進一條小巷子,一座老式的磚瓦房屋顯現在眼前,這是一個在過去中等規模的農漁人家的房子,前院是水泥地,旁邊樹下有一座抽水井,年輕的一輩都到城市發展成家去了,留下一個無伴的老人看家。盧生走近來時看到那位和善的老頭蹲在屋簷下剝花生。這老頭非常高興有盧生這樣溫馴和教養的男人來共住這一幢半廢的屋宇。盧生和這舒坦的老人例行地打招呼後,便由大廳門口進入,走到分隔在右邊的一間臥室。那裡他鋪有一張粗糙的暗紅地氈,設有一張低矮的書桌,上面堆放著二三十本書,另有一張配合書桌的籐椅,他睡眠用的行軍床擺在靠牆的一邊,上面有布巾覆蓋著棉被。他脫掉鞋子坐進那張唯一的椅子裡,點燃一支香煙,沉靜地等待夜晚的來臨。
之後,那個男人經常出現前來與盧生在一起,大都是星期三的下午臨近黃昏的時候,他的來到總是帶給沉默寡言的盧生一點莫名的生活的喜悅。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運動夾克,一條灰褲子,臉上戴著太陽眼鏡,表情總是和善和開朗,與憂鬱的盧生恰成對比,但是當他和盧生站在一起時,二個人卻混合成一種難以描摹的奇特的形象,他們外表的個別差異仍能給人一種氣質相同的孿體的印象。他和盧生在走廊勾肩搭臂,一面說一面笑時,凡是曾經在他第一次降臨看到他而產生驚擾的人,此刻都不再感到稀奇了。他已連續在這幾個星期都來過,有一次碰巧學校開完校務會議後擧行會餐,全體教職員好客地歡迎他入座,盧生拉他坐在旁邊,那時覺得他奇怪的人都幾乎把他看得清楚了。盧生向同事們介紹說,他也是一位教師,住在鄰鎮。是的,他和所有的人沒有什麼區別,在這個生活的世界裡,除了不為人知的內在外,一切的表面事物似乎是乏善可陳的。在那一次的會餐中,他和盧生的同事們互相敬酒,彷彿他也是他們中的一員,一起談論學校中所可能產生的奇怪而拗人性的規定,然後在唏噓的酒嚷中吞到肚子裡消失了。這種吃喝的場合總是喜笑和樂的,始終在半真半假的標榜或譏諷的話題中進行,甚少談論嚴肅的問題,彷彿每個人都能約制何種事體不能做認真的交談,維持一種和諧而膚淺的同事之間的關係。而這種永不傷感情的關係似乎可以保持千年恒久不變,也甚少受外界的更動或刺激而改變這種形式。在這狀如歡樂實是空寞的小天地裡,只有他和盧生卻息息相關,他隨時隨刻無不在細心偵察盧生外表擧動的內在因素,在他的眸光和鼻息中辨識出涵蘊久遠歷程的意義。他時時暗示盧生不要漫無節制地沉淪在掩蓋孤志的酒肆之中,可是盧生卻故意違逆地表現出一種隨和與順從他人的態度,且希望由這一表現激勵他自己內在的思想之光。那次酒餚之食延至夜晚猶未罷席,不斷地有在地的鄰客前來助飲,每每都能引發出一場虛誇的興潮,盧生默默如羔羊,直到他把他拖至屋外,勸解他必須離去。但頃刻有人追出,並來到他租屋的所在登門呼喚盧生,而他依然順服地與他們牌賭至黎明。
另有一次,他來時盧生即當面告訴他說,他馬上要和同事們前往附近一叫頂庄的村落去喫飲,並且說他來得正好可與他一同去。
「何事去喫飲?」他問盧生。
「據說那邊在拜拜。」盧生說。
「那邊何事在拜拜?」
「這事你總應該知道,大概是神的生日。」
「神生日?什麼神?」
「我不知道什麼神,他們要我去,我不好意思不去。」
「你總要問清楚是什麼神。」
「你知道,我並不計較那麼多,什麼神與我沒有什麼關係,我是去喫飲,不是去拜神,所有的人也都是如此,你總知道我的為人……」
「盧生,你不要去,我們可以好好在屋子裡談談,補償上一次,不是嗎?」
交談之中有一位爽朗的男同事從走廊經過,看到盧生和他的朋友在談話,便招呼他,要盧生等一下也把朋友一同攜去。這位男同事步伐健飛,理直氣壯地命令了之後,就走開了。
盧生說:「你現在看到了罷,你總該明白我在這裡任何大小事情,都無法明明白白地馬上顯示我個人的肯確態度,像類似喫飲的好事,更加無法不表示喜悅和贊同。」
「但這種喫飲有何趣味呢?」
「我的朋友,當你說到趣味來,做為一個人要是認真的去思考,沒有一樣事是有趣味的,凡是做過的事,沒有事後不反悔的。」盧生慨然地說。
「那麼你去我不去了。」他說,並且準備轉身離去。
盧生把他拉住。
「等一下,你知道,我內心也十分厭煩這類的喫飲。」
「那麼何不不去,如要飲酒,我們可以敘飲一番。」
「我當然願意這樣,但是你還不明瞭我的話,如果你為我設身處地著想的話,你就不會勸止我去做那些也頗富於情理的事。」
「盧生,你的所謂富於情理是指何而言?」
「你聽我說,無論人與人之間多麼有差異的區別,有些事是有共義的存在;譬如神的生日設喫飲的事而言,各地習俗普遍相同,這一村到另一村互相交流,相等於安排生活的消遣。就功利的觀點來看,我這沒有家庭溫暖的人可以省掉了自己去做一餐飯,對那些每天都要乖乖地回到家裡去吃單調的晚飯的人,可以有一次解除苦悶的豪放;所以他們看重這類喫飲的事,不去參與等於昧於人事,為何我們何樂不為呢?」
於是他們加入了前往的行列邁往頂庄,在路上又與其他同樣目的步往的人匯集成浩蕩的一羣;到了頂庄各街各巷都壅塞著來自他地的食客。他們早就忘掉了這是為何神而來喫飲,因為相識而招呼交談的人,並不談神的話,而只關照人間的事。他們早已安排好先到那一家,再到那一家,盧生甚至不知道神在何處,他漠不關心地與眾人飲到深夜,都酩酊大醉了。此刻,每個人似乎蠻痛快地也心甘情願地步上回程,且在途中互相告別分手了;如此一天的逝去,猶如人一生的消失。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銀波翅膀的圖書 |
 |
銀波翅膀 作者:七等生 出版社: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2-1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小說 |
$ 252 |
現代小說 |
$ 280 |
文學作品 |
$ 28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8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銀波翅膀
致敬 七等生
超越時代的前行者
他的創作歷程示現了幻譎奇偉的生命之歌
「『銀波翅膀』像他們心中所希望的光,他們詭祕地一個傳給一個這久盼的信息。於是他們全都狂喚地衝下奔向湧來沙灘的漲高的浪潮……」--〈銀波翅膀〉
一九七九至八四年七等生中期創作的十七篇小說,包括〈銀波翅膀〉、〈途經妙法寺〉、〈等待巫永森之後〉、〈老婦人〉、〈行過最後一個秋季〉、〈環虛〉、〈連體〉等。
七等生認為,寫作是平庸者茍且存活的方法,但也是為了了解自己。其小說以特殊的敘述風格與切入觀點,使閱讀心緒與人物緊密結合。
青年教師盧生的苦悶;憂心幼兒狀況的老母親詹氏素妹;在車站前等待友人時的諸多聯想;南下探視兒孫的阿婆;在異國愛城求學與戀愛的我……傳達出七等生對生命的思索,與自己、他人、世界的各種格格不入及反抗。
作者簡介:
七等生
本名劉武雄,1939-2020。生於苗栗通霄,台北師範藝術科畢業。自1962年首次在《聯合報》發表短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起,共發表124篇小說、137篇散文(含雜記、序文),及56首新詩。1989年重拾畫筆,將創作重心轉向繪畫,於1991、92年舉辦過兩次個展。
1966、67年連獲第一和第二屆台灣文學獎。1976年獲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1983年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約訪美。1985年獲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和吳三連文藝獎。小說作品《沙河悲歌》、〈結婚〉亦曾改拍同名電影、電視劇等。2010年獲頒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
國內外學者和研究生論文超過百餘篇,允為台灣當代文學最重要作家之一。
章節試閱
銀波翅膀
一個有霧的午後,盧生遽然自生地看到一個友人的形象走來,他的外表閒散,但面目卻帶著詭譎的探索。這是盧生自去年來到海濱的小學校任教以來首次有訪客前來。盧生原是城市裡的一所中學的資深教師,他的妻子發現他與一位年輕的女教師產生戀情,將此事告到校長那裡去,當校長將那位女教師解聘時,盧生憤慨地同時辭職,但幾經另謀職業的奔波後,他疲倦而心灰意冷,斷然獨自到這個偏遠的海濱的小學校權充一名教員,暫時擺脫了和妻子在家裡的不愉快。這個前來的人是盧生久遠前的好朋友,曾在城市結伴交遊過一段頗長的時光,那是在他們...
一個有霧的午後,盧生遽然自生地看到一個友人的形象走來,他的外表閒散,但面目卻帶著詭譎的探索。這是盧生自去年來到海濱的小學校任教以來首次有訪客前來。盧生原是城市裡的一所中學的資深教師,他的妻子發現他與一位年輕的女教師產生戀情,將此事告到校長那裡去,當校長將那位女教師解聘時,盧生憤慨地同時辭職,但幾經另謀職業的奔波後,他疲倦而心灰意冷,斷然獨自到這個偏遠的海濱的小學校權充一名教員,暫時擺脫了和妻子在家裡的不愉快。這個前來的人是盧生久遠前的好朋友,曾在城市結伴交遊過一段頗長的時光,那是在他們...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生命裡不免會有令人感到格格不入的時候,彷彿趔趄著從一眾和自己不同方向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然而如果那與己相逆的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一整個世界,這時又該如何自處?一生以叛逆而前衛的文學藝術屹立於世間浪潮的七等生,就是這樣一位與時代潮流相悖的逆行者。他的創作曾為他所身處的世代帶來巨大的震撼、驚詫、迷惑與躁動,而那也正是世界帶給他孤獨、隔絕和疏離的劇烈迴響。如今這抹削廋卻獨特的靈魂已離我們遠去,但他的小說仍兀自鳴放著它獨有的聲部與旋律。
該怎麼具體描繪七等生的與眾不同?或許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出版前言 削廋卻獨特的靈魂
銀波翅膀
途經妙法寺
夏日故事
等待巫永森之後
老婦人
幻象
憧憬船
我的小天使
哭泣的墾丁門
木鴨、沙馬蟹和牛仔的故事
李蘭州
真真和媽媽
克里辛娜
行過最後一個秋季
垃圾
連體
環虛
銀波翅膀
途經妙法寺
夏日故事
等待巫永森之後
老婦人
幻象
憧憬船
我的小天使
哭泣的墾丁門
木鴨、沙馬蟹和牛仔的故事
李蘭州
真真和媽媽
克里辛娜
行過最後一個秋季
垃圾
連體
環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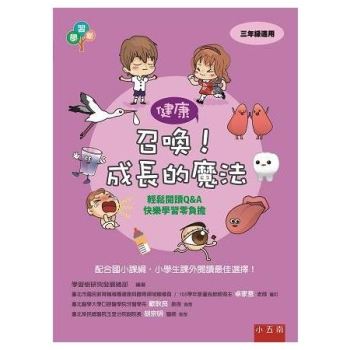









![114年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專業軍士官] 114年智力測驗快攻搶分要訣[專業軍士官]](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