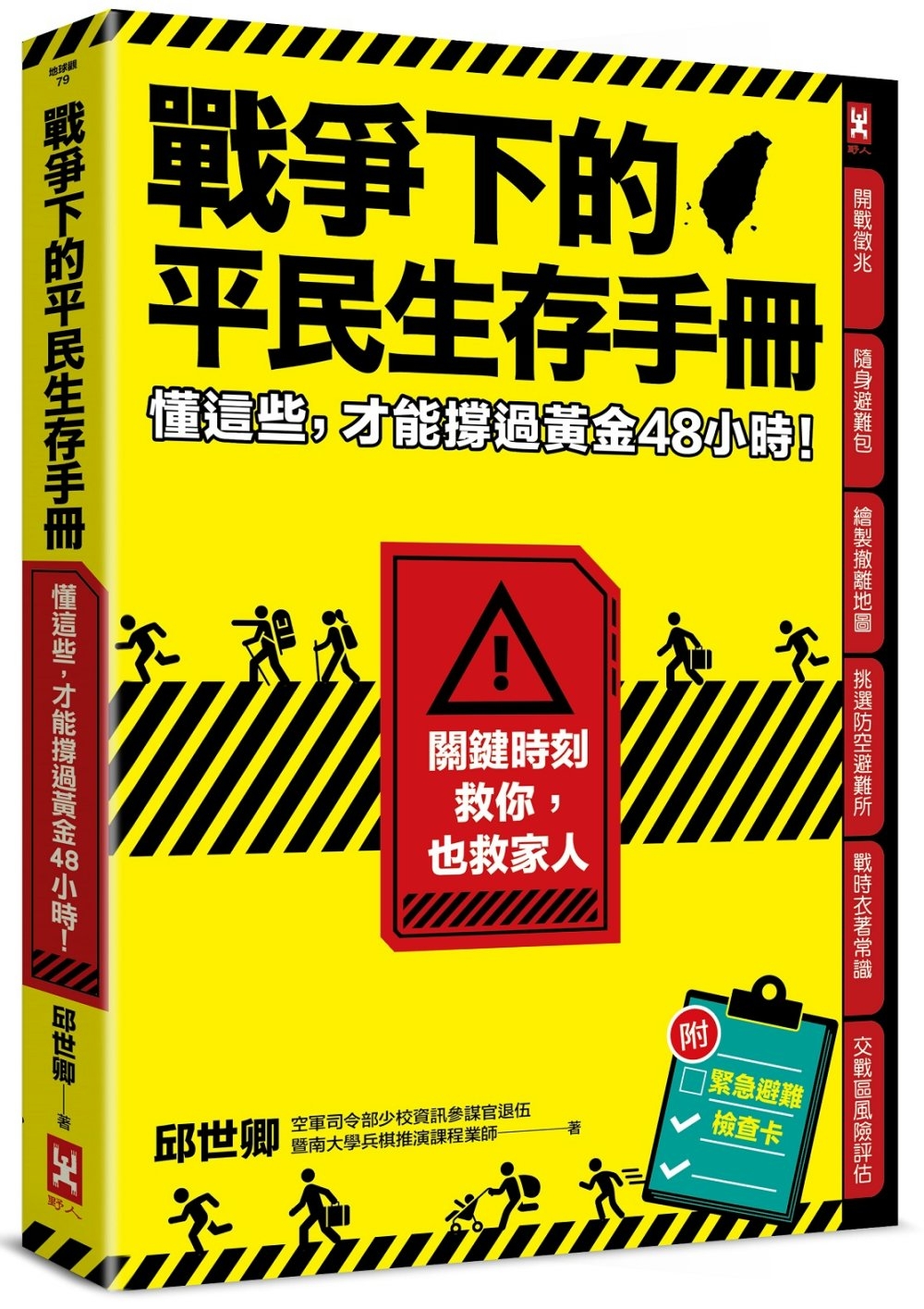圖書名稱:放逐與王國
極致輝煌下的細緻光影,
存在主義文學大師最後的放逐與追尋!
生命的沉重,錯亂和凝固的生活,對生存和死亡的憂愁……
過去的歲月、習慣和愁悶,都在這裡慢慢解開了。
如今,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根,不再顫抖。
因《異鄉人》夙負盛名的存在主義文學大師卡繆,於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聲望如日中天,然而幾年後旋即因意外溘然長逝,為世界文壇和讀者留下無盡的遺憾與悵惘。在這有如星光般迅疾閃逝的短暫輝煌裡,留有一道細緻卻不被記憶的光影。
作為卡繆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與獲得諾獎同年出版的《放逐與王國》,似乎一直沒有受到更多的重視與評價。走過《異鄉人》的人性絕境和《瘟疫》的生存掙扎,《放逐與王國》究竟透露了怎樣的追尋與探索?
本書透過六個短篇,分別描述了人們在不同狀態下所面臨的不同孤寂──一種為人世所放逐的歧杈和荒涼。困在徒具形式婚姻裡的女子,精神錯亂的叛教者,與資本家周旋挫敗的工人;又或者是孤絕的人道主義者,看似一帆風順的藝術家,自我流放的工程師……每個人都自人世的某個面向脫軌,卻也在這樣歧出的歷程中找到某種自我歸屬,即便那歸屬依然不甚為人世所理解……
作者簡介
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
1913年出生在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出生一年即成為戰爭孤兒。父親死後,與母親及外婆相依為命,在極為惡劣的窮困環境中長大。
卡繆自1932年起便開始發表創作,1942年以《異鄉人》名聲鵲起;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1月不幸在法國南部公路上死於一場意外車禍。
著有小說《異鄉人》、《瘟疫》、《墮落》、《快樂的死》等;散文集《反抗者》、《薛西弗斯的神話》等。描寫其父生平事蹟、未完成的小說遺作《第一人》於1994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放逐與王國》為其生前所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
譯者簡介
劉森堯
台灣東海大學外文系學士,愛爾蘭大學愛爾蘭文學碩士,並於法國波特爾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著有《電影生活》、《導演與電影》、《天光雲影共徘徊》,譯有《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威瑪文化》、《啟蒙運動: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閒暇》、《歡樂時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