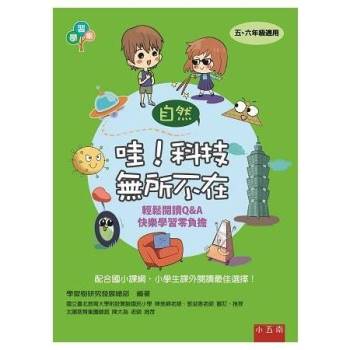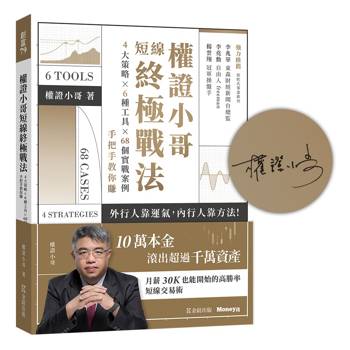繼《革命與詩》、《深淵與火》之後,「晚秋書」系列最終篇章,邀您一同品味晚境人生的至醇絮語。
所有的風聲與水聲依舊還是那麼清晰,
只是那段生命已經徹底消失。
只剩下這些文字,仍然有跡可循。
從政治場域的翻騰到文學堂奧裡的沉澱,從《謝雪紅評傳》到《台灣新文學史》;走過多少歲月寒暑,歷經無數次邊境往返,遍嘗人世滄桑。透過閱讀與書寫,作者攀附著文字終於找到生命的歸向。
那是文學靈魂匯聚閃爍的燈塔,是眾聲喧譁、繁花似錦的文學靈光。藉著這道光,令他得以卸下塵世政治的紛擾,在台灣最珍貴的文學靈魂之間,恣意探險,訪勝尋幽。在未知的內在境遇裡,每一次的閱讀都是自我邊境的跨越,每一次的書寫都是人格的再造與重鑄。
本書收錄了作者近三年的散文創作,時空跨度自一九八九年返台前夕開始,迄及此刻的人生晚境。其中越渡了《謝雪紅評傳》開筆、決意返台、政黨選舉的波濤、《台灣新文學史》的寫作挑戰等,作者個人生命的跌宕與轉折;同時也見證了九二一地震、太陽花學運、婚姻平權運動等台灣當代重大的歷史時刻。如今在人生向晚時分,盡皆醞釀成為至醇至真的生命絮語。
作者簡介: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著作等身,包括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革命與詩》、《深淵與火》;詩評集《詩和現實》、《美與殉美》;文學評論集《晚秋夜讀》、《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星遲夜讀》、《晚秋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灣新文學史》,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學者的研究典範。獲二○一六台灣文學金典獎。
章節試閱
靜靜的舊城校園
1
終於完成《謝雪紅評傳》時,彷彿是克服一場艱難的障礙賽。從一九八七年開筆撰寫到一九九一年全書殺青,前後橫跨四年的時間,也是我進入中年時期的一個挑戰,更是總結我在海外流亡十八年的一個勞作。從來沒有想過這本書會耗去我長久的時間,終於寫完的那個剎那,似乎有一種獲得解放的快感。那年到達四十歲時,已經強烈意識到即將迎接人生的下半場。在那之前,我的歷史研究始終徘徊在第十世紀到十二世紀的宋代中國。那是我學術研究的一個轉向,也是我精神航行的一個回鄉。當初開始撰寫時,以為只需要十萬字就可以有一個交代。伴隨著書寫的進行,許多未曾預料的文獻與書籍不斷浮現。最初有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只要把台灣總督府編纂的《台灣警察沿革誌》全部爬梳,大約就可掌握謝雪紅前半生的跌宕起伏。後來才訝異察覺,我似乎捅到一個蜂窩。
以書寫來刻畫自己的生命進程,是在微近中年之際慢慢養成。真正意識到以書寫形式作為不同年齡的里程碑,我已經在海外流浪十年了。一九九一年寫完這部傳記時,我好像經歷了漫長的考驗。心裡總是有一個聲音告訴自己,如果可以回到台灣,究竟會交出怎樣的成績單。這部評傳就是我要呈現給故鄉的作品,而且是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回航海島。在此之前,我是右派的思考者,也是男性的書寫者,更是中國的信仰者。在此之後,我已經具備了左派觀點,也具備了女性觀點,更具備了台灣觀點。這是我生命中非常關鍵的迴旋,從此開始主導我未來的創作與學術。跨過一九九○年代之後,我已經看見台灣正朝著全新的方向航行。我無法原諒自己繼續留在海外,更無法原諒自己向台灣繳了白卷。
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回到台灣時,非常感謝一位朋友陪伴我講話。從下午一直到黃昏之後,我到現在還是清楚記得那個場景。從未謀面的初安民,邀請女性詩人沈花末來我的住處見面。那天房子的主人陳永興恰好不在,初安民與我第一次見面,相談甚歡。那時他是《聯合文學》的主編,我未曾在他的雜誌寫稿。但是他像故人一般,很親切與我談話。那是我返台後所認識第一位陌生的朋友,他在《聯合文學》工作,屬於《聯合報》系統,在當時也是把我視為假想敵的半官方媒體。初安民好像不為所動,在談話間不斷邀請我為這份雜誌寫稿。在夏天一個
返鄉的陌生旅人,心情不免有些浮動,卻因為與這位年輕編輯靜靜談話,整個心情都穩定下來。後來他才讓我知道,原來是畢業於成功大學中文系,是一位從韓國回來的僑生。他已經定居下來,也把自己定位為台灣人。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對我在海外所寫的散文頗多注意。
一九八八年還未回鄉之前,林佛兒所主持的林白出版社,特地為我的散文與評論結集。一本是以陳嘉農為筆名的散文《受傷的蘆葦》,一本是以宋冬陽為筆名的文學評論集《放膽文章拚命酒》。那是我離鄉那麼久之後,第一次化名重現台灣文壇。初安民與我對談時,似乎特別欣賞我所寫的散文。總覺得自己已經被故鄉忘記,甚至覺得沒有多少舊識敢於前來相認。初安民是我少數認識的新朋友,卻對我表達相當的信任。他甚至也說,希望我能夠為《聯合文學》撰稿。在那時刻,內心頗為感動。至少還有一位編者扮演讀者的角色,肯定我的作品。我不知道如何解釋那時的心情,極為感動甚至有些激動。在海外一個人默默孤獨地書寫,其實從來不會期待有人會讀我。在那麼久的時光裡,總是覺得自己是被遺棄的人,甚至是被整個世代放棄的剩餘與多餘。那時年輕的初安民毫不畏懼與我相見,前後大約有四五個小時之久。望著窗外天已經黑了,我邀請他一起晚餐。但是他說,要趕回去編輯部,我才知道他是抽空出來。
那年夏天的黃昏夜空暗得好快,我的內心卻亮起來。至少在那麼大的台北盆地,還有一位文學編輯默默關注著我,也默默閱讀著我。他是我新認識的朋友,卻開啟了我後半生長期的友誼。那年以思想犯的身分回到台灣,年過四十二歲。生命底層不免燃燒著一些焦慮,常常在望著台北夜燈的時刻,總會不斷追問自己,生命是不是從此就這樣定型,是不是永遠要扮演著被遺棄的角色,是不是永遠被迫拘禁在海外,而終於注定在另一個海岸瞭望台灣。每思及此,就有一種不明的恐慌降臨在周遭。初安民來訪的時刻,使我又對自己產生信心。一位在台上表演的舞者,即使整個廳堂只剩下一個觀眾在觀賞,那樣的表演就值得了。而一位作者書寫文字時,如果只剩下一個讀者在閱讀,應該就可以繼續勇敢寫下去。在返鄉最孤獨的時刻,這位年輕朋友適時出現,簡直是伸出有力的手臂,把我從深淵中拉了一把。
我對整個風貌改變後的台北似乎有一些茫然,總覺得自己雨落大海那樣完全消失不見。整個文壇風景也完全改變了,許多新作家不斷崛起,我更覺得陌生無比。那時一批新的寫手已經登場,包括張大春、楊照、林燿德、朱天文、朱天心。他們作品中所書寫的語法,已經不是我所熟悉的現代主義風格,更不是我已經習慣的鄉土文學味道。他們大約都是一九六○年代出生,比起我的世代,他們的作品更加開放、更加灑脫。我回來時,台灣已經解嚴兩年,整個文壇的空氣顯得特別活潑。對他們而言,我就是陌生人。在誠品書店、金石堂書店,我努力購買年輕作者的書籍,並且在晚間認真閱讀。台灣文壇已經換了一批陌生面孔,只能站在外面閱讀他們的作品。
我確實是一個陌生人,當時所聽到的音樂卡帶也換了一批陌生的聲音。最常聽到的歌手,無非是蔡琴或鳳飛飛。全新面孔的浮現,似乎在宣告我的時代已經完全過去。那麼大的台北市,只是多出了一個像我這樣的陌生人。內心深處升起了一個焦慮的問題,我必須重新再來,必須以新的文字、新的作品證明自己的存在。我是完全死去的人,只是魂魄重新歸來而已。我的前生已經變得虛無飄渺,我的今世卻不再誕生。坐在咖啡室裡,閱讀每份報紙的副刊,那些作者於我都是陌生人,完全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多餘還是剩餘。在別人眼中,我只是一縷幽魂而已,不多也不少。如果要真正活過來,就必須回來海島的土地重新扎根。那時才強烈感覺到,我不僅僅是一位放逐者,更是一位被棄者。體內的血液脈搏再也不是跟著土地的節奏一起跳動,我是不折不扣的畸零者,更是遭到棄擲的異鄉人。我的在與不在,完全與自己的土地毫不相干。
2
在台北停留一個星期後,我必須回到故鄉左營探望自己的父母。我大哥親自開車,載著我與兩個孩子一起南下。南北高速公路的兩旁風景,於我是完全陌生。童年時期曾經與父親一起北上,乘坐縱貫鐵路的快車,徹夜奔向台北。父親為了節省投宿旅館的錢,總是選擇在火車上過夜。那時鐵路已經電氣化,毋需擔心蒸汽機冒出的黑煙撲面而來。父子兩人擠在一張座椅上,從未有過安眠。那是父親生命裡最辛苦的歲月,卻為了滿足孩子對台北的好奇,總是帶著我一起北上。縱貫鐵道是由日本人鋪成,每次經過勝興車站時車速特別慢,因為要通過山洞與橋梁。半夜裡火車渡河時,都可清楚聽到枕木所傳出壓軋的聲音。那是我童年時
期最難忘懷的記憶。
與大哥驅車南下,後座的兒子與女兒也非常好奇,注視著他們父親的故鄉土地。車子跨過大肚溪進入彰化以後,就可以看到非常廣闊的綠色田野。車子朝向彰化平原前進時,不久就跨越濁水溪。從車窗放眼望去,河床亂石累累。那個時節大約還未出現山洪暴發,低淺的水流在沙洲之間蜿蜒穿越。我心裡很明白,跨過這條溪流之後,廣闊的嘉南平原就要在眼前展開。猶記得在史丹佛大學圖書館閱讀台灣歷史,從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到馬偕的《台灣遙寄》,都提到濁水溪的水流。最早的荷蘭地圖曾經把福爾摩沙畫成南北兩塊島嶼,也許他們最早到達台灣的時候,濁水溪洪水滾滾,他們誤以為是兩個海島。那些閱讀的記憶,帶著我重新認識我島國的地理形勢。如今在高速公路目睹這條壯闊的河流出現時,更加覺得自己是何等渺小。見到夢想中的濁水溪,心情有些激動。離鄉那麼久,終於探測出我對台灣土地的感情。噙著淚水,我注視著濁水溪在車窗外呼嘯而過。我不敢回頭看駕駛中的大哥,還有後座的兩個孩子。那種感情只屬於我私密的內心,只能暗暗消化在起伏的情緒裡。
我似乎聽到後座的兒女發出驚呼,這是他們生命中第一次看見台灣。中央山脈伴隨著高速公路一起向南奔跑,離鄉那麼久,終於看見那屬於台灣土地的綠,眼睛不禁湧出淚水。曾經在加州的書窗裡寫過一篇散文〈深夜的嘉南平原〉,那種想像都在眼前得到印證。大哥驅車相當順利,早上八點從台北出發,下午兩點就進入高雄了。他選擇在楠梓交流道出去,沿著中油公司牆外的那條公路直奔左營。所有的景觀已經改變,再也不是我熟悉的風景。車子停靠在左營大路的家門前,竟然於我是完全陌生。那一排瓦屋仍然還保持原樣,而我卻無法辨識。畢竟離鄉已經超過十五年,所有的景物在記憶裡都已經變形。記憶的錯亂再次證明,我是不折不扣的異鄉人。
進入家門,我走上後棟的二樓。那水泥階梯是我年少時期上上下下走過,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迫不及待在樓梯口就高呼爸爸媽媽。他們兩人已經坐在客廳等待,看到我出現時,卻立刻問我兩個孩子呢?十歲的男孩、七歲的女孩,立刻走過去與他們擁抱。女兒似乎有些羞澀,卻壓抑不住她神情的興奮。終於回來了,終於回到父母的身邊。長期離開台灣,我一直有深刻的體會,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故鄉。七月的南台灣特別悶熱,似乎只有客廳才有冷氣,全家圍坐在沙發與藤椅。父親與母親搶著要跟兩個孫兒說話,而且都是使用台語提問。兩個孩子似懂非懂,也盡量用生澀的台語回答他們。再過不久,孩子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裡,開始在樓上樓下奔跑。父母在家裡也許寂寞許久,聽到孩子的聲音,心情特別愉快。他們在茶几準備許多台灣的土產甜點,兒子好像特別喜歡。當他們開始接受故鄉的食物,似乎整個情緒也穩定下來。
晚上睡覺時,我與兩個孩子分配在三樓的房間。那是我高中時期的寢室,尤其在聯考前的半年,幾乎每天清晨五點半就起床,完全是為了背誦英文單字。當年左營的小鎮風光,還保持著素樸狀態,周邊並沒有任何高樓。兩個孩子睡在隔壁的房間,而我直到深夜久久未眠。可能心情太過興奮,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經回到故鄉。左營的夜晚特別寧靜,覺得應該給自己一個安詳的時刻。第二天清晨五點,睡夢中隱隱聽到後院鄰家的雞鳴。那麼多年,從來沒有聽到這樣熟悉的聲音。似醒未醒之際,淚水不禁流下。那好像是一種親情的呼喚,對著我內心的幽谷傳送。清晨雞鳴的聲音,在毫不設防的時刻就觸動了我脆弱的感情。在半醒之間我告訴自己,終於真正回到故鄉左營。這小小的市鎮,見證過我走到舊城國民小學的身影,也看過我騎車到左營中學的背影。整個青春時期經歷了知識啟蒙與政治啟蒙,在這個安靜的故鄉,容許我幼小的身軀慢慢變成青年體魄。我總覺得蓮池潭旁邊的那一排朽舊城牆,就是我生命的護城河。
在雞鳴中拭去淚水,我迎接了回到故鄉的第一天。我答應孩子要帶他們去看蓮池潭,也要去看水中的半屏山倒影。那天早上,帶著兩個孩子穿越那古老的菜市場。最初的記憶,這市場一直都那麼髒亂。通過市場的走廊,依舊潮濕,而且空氣中可以嗅到發霉的味道。販賣肉粽、肉圓、碗粿的攤位,還是擺在原來的地方。童年時期的許多記憶,竟然還那麼完好地保留下來。我的孩子非常好奇,站在那裡觀察許久。依稀中,彷彿就是我童年時期複製的身影。他們在加州非常喜歡去超市,從來沒有想過台灣的傳統市場是那麼好玩。他們甚至蹲在路邊,看到賣金魚的攤販勾起他們的好奇心,蹲在那裡圍觀許久,遲遲不想離去。在那附近也看到一攤販賣火龍果,那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離開台灣之前,從來不知道有這種水果。紅色的果皮在陽光下特別亮麗,周身的果刺張牙舞爪,使我感到非常訝異。離鄉太久了,有太多細節變化完全改變我的記憶。
穿過市場之後,我選擇曾經穿越的小巷,終於經過城隍廟。那是小時候最喜歡與同學探險的地方。那時常常走進廟裡,去看七爺八爺的廂房。窺探了白臉吐舌的七爺,面孔漆黑、眼睛猙獰的八爺,總會驚聲尖叫,然後拔腿而跑,那是幼小心靈最早的冒險。我也帶著兩個孩子去城隍廟拜拜,但是沒有帶他們去看七爺八爺。然後繼續沿著小巷,一直走到舊城國小。走進去時,頗覺陌生。所有的建築已經完全改變,只有校園內的孔廟與那棵榕樹還在。那株榕樹是永恆的記憶,那種開枝散葉的盛況,勾起童年時期的浮光掠影。孔廟的建築格局有限,那是清朝時期遺留下來的古蹟。左營的孔廟已經遷到半屏山下,校園裡舊有的規模似乎已經沒落。孔子與弟子的牌位全部都移走了,只剩下空蕩的廊柱。我在這個屋簷下度過幼稚園時期,那是我接受知識教育的最早階段。坐在紅色的地板上,忽然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在這裡接受完整的小學教育,也在這裡結識許多幼年時期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叫謝新達,也是一九八○年代家喻戶曉的豬哥亮。在同一個學校度過童年時期,但最後都擁有不同的人生。我走過教室的走廊,從窗口望進去,才發現桌椅那麼矮小。簡直不敢相信幼年的自己,可以坐在格局如此有限的小椅上。我的知識旅程確實是從這裡出發,從來未曾想像過,會經過那麼多危險的道路。旅途上的風雨,讓我嘗盡了苦澀、訝異、惆悵與驚喜。終於回到母校時,我已經是四十二歲的中年。怔忡站在走廊許久,我很懷疑自己回到了故鄉,更懷疑自己是不是能夠回到自己的土地安身立命。我生命中夢想的原型,原來都是從這裡釀造出來。生命中有太多的回不去,也有太多的過不去。在那時刻,我下定決心,有一天一定要回到台灣歷史的現場,重新開啟我未來的人生。
二○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政大台文所
靜靜的舊城校園
1
終於完成《謝雪紅評傳》時,彷彿是克服一場艱難的障礙賽。從一九八七年開筆撰寫到一九九一年全書殺青,前後橫跨四年的時間,也是我進入中年時期的一個挑戰,更是總結我在海外流亡十八年的一個勞作。從來沒有想過這本書會耗去我長久的時間,終於寫完的那個剎那,似乎有一種獲得解放的快感。那年到達四十歲時,已經強烈意識到即將迎接人生的下半場。在那之前,我的歷史研究始終徘徊在第十世紀到十二世紀的宋代中國。那是我學術研究的一個轉向,也是我精神航行的一個回鄉。當初開始撰寫時,以為只需要十萬字就可以有一...
作者序
最後那盞燈
──《邊界與燈》序
到達晚歲的邊境,不知道前面還有多長的路需要追趕。從前計算時間的方式,大約多是每十年作為一個階段。如今跨過七十歲,再也不可能以十年的跨度來計算。六年前開始撰寫「晚秋書」的專欄,總覺得生命的旅途還可以繼續追趕。每兩年完成一部散文專書,從《革命與詩》到《深淵與火》,就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的書寫工程。第三部《邊界與燈》,終於也寫好最後一篇,我才驚覺六年的速度稍縱即逝。所有的文字都只是時間的痕跡,彷彿是沙灘的腳印那樣,可以看見最早的起點是如何蜿蜒展開。海水的漲潮與退潮,終究會把沙灘的痕跡擦拭得乾乾淨淨。站在時間的盡頭這邊回望,所有的風聲與水聲依舊還是那麼清晰,只是那段生命已經徹底消失。只剩下這些文字,仍然有跡可循。時間就是潮水,無論留下足跡或字跡,最後終究會被沖刷而走。
身為文字書寫者,永遠都是心有未甘。不同年齡層所留下的文字,最後都被時間的大海所吞噬。生命底層總是存留一些頑強的抵抗,不免懷抱著希望緩慢一點遭到洗刷。至少容許那些文字,變成一部書籍,讓時間轉換成空間,至少還可以留存久一點。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說過,每一部書都可以視為墓誌銘,記錄著過往歲月的轟轟烈烈,只要不致過於潦草,多少還是可以窺見自己的背影。最初寫下第一篇時,總覺得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需要追趕。面對一大片生命的草原,總覺得需要跋涉前進。如今終究也到達了邊界,也到達了時間的峰頂。即使雲層或迷霧遮去了望眼,內心卻非常明白,已經到達一個毋需辯論的境界。
俯望山下的世界,都可以辨識清楚,在怎樣的年齡到達怎樣的高度。前後三本散文集,耗去我六年的時間。眼見自己的友朋次第退休,我仍然還留在學校任教。那份眷戀,全然是由自己的閱讀癖與書寫癖延伸而來。坐在文學院的樓頭,也坐在時間的盡頭,文字與書籍為我開啟了一個無窮無盡的世界。閱讀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時間的旅行,也是一種空間的旅行。完成一部書的閱讀,通常需要兩天的時間。在最深的夜裡,能夠與作者獨處,並且也進行對話,那可能是我生命中極為幸福的時刻。因為幸福,所以不捨。結束對話後,便是動筆書寫書序或書評的時刻。
文學院的樓頭,總是亮著一盞燈。無論是霧氣襲來或雨聲降臨,似乎都是在釀造閱讀時刻的氛圍。第一次到達這個山上的校園時,已經是五十三歲,晚境已然在望。那時已經隱藏一場漫長的追逐,許多夢的企圖等待我去實現。遠離政治之後,讓我有一種浴火重生的感覺,覺得自己的生命不再輕易浪費。我總是把山下的那一條景美溪,視為一道護城河。繁華的城市燈光,總是在遠處閃爍。坐在林蔭樹下的書窗,心情平靜如水,那是最好的思考空間。二十年匆匆過去,自己也從中年跨向晚年,浮動的情緒隨著歲月慢慢沉澱下來。熱情猶在,思考也還在。如今到達生命的晚期邊界,許多夢想已多過濾淨盡。這個座標曾經非常遙遠,如今終於也到了跨越的時刻。
從前有過太多的夢想與幻想,不時可以營造,不時也可以放棄。那是奢華時代的特權,營造一個夢又一個夢。在生命過程中確實有太多的海市蜃樓,只覺得歲月還正漫長,都輕易容其幻化。那時跨越許多邊境與疆界,每次告別一個城市時,都會暗自告訴自己還會再回來,那真的是非常豪邁的時期。走到今天,才察覺自己已經不可能如此奢侈。那時常常攤開地圖,尋找下次即將旅行的城市。甚至也會去尋找,那城市的經緯度。有一年到達喬治亞州的首府亞特蘭大,特別去拜訪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的墳墓。那時是夏天,整個城市非常悶熱,而且汗水濕透了內衣。他的墓座落在藍色池水的中央,莊嚴而親民。在那時刻,才真正感受了美國歷史的莊嚴與偉大。於我而言,那也是一次邊境旅行。終於觸及了黑人文化的靈魂,完全化解了自己從前的膚色偏見。
生命的邊境無所不在,從膚色到族群,從性別到階級,都是在漫長的旅途中逐漸跨越。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從來都是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盲點與偏見,也往往是從知識養成過程中慢慢形成。如果未曾到達,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知識。對於生命的理解,也必須真正穿越過,才會發現自己的未知與無知。年輕時期耽溺在宋代歷史的知識,卻從未造訪過北宋的開封,或南宋的杭州。那樣的知識旅行,不僅沒有攜帶地圖,也未曾到達歷史現場。終於在跨過中年之後,才知道那樣的知識追求只是一場徒勞。終於回歸到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生命早就跨過中年的邊境。彷彿是作了一場虛幻的夢,終於察覺自己深陷在時間的迷宮。
回到台灣文學的場域時,才察覺自己所追求的知識終於都點亮了。穿越那麼多邊界之後,也經過那麼多的迷路與摸索,才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安頓。站在生命這頭,再次回望迢迢的路程,更加明白自己所穿越過的關卡。從前的許多驚險,都化為如今的文字,彷彿自己的靈魂也都馴服下來。站在歲月的邊界,選擇這些文字記錄自己的跋涉過程,無非是點燃一盞盞燈,照亮過去的來路。前面還有多少旅程要追趕,似乎還無法辨識。站在這個時間的邊界,能夠暖和自己的靈魂,唯有繼續追求知識,勇敢走下去。
二○二一年二月一日 政大台文所
最後那盞燈
──《邊界與燈》序
到達晚歲的邊境,不知道前面還有多長的路需要追趕。從前計算時間的方式,大約多是每十年作為一個階段。如今跨過七十歲,再也不可能以十年的跨度來計算。六年前開始撰寫「晚秋書」的專欄,總覺得生命的旅途還可以繼續追趕。每兩年完成一部散文專書,從《革命與詩》到《深淵與火》,就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的書寫工程。第三部《邊界與燈》,終於也寫好最後一篇,我才驚覺六年的速度稍縱即逝。所有的文字都只是時間的痕跡,彷彿是沙灘的腳印那樣,可以看見最早的起點是如何蜿蜒展開。海水的漲潮與退潮,...
目錄
序 最後那盞燈
靜靜的舊城校園
盛夏的左營陽光
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下
意外的東京之旅
初訪上海
在魯迅墓前
寒山寺之行
時代轉彎的時刻
歷史之旅的終結
罌粟花的山路
一九九二年秋天
向夕陽奔馳而去
獨自面對沙鹿海岸
重新出發的喜悅
生命之秋
九二一大地震
再回傷心地
文學院的長廊
晨曦擦亮了歲月
天星碼頭
彩虹旗與太陽花
到達延安的道路
夏威夷海岸
在書架之間徘徊
序 最後那盞燈
靜靜的舊城校園
盛夏的左營陽光
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下
意外的東京之旅
初訪上海
在魯迅墓前
寒山寺之行
時代轉彎的時刻
歷史之旅的終結
罌粟花的山路
一九九二年秋天
向夕陽奔馳而去
獨自面對沙鹿海岸
重新出發的喜悅
生命之秋
九二一大地震
再回傷心地
文學院的長廊
晨曦擦亮了歲月
天星碼頭
彩虹旗與太陽花
到達延安的道路
夏威夷海岸
在書架之間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