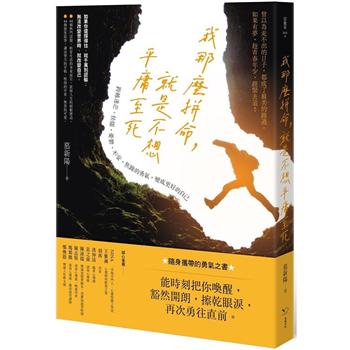序
一切都從這裡開始
朱天衣
一九五四年的台灣,距光復不到十年,離「二二八」也才八年,白色恐怖餘波盪漾,即便緝捕的對象不分省籍,但以外省人為主幹的執政者,尤其是軍隊,遂成了民間百姓怨怒對象。
我的大舅,當時不過是個高中生,就讀新竹中學,喜歡音樂、體育、閱讀,是個身心健全前途大好的孩子,只因看了幾本校內傳閱的《青年修養與意識鍛鍊》及《大眾哲學》等所謂的反動書刊,被判刑四年,送至綠島管訓。原對重回祖國心存歡喜的外公(初從南洋回來,還曾訂閱國語日報一字一字認真學習漢語),因著大舅、因著放眼所見軍紀不整諸多亂象,遂對外省人,尤其外省軍人深惡痛絕,故而說過「女兒若嫁外省兵,不如剁剁餵豬吃。」的話語。
一九四九年,還在杭州藝專就讀的父親,響應孫立人新軍徵召,棄筆從戎來到台灣,原以為兩三年便可還鄉投入反共抗俄的戰場,不想在基隆登島南下的車程中,便得知南京失守,大陸全面易幟,至此與親友音訊完全斷絕生死兩茫茫。離家前夕的日記,被淚水湮花的字跡,滿是離愁、滿是苦楚。父親最不捨的除了年邁雙親、至親手足,便是那年少戀人鳳子。
所以一九五三年,當父親來台不滿四年,在報上看到與鳳子同名同姓又年齡相仿的女孩榮獲網賽冠軍的報導時,便寫了封信至女孩就讀的新竹女中探詢可是故人否,因文采奕奕態度磊落,連學校把關的老師都放行了,至此,兩人便魚雁往返起來,而這女孩便是母親雙網搭檔劉玉蘭。
父親書信中談的多是文學,且不時寄些書籍雜誌給她。對文學並無興趣的女孩,只好抓那從小就愛讀善寫的搭檔我的母親代筆,每每父親寄來的文學雜誌書籍,也唯母親會讀,且愛不釋手。如此通信近一年,同樣出身保守客家庄的女孩劉玉蘭畢業在即,因著家庭壓力及志趣不投,遂斷了和父親的來往。
父親母親倆正式開始通信,是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也是母親高中畢業回家待職待嫁的時刻,父親的信件當然不可能登堂入室直接寄至家裡,只能轉託住在隔著鐵道另一邊的密友,也是母親爾後的大嫂、我們的大舅媽處,只要舅媽出現鐵道那頭,比出長方形的手式,母親便知道父親寄信來了。期間也曾發生郵差自作主張把信直送至外公家,幸得母親正巧在藥局幫忙攔截成功,否則後果是難以設想的,後又因種種原因,必須更換收件人名、收件地址,這書信往來真的是波折重重險象環生。
從第一封信到最後母親奔赴遠在鳳山的父親,歷時一年兩個月又二十天,留存的有一百餘封,合計近三十萬字。通信前,父母親見過兩次面,通信期間又見過兩次面,這四次會遇總是眾人一起,連私語機會都沒有,為什麼母親最終會毅然決定奔赴世俗眼中一無所有的父親,這,從他們的書信便可明白。
在那一年多的書信裡,父親亦師亦友亦父兄的與母親談文學談信仰,即便後來論及感情,他們念茲在茲的仍是文學與信仰。期間,也可看到他們努力填補兩地分隔的空間距離,父親除在每封信末註記月和日,也會將時與分寫上,為的是想知道同一時間的母親在做甚麼想甚麼。他們也曾約定某一天的某一刻,同在月下吟唱「霍夫曼船歌」,這不是一時的浪漫,事隔四十三年,父親離世前在病榻上和我談及此事,眼神恍然乍現的年輕光采,讓人動容神往。而母親在事後得悉慟說:「為什麼不告訴我,我可以再唱給他聽啊!」
世間情事無數,但那樣一個時空背景,成長環境如此南轅北轍的兩個年輕人,是如何因靈犀相通決定共負一軛結伴此生的,他們以文字記下這一切,也用其後的一生證明當時所思所想並不止於少年心志,更不是愛情囈語,而是紮紮實實的貫徹到爾後生命的每一刻。
父親啟筆動輒數千字,也因此書信累積到一個數量,母親無法藏匿,只好燒燬了一部分,這真真令人扼腕。當母親詢問父親如何處置這些書信時,父親說「致于我的書信,我倒不希望你燒了,留給我們年老的時候(我想得多遠!)再翻出來溫習我們年青時代的感情不是很好麼?哦,讓我們的子女也明白他們的父母是怎樣在困苦中奮鬥結合的,我想那對于他們是有著教育意義的。如果為著安全,不妨再寄交我來保存。如果業已燒燬,當然那也無所謂,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東西。」
人們總以為自己看到的是父母親的全貌、生命的所有,然父母意氣風發的年少、豐華正盛的青壯,孩子們多錯過且無意追尋,這會無憾嗎?因著父母親留下的最初的日記書信,為這文學朱家補上最後一塊拼圖,也如同他們在最終病榻上待我們仨陪伴、準備好才遠行一般,讓我們了無遺憾。
緣此,我們姊妹仨決定將這原屬於他們倆私密書信付梓,這些「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東西」,是我們今生聚首的緣起,而文學朱家的一切就是這麼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