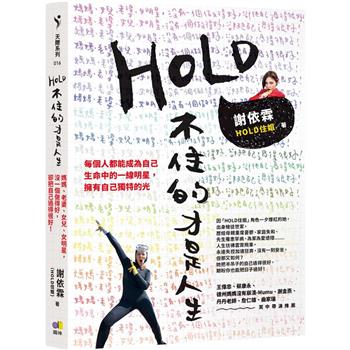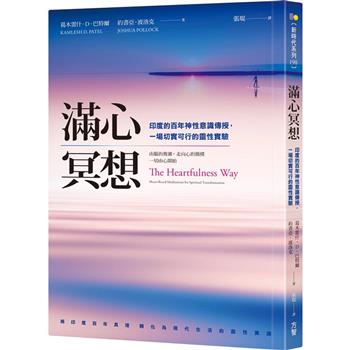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西北雨的圖書 |
 |
西北雨 作者:童偉格 出版社: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7-05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31 |
文學研究 |
二手書 |
$ 241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中文現代文學 |
$ 290 |
中文書 |
$ 290 |
小說 |
$ 297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敬啟者───我們潦草書寫:世界太大,我無處可去。
無論最後一個搬離的人離去多久,在某個黑夜與白天交替之時,當我初次站在大門口,我輕易就能察覺:它正用牆縫,用水漬,用過往一天的全部餘溫,對著我去思念他。
●朱天文、宋澤萊、邱坤良、房慧真、胡淑雯、陳淑瑤、楊凱麟、楊澤、舞鶴、劉克襄、駱以軍 誠摯推薦(依筆劃序)
我讀童偉格,視覺上那翻動著空曠的場景如此像年輕時看的塔可夫斯基;流動的詩意卻讓我想到以色列小說家奧茲,或較好時的石黑一雄……延遲,倒帶,透明,那時間與命運的畸人之「我」揹著快樂無害的他們在這片夢中荒原跑,從葬禮出逃,拉出這樣一幅浩瀚如星河,讓我們喟歎、悲不能抑、靈魂被塞滿巨大風景的「贖回最初依偎時光」的夢的卷軸。 ──駱以軍(作家)
你得要夠遼闊才能夠深邃,《西北雨》就是這樣。像大地吸收了淚水,以一種「將死之人」特有的遼闊,穿入地心,抵達文學的心臟:一種複雜無比的善良。 ──胡淑雯(作家)
一整座清釅悠長的宇宙:記憶中的事物在此散放著透亮光澤,並因此乾淨與確實存在著。這是一本關於陽光、微風、空氣與雨霧的信仰之書,生命的永恆哀痛被安靜與飽滿的文字所護衛與洗滌。我們因此懂得孤身一人卻盈溢各種細緻的身體感受,在童偉格所許諾的魔幻鄉土中,沉靜等待重生,並因生命的這個恩賜而深情的微笑。 ──楊凱麟(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童偉格知性的抒情寓言,總讓人覺得自己懂得太少,又說得太多。他的小說奇怪的靜烙快閃卻又水氣遍布,從虎年到虎年,曾經來過對誰都一樣的西北雨已不可同日而語。 ──陳淑瑤(作家)
那座聒噪的泳池底,的確藏存著世上最安靜的角落:一個極廣大的宇宙,被摺疊在泳池的偏旁。
我抬頭,看遮天的蒼老,那樣從容而別無旁騖地迴游;像上古的星河,也像史前第一道旋轉的焚風。倘若我沉落過久,總會有人記得降下他們細長的手,將我打撈上岸。總會有人邀我坐在他們身旁,給我溫熱的飲料,告知我一些離散的往事。
/
作者簡介: 童偉格
一九七七年生,萬里人,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著有《童話故事》等書,合著有《字母會A~Z》。合編有《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