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滌、打磨、沉澱、結晶。
書籍仍是人類世界最大規模明亮起來的豐饒之地。
刻舟求劍。只是船身的一道又一道愚人刻痕,我們想用它來找掉落時間大河裡的某物。至少,這些歷歷刻痕讓我們記得,曾經有這個東西,我們也一直記掛著這個東西。
奉年輕之名的自在時光該止於三十歲,或多饒五年(三十五歲),這「借來的時間」是對自己年輕身分及其一切依依告別的五年。
進入中年,世界以一種不修飾、沒粉彩、沒糖衣的硬生生面貌逼視著你,後面沒有人了。
23篇關於「年紀、閱讀、書寫」的重磅思辯,逐年增長的年紀,迫使書寫者時刻面對日益年輕的世界,最大好處是,書籍也跟著年輕起來──穩定前行的年紀,使閱讀和書寫產生了一種從容跟得上的轉動,得以一步步揭露,深入作者希冀抵達之處。後來者逐步追上,並漸趨活過,如卡爾維諾、波赫士、康德、屠格涅夫等人創作的年紀,確認對這一切,喜歡緩高於敬畏,有把握辨識出比文字更稠密的東西,並且不容易上當了。
在創作、書寫的世界,有這個接近於通則的趨向,一個真的夠好,尤其肯於持續盯住世界、盯住人的創作者,隨年紀隨著他認識的進展、隨著時間作用於他身體的種種奇妙熟成,總會緩緩走向真實世界。
*年紀
有一天,我忽然清清楚楚意識到這個應該早就如此明顯的事實──我意識到,我面對著的是一個這麼年輕的世界,並且彷彿回春,相對於我,這個世界只能一天比一天、每一樣事物不停止的更年輕起來。
從那一刻起,我把年紀這個(其實還不斷在前行、變化的)東西加進我每天的閱讀和書寫裡,是我讀和寫的新視角,以及更實體更遍在的,是新元素,每一個思維每一段文字之中都有它;而且,正因為年紀是穩定前行的,它因此給了閱讀和書寫一種難以言喻的生動感、一種你從容跟得上的轉動,好像每一次都多揭露一點點,更探入一點點。
這應該是近年來在我身上所能發生最好的事,抵銷身體衰老的種種難受還有餘。
*閱讀
時間愈拉長,書愈能顯露出它源源的、豐厚的內容,所以找書可以比找人更主動更多選擇也更準確,你愈找它就愈會找,你會感覺還有些東西──技藝、見識、鑑賞能力云云──默默在自己身作裡累積著,如多得的禮物。
師徒制至今仍然是最好的教授/學習方式,只是變得最奢侈且不易執行,我們合情合理可把這樣攜帶著的書想成是閱讀世界為我們保存的師徒制,而且非常便宜,又易於執行。
如此,你會清清楚楚體認到「成長」,你和你攜帶著書亦步亦趨,以一種幾乎可看得見可丈量、一節一節的明亮起來方式,因為這種前行包含了證實,至少告訴你並不是你一個人的胡思亂想,你確實在「某條已有人走過的路上」,這樣很讓人安心──也許更明確也更持續的成長感覺不是變大,而是變厚,變得稠密結實,人心的一處一處空隙可感的補起來。
*書寫
文字只能指示(伸手去指),它和事物的真正接觸就只是這一個點,空間的,更是時間的,變動不居的時間會又旋即把它們分開,刻舟求劍。文字根本上只能是隱喻(包含名詞其實都是),如輕紗引風,它不占領事物本身;文字也只是火花,能燃起來的還是我們心裡本來就有的東西,如果我們有的話。
這門古老的行當,所能夠做到最好的、最神奇的事,只在進入一筆一字的書寫時刻才真正發生。
作者簡介:
唐諾
一九五八年生,台灣宜蘭人,台大歷史系畢業,現從事自由寫作。不是專業球評,早期卻以NBA籃球文章廣為人知。不是專業推理小說評論者,著有「唐諾」風的推理小說導讀。不是專業文字學者,著有《文字的故事》一書,同年囊括國內三大好書獎;《盡頭》獲金鼎獎文學圖書獎;《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獲台灣文學金典獎。唯一「專業」的頭銜是作家、兼資深讀者,著有《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眼前──讀《左傳》》、《盡頭》、《世間的名字》、《讀者時代》、《閱讀的故事》、《唐諾推理小說導讀選Ⅰ》、《唐諾推理小說導讀選II》、《在咖啡館遇見十四個作家》等。
章節試閱
一直年輕起來的眼前世界
有一天,我忽然清清楚楚意識到這個應該早就如此明顯的事實—我意識到,我面對著的是一個這麼年輕的世界,並且彷彿回春,相對於我,這個世界只能一天比一天、每一樣事物不停止的更年輕起來。
我猜,這極可能就像吳清源發現圍碁新布局時的感覺,吳清源說他當時正泡在那種日式溫泉澡堂裡,「宛如天公的啟示」,就是這一句話,一道光般讓他一下子纖毫畢露的、再無一絲懷疑陰影的看清楚早已如此明擺著的事實。從此,圍碁由原來的大正碁正式進入昭和碁,進入現代。
從此,我把這一全新的世界圖像,如同聽從梵樂希的建言,「攜帶在身上」—這是我閱讀和書寫的新布局。
也就是說,從那一刻起,我把年紀這個(其實還不斷在前行、變化的)東西加進我每天的閱讀和書寫裡,是我讀和寫的新視角,以及更實體更遍在的,是新元素,每一個思維每一段文字之中都有它;而且,正因為年紀是穩定前行的,它因此給了閱讀和書寫一種難以言喻的生動感、一種你從容跟得上的轉動,好像每一次都多揭露一點點,更探入一點點。
這應該是近年來在我身上所能發生最好的事,抵銷身體衰老的種種難受還有餘。
前些時,《紐約時報》登出來一篇帶著輕輕憂慮和告誡之感的頗有意思文章,講我們當前的世界是個「太多年輕人」的世界,包括硬碰硬的人口統計數字,比方像印度這樣人們仍生個不停的大國(原是為著對抗大自然的古老生存傳種策略),這背反了我們活在台灣、在所謂已開發國家「太多老人」、已成沉重威脅的事實。但全球性的視角暨其統計顯示出另一側更大規模的真相,換句話說,人口還在增加,人類世界猶在加重試探我們這顆藍色小行星的承受能耐不休。
但我說的年輕世界不是指這個,我的年輕化世界只是來自於我的年紀,這個只進不退的東西,它在某一天抵達了某個臨界點,浮上來了,以至於,比方說早晨坐咖啡館書寫時,我發現自己總是置身於一堆年輕人及其年輕的話題之中,從顧客到店員;閱讀時,也不常再遇見年紀大於我的人了,包括書中的主人物和其書寫者—年輕的容顏,年輕式的想事情方式,年輕的欲求、判斷、憂懼、決定和其茫然,他們最常態性出錯的是對老年和死亡的猜想和描述,有時候我幾乎忍不住插嘴(當然僅限於我一人讀書時,我愈來愈少和活人爭辯),不是的,你講的未來不會那樣子發生,冷冷等在你們面前的不是如此,你這麼做不可能得到那種結果,等你年紀走到那一刻你想的不會是這些,等等,只因為,這是一再發生過的、驗證過的,不管你多不想要、多不想知道。
不只人,還有其他包括動物植物(台北市貓狗常見,近些年友善起來大量增加如觀光客的是大大小小各種鳥,還有松鼠、蜥蜴、烏龜等等),以及無生命的物體物品。我攜帶著這一發現如帶著一張新地圖四下行走,很輕易就看(比對)得出它們的各自來歷(以及一部分的未來可能命運),知道眼前這些絕大多數都是很年輕的、晚到的,舉凡行道樹、交通工具和馬路、大樓、商家和商品,以及其間人們的行為方式、習慣、姿態和神情。其中,最年輕晚到的總是一些小店家(比方小咖啡館),我甚至說得出它們何時開的店,也說得出它們大約何時會消失,一個月後、半年後云云,這是比較令人悲傷的部分,這樣開店的通常是年輕人,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的錢,虛擲只換來沮喪的生命時間,純浪費的異想天開夢想,我往往打開始就知道這必死無疑,惟無從勸阻。
還有,我現在猶居住的老屋子,已老得廢墟化了,以至於周遭短短幾十米巷道,近些年幾乎沒安靜停工的沉睡日子,總是這家沒修補完又一家,魚鱗式疊瓦式的進行。但仔細算,這是民國六十年、第二個辛亥年蓋的,峻工交屋同時隧道才打通啟用,也許因此才命名為緬懷開國先人的辛亥隧道吧(那是一個國家會要你記住較多東西的年代),然而民國六○年,我已存在這個世界很久很久了,再稍後,朱天心在這裡寫了她的第一本小說集《昨日當我年輕時》。
之前,也許是當它們是某種生命背景的緣故,自自然然結合著亙古的太陽、月亮和滿天星辰,以及山脈河流雲朵,我總不加察究的把這一切都看成原有的、既在的、而且一體成形的東西,我自己則是「闖入者」,且過客般會早一步隻身離開如《魯拜集》詩行裡說的那樣(且不管究竟會是何種方式),打擾的、異質的、移動不穩定的是我,會像卡爾維諾說的加進我再減去我。但現在,這恆定的、連綿的世界景觀分解開來了如莊子口中的那頭牛,各自單獨成物、成生命,是組合起來的,彼此之間有很大縫隙,也呈現出前後縱深;它們各有來歷,不站在同一時間平面上,也長短不一聽天由命(屠格涅夫《羅亭》裡那一句:「我們全都聽天由命。」)的各自走向消逝,這也是臨時的、偶然的、因此想必也很脆弱的搭建,或者說是我觀看者角度的不知不察錯覺而已,如同我們把彼此相隔不曉得多少光年遠的星球看成同一個星體組合,一種星象,一個神,合起來決定著我們人生福厄生死。如今,我已可以分別的、單獨的一個一個看它們想它們,如今的我比較準確。
一般,我們會把無生命的物件想成比我們自身持久,好像說沒有生也就不會有死,這泰半仍是錯覺,以及一小部分係源自於一個古老的、物件往往一代代繼承使用的已消逝記憶。於此,維吉妮亞.吳爾夫是極敏感的,她的太過敏感也令她容易感覺衰弱和提前蒼老並趨近死亡。吳爾夫參觀小說家夏洛蒂.勃朗特紀念館時有點激動,遂如此纖細的寫下來:「她的鞋子和薄紗裙子比她還長壽。」—即便仍身處那樣一個人們並不輕易用壞丟棄東西、二手市集仍是假日節慶之地的年代和國家裡,吳爾夫仍正確的感覺驚奇,並深知這非比尋常(「這些東西不應該放在這種死氣沉沉的地方,但若不是保存在這裡,多半便只有湮沒的下場。」),只因為這些個人用品、衣服、還有鞋子「照例先於用過它們的那個軀體消亡」。
吳爾夫人敏感到自己負荷不住,身體或心裡某一根細線時時屆臨繃斷。她當時應該才三十幾歲,五十九歲自殺而死,當然算早逝,非常非常可惜。
樹亦如此。我說,樹必定就是城市裡面永遠最好看的東西,沒有之一;我相信莊子若活在今日城市裡也必定這麼說,他是那個樹還毫不值錢、樹猶是人生存障礙、砍樹沒道德問題遠昔時代最喜歡樹的人,他的此一睿智和心思悠閒是很驚人的,提前人類真的太多了。莊子談論樹的樂呵呵方式彷彿是正抬頭看著某一株遠比我們年紀都大的大樹,拍拍它,摸它。
當然,他所說的樹都是不可思議長存的,活在某個大時間裡。
我強烈到自知是偏見的看法是,世間從來沒有任一幢建築物美麗到、完整到可以單獨欣賞不出事的(除非只是封閉性的滿足於某種工匠技藝成果的欣賞和思索討論)。我這麼說絲毫不帶著多餘的喻意和那種故意拐彎抹角的「哲思」,也不是只指現代建築而已,而是包括了所有已列為人類偉大遺產的古老教堂、皇宮、城堡、寺廟和神社。不植樹,不靠樹來正確的遮擋和填補,沒有一幢建築不當場真相畢露的狼狽起來,線條總是太生硬、單調而且稀疏,仍只是「架子」,不會有足夠的生動感尤其稠密感。
然而,大多數樹種的天年其實都短於我們當前的人壽不是嗎?我們只是不容易察覺它們靜默的死亡和更生,並往往弄混了它們的群體和個體而已。況且,存活在城市裡的樹想自然死亡又何其困難如古書裡常說的「幸而得死」,人們總生得出各種莫名其妙的「必要理由」來害死它們,也因此,台北市很明智的規定活超過五十年的樹就稱之為大樹、老樹,列入保護。五十歲?這麼年輕,可又已這麼稀罕珍貴,台北市五十歲以上的人不滿街都是嗎?
京都著名的櫻景點哲學之道其實花已遲暮,老照片裡那樣如滿天飛雪的懾人景象已不會重現了—染井吉野櫻的天年是六十歲,而且染井吉野櫻已無法自然繁殖了,原是演化裡那種走錯了路、已該滅絕的物種(動物的馬也是),它得靠人來接枝育種(該有人去問問莊子,這算因為有用或無用才得以存活下來?),日本有這樣如吉野櫻守護者的工匠職人,仍是一個養活得了人的職業說明它的需求量,這些年極可能還多出了外銷訂單,連同櫻花祭一起輸出海外,知道這個讓我心情變得很好。
如同書寫此刻我看著敦化南路已有森林架勢的大樟樹群。
所以,在台北市四下行走、站立、或坐下來,如今我看著的便多是這些年紀輕輕的樹、一株一株比我兒子謝海盟年紀小的樹,「比樹老,比山小」,所以這兩句開車回家的老歌詞是對的。
我想起來,我小學國語課本裡有篇奇異的課文叫〈仲夏之夢〉,和只活五十二歲的莎士比亞完全無關,由一個披頭散髮的怪老人講故事或講時間裡發生和流逝的事給「我」這個小孩聽。末段,宛如天起涼風,溫煦的老人突然變臉狂笑,並從身體射出「綠色的彈子」把「我」從夏日午睡打醒,原來老人就是「我」睡它樹蔭裡的大榕樹。這文章收得有點笨拙,又鬼氣森森,當場嚇哭了班上好幾個女同學(已經都是快六十歲的祖母了,她們不會還記得吧?)。物換星移,如今輪我來講台北市從前種種給這些樹聽了(像辛亥路二段到復興南路那排年輕漂亮的楓香樹,你們自己曉得嗎?這裡曾是三路公車總站,這班公車既經北一女又到建中,是當年我的高中同學們的神級公車,少量的戀愛故事和極其大量的綺夢幻想就在此車上發生),並囑咐它們得努力好好活著,儘管這麼說並沒什麼實質意義,只是一份心情—當我們說聽天由命,這是很感傷的話;但對於所有城市的樹,則僅僅是個事實而已,比方一次大颱風,或一任新市長及其麾下的都發局局長。
理論上,我絕非一覺醒來到今天這年紀的,「日曆日曆,掛在牆壁,一天撕去一頁,叫我心裡著急」,這應該早早的、由弱而強的逐步察知才對,不是突如其來的發現。但這樣也許更好也說不定,我的遲鈍把這一察覺過程完整存留下來一次爆開,變得像是有事發生,因此不是結論關門,而是如棋局重開,帶著相當的熱度;是一種清清楚楚的知覺,不只被動的看,還要你有意識的尋求—像是自己身上攜帶著某種特殊光源(比方C.S.I.裡用來顯現命案現場不可見血跡、精液或漂白水的光敏靈),走到哪裡亮到哪裡,世界極生動的彷彿就在眼前一寸一寸剝開、呈現、柳暗花明。
我還真喜歡整個世界以這種方式年輕起來、復活起來。我說過,這很可能就是近幾年來我所能發生最好的事(其他時候,就像卡爾維諾講的,你充其量只能希冀別再有壞消息、世界不持續變得更糟),或者說,根本沒事發生卻能變得更好。每個東西都輕巧的動了一下,忽然生出了新的光采,有著不盡相同於過往的意思及其生命軌跡,或者說,變完整了,復原了它們各自的更完整模樣和內容,遂一一從群聚的、類化的扁平世界分離出來,跳入你眼睛裡。更好的是,無責任也不被催趕,可以仔仔細細的、完全由自己決定時間長度的看、想、描述和沉澱反省,沒人理你,一種自在(這是人老的好事之一,不急於也不被要求趕赴未來,所謂「晚上的自由」)。《聖經.創世紀》所謂「眼睛就明亮了」(很有趣,這也是人第一宗、且是最沉重的永世不赦之罪,傳及子子孫孫成為詛咒),人眼睛的蒼茫疲憊不僅僅是生理性的如不可逆的黃斑部病變,更多人更多時候是因為很長一段時日感覺沒東西可看了,沒再出現足夠讓人激動想講給別人也知道的書,沒幾個太值得等待所以必須一直盯住他的人,眼睛一直停滯於一種淡漠的、沒焦點的不良狀態。
最大規模明亮起來、豐饒起來的會是哪裡?我的真實經驗是(這也符合我的猜想),仍是書籍,也全部跟著年輕起來的書,施了魔法也似的。現在,我相信自己過去讀它們時一定忽略了很重要的什麼,我自己少了某些成分,從而少掉了某個很必要的視角和警覺,讓閱讀結果很不完整,而且可疑起來了,因此,每本像回事的書盡可能都該重新讀過才行—這有點像回到四十幾年前某個星期天早晨,我才剛搬家台北並第一次站在重慶南路上,傳說中的彼時重慶南路,人整個是空的,卻也像是個容器。當時的重慶南路書店一家挨著一家,一直伸到極目天際之處,眼前整個世界彷彿是用書鋪起來的。
稍微不同的是,這回我比較「不怕」了,也不容易上當,我喜歡它們的成分終於緩緩稍高於敬畏它們的成分,我能更精細的分辨、更知道如何讀所謂的「字裡行間」、那些比文字更稠密的東西。
所以,不只重讀,而是很接近於重來—從此(二○一五伊始),我以每兩天左右一本書的速度持續前行(倒不鼓勵人們這麼看書,不需要,我這多少是包含著某種工作成分,自覺性的,像昔日福樓拜為寫一部小說密集讀一千五百本書),我和書的一度漸凍關係看來完全醒過來了。
我尤其想好好再讀其中一些書,像是、卡爾維諾才寫成就死去的《帕洛瑪先生》,一個不只進行文學實驗還不斷擴大文學實驗範疇和可能性的卡爾維諾,比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更感覺死亡已臨身更私密遺言的卡爾維諾,在如此有限的時間知覺的篩選下,他被迫想什麼、覺得還可以想什麼並以為可走多遠云云;像是,波赫士全集的第三卷,這收存著他七十歲以後的詩和散文、演講辭,是一般人無意以及有意忽略甚至認為非波赫士的波赫士,也是不撐作品形式架子遂更去除了「虛張聲勢和言不由衷」的赤誠波赫士;像是、賈西亞.馬奎斯如此優雅退場的《妓女回憶錄》,尤其,書寫彼時他應該已進入所謂老年痴呆的阿茲海默症世界,不該離去的,不該消失的,但他仍有剩下,而且剩下的依然如此沉靜的熠熠發光,仍這麼美好無匹、有價值,也許我哪天也會那樣,我希望屆時我仍會記得這部奇妙的小說並記得我此時此刻的想法、感覺。
又像是,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六十六歲的作品),我的閱讀記憶告訴我這書不算「成功」,且讓人爽然若失的感覺有點「簡單」,以康德的思維規格,相較於《純粹理性批判》一路而來那個深奧、結實、一步也不跳過不分神不省略到壓垮人的康德(我還記得卡爾.雅斯培講過極精準的一番話,大意是,讀康德,總覺得康德把他才給你的東西又拿回去了),可見鑑賞、判斷這一領域多麼難,難想、難整理、難敘述、難解說、難以確信以及證實,包括對自己說和對別人說,每一步都困難而且又冒出來新的、近乎無解的困難。而鑑賞和判斷恰恰是我近年來最在意的,也是我的工作最無法閃躲的兩個大麻煩東西,我因此感覺自己不斷在遠離當下世界,鑑賞和判斷不應該、但難道最終只能是自娛嗎?
康德後來,和賈西亞.馬奎茲一樣,也進到那個如賈西亞.馬奎茲年輕時所說「死亡的遺忘」的世界。
一直年輕起來的眼前世界
有一天,我忽然清清楚楚意識到這個應該早就如此明顯的事實—我意識到,我面對著的是一個這麼年輕的世界,並且彷彿回春,相對於我,這個世界只能一天比一天、每一樣事物不停止的更年輕起來。
我猜,這極可能就像吳清源發現圍碁新布局時的感覺,吳清源說他當時正泡在那種日式溫泉澡堂裡,「宛如天公的啟示」,就是這一句話,一道光般讓他一下子纖毫畢露的、再無一絲懷疑陰影的看清楚早已如此明擺著的事實。從此,圍碁由原來的大正碁正式進入昭和碁,進入現代。
從此,我把這一全新的世界圖像,如同聽從梵樂希的建言,...
目錄
輯一 年紀
1.一直年輕起來的眼前世界
2.他們是幾歲時寫的?
3.延後二十年變大變老
4.身體部位一處一處浮現出來
5.暫時按下不表的死亡
輯二 閱讀
1.攜帶著的書
2.結論難免荒唐,所以何妨先蓋住它不讀
3.有關鑑賞這麻煩東西,並試以屠格涅夫為例子
4.黃英哲其書其人,以及少年心志這東西
5.集體‧遞減的生命經歷和記憶
6.一個現場目擊者的記憶和說明
7.再來的張愛玲.愛與憎
8.沒惡人的寅次郎國
輯三 書寫
1.五百個讀者,以及這問題:剩多少個讀者你仍願意寫?
2.第二次慶祝無意義,一本八十幾歲的小說
3.將愈來愈純粹
4.重寫的小說
5.請稍稍早一點開始寫,趁這些東西還在
6.字有大有小‧這是字的本來模樣
7.不願解釋自己的作品,卻得能夠解釋自己的作品
8.文學書寫做為一個職業,以及那種東邊拿一點西邊拿一點的脫困生活方式
輯四 年紀
6.瘟疫時期的愛情在日本
附錄
千年大夢
輯一 年紀
1.一直年輕起來的眼前世界
2.他們是幾歲時寫的?
3.延後二十年變大變老
4.身體部位一處一處浮現出來
5.暫時按下不表的死亡
輯二 閱讀
1.攜帶著的書
2.結論難免荒唐,所以何妨先蓋住它不讀
3.有關鑑賞這麻煩東西,並試以屠格涅夫為例子
4.黃英哲其書其人,以及少年心志這東西
5.集體‧遞減的生命經歷和記憶
6.一個現場目擊者的記憶和說明
7.再來的張愛玲.愛與憎
8.沒惡人的寅次郎國
輯三 書寫
1.五百個讀者,以及這問題:剩多少個讀者你仍願意寫?
2.第二次慶祝無意義,一本八十幾歲的小說
3.將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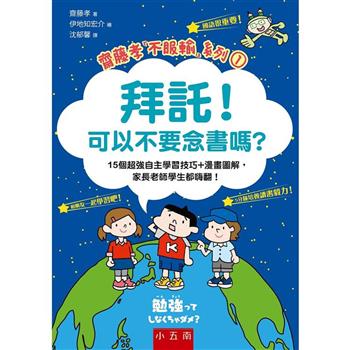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政類超強5合1題庫[國民營事業]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綜合行政類超強5合1題庫[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