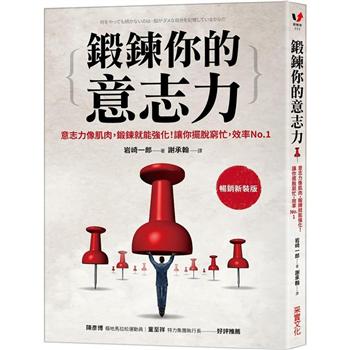序言
體驗旅行
人生無時無刻不在旅行,從匍匐爬行,探頭探腦,四處張望外在世界,到走出家門,在庭院街坊玩耍,或上學,郊遊,就業,出差,或找個花前月下,浪漫訴情,或東奔西跑,飛越洲際,繞著地球跑……。人因為是「動」物,所以一直都有所行動。若真的到了「動不了」的那一刻,也會興嘆:「人生如旅」。
日前讀著詩人瘂弦的回憶錄,提及他去探候一位老病纏身的文壇前輩,聽他說到「人生如旅」這句話,心底備感悵然。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到了生命終點,如果還有力氣的話,相信也一定會說出這句話。這不就印證著人類來到地球跑一趟,實際上也就是做了一趟旅行而已。瘂弦老師還說:「什麼人都可以寫(回憶錄),都有它的意義。」這裡的「回憶錄」不就是我們作為人類,做了一趟旅行的所見或所思。有人問法國第一任文化部長馬爾侯(André Malraux)何謂「文化」?他回答:「人死去時,回想這一輩子所做過的那些事。」原來,「文化」的界定這麼簡單,不就是我們做為「旅人」,在世短短數十寒暑中的所見所聞。
人生如旅
「旅行」可說是人類與生俱有的基因。人類跟許多動物一樣,到了成年就得分枝展葉,出外另謀發展。這項出門闖天下的衝動根本就是一種本能。數千年來,人類一直都在旅行,不分中外,無分貴賤,或好奇,或增廣見聞,或信靈,或娛樂,或出於社會壓力,英諺有云:「行遠多識」(He who travels far knows much.)。現代意義的觀光休閒旅行正是十八世紀末從英國興起的。再如,每年九月「開季」(la rentrée),法國人見面的第一眼便是瞧看對方是否曬成「古銅色」(bien bronzé),第一句寒暄話就是:「你去了哪渡假?」「旅行」根本也就是人類生存的必備條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古代西方世界最大規模的旅遊形式乃是「進香團」(朝聖)。根據基督教紀錄,及至十四世紀末,登錄在案的朝聖客已達五十萬人。而當時梵諦岡所在的羅馬城總人口也不及十萬人。同樣的,歐洲人出於好奇,成群結隊進行海外探險,最終發現了「新大陸」,就此改變了地球的命運。曾有學者研究發現,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的最初十年,那些冒險到新大陸考察的歐洲人,返國後都出現一種超級的優越感。換言之,「到新大陸旅行,不僅創造了歐洲人的新文化身分,也讓他們趾高氣昂,不可一世,因而鑄下毀滅拉丁美洲文化的帝國主義暴行」。
在十六世紀的百年中,歐洲一地所出版的旅遊手冊就多達一千種,是當時新興引進印刷術的最大宗,遠遠超過古典樂譜。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國明朝中葉,也大量出現由商人自編自印的商旅地圖,供作經營服務,水陸路引,經商須知之用。簡言之,人類大規模的旅行活動是從個人的好奇本性,到宗教的虔心嚮往,經商營利,才進入到當代的觀光休閒旅遊。
「旅行」的定義相當廣泛,從休閒旅遊、探險、流浪、遊學(留學),到商務旅遊、軍事遠征、外交出使、宗教朝聖、流放、移民等等皆屬之。這些對於提升個人見識,想像與創造力,增進文化交流,多元互重,乃至商務交易,互通有無等皆有助益。以孔子為例,他應是上古中國最偉大的「旅行家」。根據孟子的整理,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共遊歷九國、七都、十三縣、十八鄉,訪八座名山、九處文化遺跡、四個洞穴,拜會五十九位政要、文人及顯要。其他著名的旅行家,有司馬遷、玄奘等人。古代西方世界的「大旅行家」,則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莫屬。旅行讓這些歷史名人增廣見聞,也名留青史。質言之,驅動人類出外旅行的動因有別,目的迥異,惟其結果,則是創造了當今人類的文明,不論是好是壞,皆交由時間去做篩選。
人生如戲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生活就像一齣戲。它是演不完、道不盡的喜怒哀樂,讓我們嘗試著酸甜苦辣,只有經歷了這些,生活才有滋有味。莎士比亞在他所寫的名劇《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不也說出:「世界是座舞台,所有男男女女都只是演員。各有其出場和入場。每個人皆扮演著許多角色。」我們走過,必定留下痕跡。重要的是,如何記下我們粉墨登場時每個重要的、感動的時刻。
法國作家歐梅松(Jean d’Ormesson)說過一句名言:「人類戰勝死亡的唯一方法,就是即便你死去,有人還會記起你的名字。」所以,只要能做到「死後留名」,人就可以不朽,這輩子也就活得有意義。我們參加親友的告別式,或觀看電視轉播某某達官貴人的葬禮,心底總會想著,他(她)到底在人世間留下了些什麼?甚至還置之度外暗自私忖:「寧可活得精彩,也不要死得隆重」。人生這齣戲只不過是一個過場。態度就決定了你的高度。閩南語歌星陳雷的那首招牌歌〈歡喜就好〉(吳嘉祥填詞),不就訴說著:「人生短短,好親像咧迌」(人生短暫,就像是來遊玩)。我們如果抱定這種態度,不管榮華富貴,或度日如年,生活一定會過得既充實又幸福。
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在《異鄉人》書裡,透過牢裡的主角說道:「一個人哪怕只生活過一天,也可以毫無困難的在牢裡過上一百年。」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也得出一個體驗:「一個人在家裡也可以過得很游牧。」還有十八世紀那位因比武犯禁的作家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被處以四十二天的居家禁足,因而寫下了一本書《在自己房間裡旅行》。易言之,旅行並不是非得長途跋涉,強迫身體位移不可,只要你活過,思過,回憶過,想像過,旅行就在你心中,旅行就屬於你。
兩三個純樸且偉大的形象
人生無處不旅行,關鍵在於如何體悟箇中的意涵。藝術家做到了,所以我們擁有精采絕倫、引人深思的文藝創作。史家也做到了,所以我們擁有綿亙不斷,璀璨美麗的文明。換言之,人類所有的創作及文明都與旅行有關,皆因旅行而生,尤其是文字書寫。卡繆說過,他是靠著「兩三個純樸且偉大的形象」來創作的。他提到有一次回阿爾及利亞老家探親,母親正和她的姊妹們聚在一塊聊天喝下午茶,年邁的姨媽們對映著牆上一幀她們一群姊妹青春年少的模樣,讓他揪心不已。如果說「人生如戲」,那麼最大的不同點是,這齣戲從沒有給出劇本,而且它也不允許暫停,任誰也不知道哪個時間點會劇終。當然,更不會有謝幕這樣的排場。我們能做的,不就是放鬆心情,步步驚魂地踏出下一步,然後小心謹慎地回憶過往。
我住台北文昌街已有三十餘年,離我們家不到五十公尺處,一棟狹窄的平房,住著一位清癯的長者。看不出他的實際年齡,也不知他的真實姓名。每天早早晨起,有一隻黑色土狗相伴。他孑然一生,應該是這條熱鬧家具街的老住戶。我們路過都會喊他:「伯伯好!」有時打從市場採買回來,也會塞幾個水果給他,他也會欣然收下。平時都靜靜地在騎樓下活動,寒暄幾句,也回收些紙箱賺點零用,然後叼根菸四處走走。屋裡有一台電視機,生活一切自理,偶爾會有社會局的志工過來探候一下。他為人真的夠低調。隔壁的財哥是他唯一的談話對象。年紀比我小的財哥告訴過我,他不回大陸探親,說那兒沒有親人了。直到有一天路過他家,赫然發現大門深鎖,上頭還貼了個封條。打聽之下才知道幾天前他已靜悄悄地走了。這麼一位無名無姓的無名氏,與我們毗鄰這麼多年,他的親切隨和,與世無爭,給我們太多的懷想。他那和藹的模樣,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另一個形象是我十九歲那年,與一群同學到新店坪林露營,在河邊拍下的黑白照片。那時我已「轉大人」,因平素有打工,體魄相當不錯。最近翻看才發現那年我已有六塊肌了!坪林是我們年輕時最常去玩水的地方。撫今追昔,這張照片喚醒我們的青春年少,那樣單純又自在,還有彼時的事事物物。有回騎單車環島路過小歇,看到舊橋依在,當年帶領我們玩耍的阿濱卻已不在,備感唏噓。還有每次搭車到礁溪,即將駛進雪山隧道前,我都會不自覺地探頭,張望那片有著我們許多嘻笑歡樂的河畔……
旅行讓我們記錄人生,也體驗生存。我們起而行,勝讀萬卷書;我們坐而思,可以馳騁古今,做個幸福的時空旅人。人生如旅,指的是生命的形式;人生如戲,說的是每個人自身所開創的內容。至於人生如夢,講的恐怕是生存的幻景,其實它也是生命的本質,也是一種恆久的真理,就是所謂的「神話」。
(二○二二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