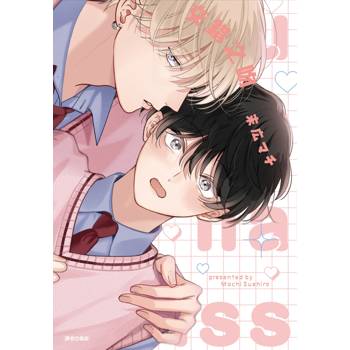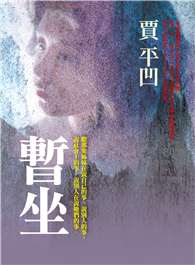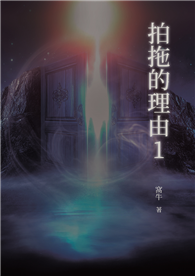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再孤單的島,也有我的熱鬧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15 |
散文 |
$ 356 |
現代散文 |
$ 396 |
中文書 |
$ 405 |
現代散文 |
$ 405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40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再孤單的島,也有我的熱鬧
她化為島嶼一員,放開來豁出去,
闖一條熱烈且寂寞的路途。
她,大使夫人,大使身邊一枚隱約的綠葉。下了外交舞台官方場域,是小島友人們眼中坦率熱情的台灣女子潔思敏。回到昭瑩的世界,則是在文字與麵粉的一方天地安然自得,以及在一只海島空巢與丈夫啾啾和鳴的她自己。
小島宇宙裡,三個不同身分轉圜,有時獨挑大梁,有時輪番登場,有些時候更得分飾多角。島國采風探索、社群往來密友聚首,大海瑜伽流浪共學、享受一個人的寂寞也學習與伴侶並肩同行。邁開熱情的腳步,睜大好奇的雙眼,唯有熱烈生活並真正愛過,才能理直氣壯且了無遺憾說:
「再孤單的島,也有我的熱鬧。」
作者簡介
杜昭瑩
台灣台南人,輔大中文研究所碩士。
旅居各國多年,先後在英國牛津、美國洛杉磯、比利時布魯塞爾、印尼雅加達、印尼泗水、馬紹爾群島等地落腳停留。
不論天涯海角,始終未曾離開過文學溫暖的懷抱。
著有《20分的媽媽,80分的小孩──我在比利時的教養手記》、《淡定,讓孩子起飛》、《這國,這島,這城──你意想不到的印度尼西亞》、《你的星空,我的愛情少尉》、《聽見花開的聲音:24朵印尼芳華的生命寫真》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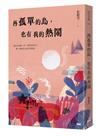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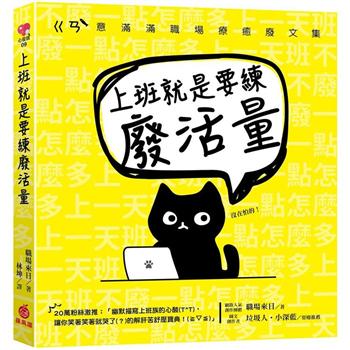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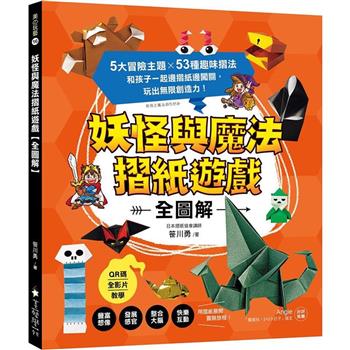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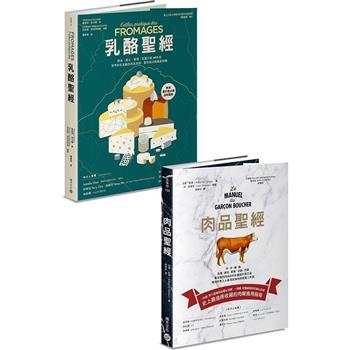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