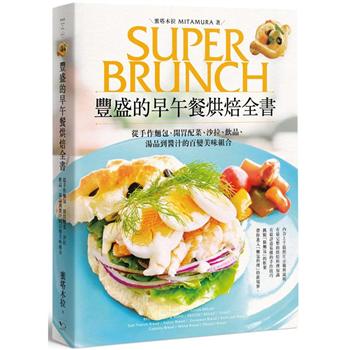生命過往所經歷的一切,有如不朽也沉寂的一張白紙,
永遠等待著又一次的翻頁啟幕。
永遠等待著又一次的翻頁啟幕。
人生一路走來是如何虯結成如今的模樣?曾經以為自己確切經歷並且見證過的,為何怎麼也無法重溯當時的細節?該如何再次凝視那些總是回繞不去、並不斷刺戳內裡的纏身過往?
總是沉靜幽緩、過往卻恍如一片空白的婆,喜歡在丈夫面前張揚娘家昔日榮光的母親,看似豪邁飛揚實則內隱著敏感拘謹的父親,俊逸如風終而失心癲狂的小舅,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彷若褪色模糊疊影的小舅媽……
沉默無語的童年,在成長軌跡留下深刻印痕的兒時至親,以及曾經在生命中進出的情人與密友;如岩層般壘疊的厚實記憶,是否就等於自我的生命意涵?而在意識邊陲之外,夢境與記憶相互滲漏、彼此重塑,能夠透露出更多的真相?
為了解答存在之謎,作者以小說之筆自我解剖,透過文字一次又一次復返記憶現場,審視記憶與書寫之間永恆的爭辯與彼此違逆。也經由書寫將記憶放下、通往領悟和渴慕,以此彌縫自我生命創傷困境。
本書特色
阮慶岳最新小說作品,以小說之筆自我解剖,彌縫自我生命創傷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