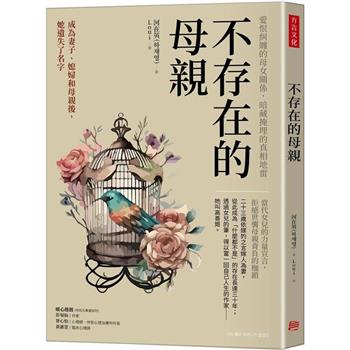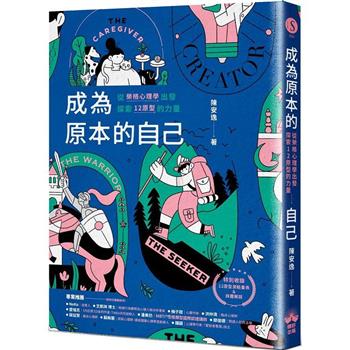糧食就是生命!而江湖啊,水的流域。
二○○五年,震驚社會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宣判入獄,也是在這時,吳音寧開啟了與楊儒門的書信往來。《江湖在哪裡》藉由這起事件,從媒體對事件的挖掘報導談起,真實在「實況報導」中消失殆盡,取代的是各種臆測,也「現形」了台灣島嶼,農業成為藍綠政治對決的犧牲品。
本書不僅是一頁台灣農業史,更是這塊土地曾有的豐美記憶與耕者的斑斑血淚。作者以感性的筆觸、佐以詳盡的文資史料,從家鄉溪州出發,帶領讀者走過政權更迭前後、走過「多吃麵,少吃米」,走過紅葉少棒年代,走過左翼社會主義、走過偉大的領袖,走過國際孤立本土認同,從蔗糖、香蕉到鳳梨罐頭,印證了「稻米就是生命」。
★「Books From Taiwan 2008」國際版權推薦書
★2007年《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獎
★2007年8月誠品選書
‧特聘金鼎獎與金蝶獎書封設計師得主 楊啟巽,重新打造新款封面,以稻米作為設計發想主軸,單純的農業,不應該有那麽多的人為因素干擾,故在書名間,牽起象徵造成阻礙的線段,形塑稻米從生長到落地,須面臨的困境。並選用較具纖維成分的封面紙張,佐以燙金呈現顆顆米粒,顯現層次。
‧一窺台灣農業發展史,以農業狀況,現形台灣島嶼。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經典典藏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00 |
二手中文書 |
$ 440 |
中文書 |
$ 440 |
台灣研究 |
$ 450 |
城市/土地發展 |
$ 450 |
中文現代文學 |
$ 450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經典典藏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