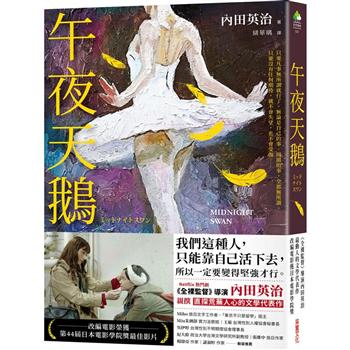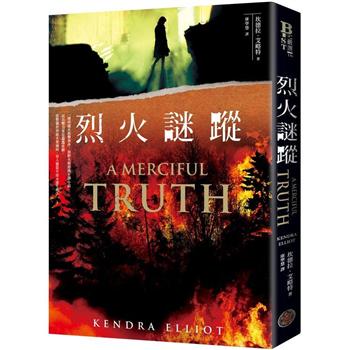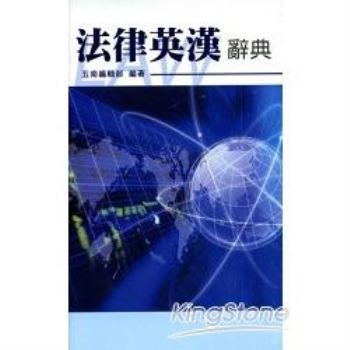我漫漫的書寫就是一種至簡的備忘,
安頓好那些脈絡有限卻不斷交錯的記憶,
同時保存下這座島嶼歷來生存的軌跡。
作為小說,《至簡的備忘》的創作形式在台灣文壇算是不常出現的美術與視覺藝術文學作品──全書試圖以九十餘個畫面裝幀作為書寫底質,播散成具倍數效應的多維時空超覺展開,部署大河式庶民生活斷代的嘗試之作,亦是台灣當代文學跨領域創作的書寫實驗。
本書試著以地方上家族幽微人物交織生命力道回應島嶼歷來被絕對化的存續孤寂。書寫島嶼過去的同時也在書寫著未來與現在的關聯,藉由撤除寫讀界線讓讀者更容易看見實際書寫的工作狀態,透過層疊灰階替代書寫政治的商品化框架──多軌並置的時空軸線,狠狠地甩開虛構與非虛構的真實迷亂──透過發散裂解中九十餘個影像敘事的再影像函化,不斷邀請讀者一起進入已知的未知時空間裡,感受另類「看見」島嶼生成的跨時區縐褶,徹底以一種身為島嶼人都能閱讀的再創方式開放參與,每個人都會被熱情地歡迎進入庶民書寫之中,這是身在福爾摩沙的你我都該閱讀的庶民書寫!
聯名推薦
台灣當代文學與視覺藝術跨域式小說
高翊峰(作家)
楊凱麟(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
廖仁義(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至簡的備忘:哈古棯與少年西格的島嶼記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10 |
二手中文書 |
$ 616 |
中文現代文學 |
$ 686 |
中文書 |
$ 702 |
現代小說 |
$ 70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至簡的備忘:哈古棯與少年西格的島嶼記憶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愷璜
跨領域觀念藝術家(是視覺藝術家同時也是策展人、複合媒體導演、跨域書寫者多重當代創作身分)。遍歷當代藝術創作多元分類,同時也是藝術教育行政治理階層工作者、藝術社會介入與永續推動者。一九八○年代末期即開始以計畫型藝術方案纏叢在主體思辨議題之空間裝置、影像與複合媒體、環境地景、策展書寫等進行總體式的創作實踐。
陳愷璜
跨領域觀念藝術家(是視覺藝術家同時也是策展人、複合媒體導演、跨域書寫者多重當代創作身分)。遍歷當代藝術創作多元分類,同時也是藝術教育行政治理階層工作者、藝術社會介入與永續推動者。一九八○年代末期即開始以計畫型藝術方案纏叢在主體思辨議題之空間裝置、影像與複合媒體、環境地景、策展書寫等進行總體式的創作實踐。
目錄
可進化的前言
那開始起響
傳衍
封建已然流浪數百年
作為姓名的「羅蕃薯」
超脫遺傳的無謂細碎紛亂
持續切分的關聯
只有認命啦!
漢和合體的所在
生物動力學的具體效應
「三泰株式會社」
百年幼稚園
童子尿
本體的鍛鍊
移轉認同
從頓角難行到臻於流暢的圓弧
人生會否輪轉
「吳百發診所」
脆弱時代的強度生活
存有逕自朝向成為擬想式的直觀練習反覆邁進
觀看的純粹:人生被迫瘋癲
小打工仔意外的共享體味
身體在空間裡的過渡
短暫離開人的尺度
偶然與必然
博愛路上這一家
華麗的蘋果滋味
關於感知演繹的單純驅力
透過直觀,試著動用極不熟練的身體
屎沆仔
跟上時代翻轉人生?
火的文明起點
經由任意微系統開始啟動的生活觀察基礎,多少都能貼緊本能
不退老派的「決定性瞬間」
嘉義福音堂教會裡的異教徒
屢敗屢戰的家庭投資履歷
局部實木配上局部膠合的雕花柚木方盒子
「崎腳變電所」
百多年前,化學知識隨著日本帝國緩步進入島嶼
《勇士們》
其來有自的古早生存學
以拋擲作為湧現
終於到來的阿里山首遊
周仔與茂林仔
B to C的源起
大同牌
豪賭運氣
社會化的演練路徑
民族國小大禮堂
以認同流變為師
基樺師木作工坊
鋪上草蓆靜躺在石板中庭裡,仰望星空的高爽快意
極權總是在靜默裡伺機變化並且藉著異端轉向
關於人種的新視野
「老母雞」
周太太
那些年的私微節奏
地景裝置的本能起點,同時也正是藝術人生地景裡的始源想像
「香蘭」
一璐冰
少棒隊
有意識的告別,就足以向世界說出什麼
停不下來的空間異動
「美國」
軍緣二三事
自己的房子自己蓋
到底要怎麼樣調整,才能跟得上時代?
青少年的不舒適性
影像叢集生活
被詛咒之域
島嶼的第二次一道黑
以迂迴作為進路
諧擬桃花源
凝視陰極射線管螢幕,西格式的夜想畫(Nocturne)
清淤的自然反覆
混合型力比多?
童軍社團的經營
受制於原來就不可見的存在波動
黑色鋼筆桿
「傾斜、再傾斜、一直傾斜、不斷傾斜、直到傾斜」
「葡萄成熟時」
沉潛速度的極限
想像著瞬間成為他人
一年生活:二十四坪
違建麵攤們正作勢展現不同的都會慾望
永誌之物
偶遇的強度訓練
經常不由自主地就會浮現亂錯的離散想像
麟洛營區
為什麼會在軍事基地裡生成擺脫紀律的異質場所︖
日日流洩的日常
關於反轉未來的預置脫鉤
島嶼的可能性
終究是個只能與地球同框的島嶼
後記
附錄:
空間性靈的游絲若離:一個短舞作劇場
那開始起響
傳衍
封建已然流浪數百年
作為姓名的「羅蕃薯」
超脫遺傳的無謂細碎紛亂
持續切分的關聯
只有認命啦!
漢和合體的所在
生物動力學的具體效應
「三泰株式會社」
百年幼稚園
童子尿
本體的鍛鍊
移轉認同
從頓角難行到臻於流暢的圓弧
人生會否輪轉
「吳百發診所」
脆弱時代的強度生活
存有逕自朝向成為擬想式的直觀練習反覆邁進
觀看的純粹:人生被迫瘋癲
小打工仔意外的共享體味
身體在空間裡的過渡
短暫離開人的尺度
偶然與必然
博愛路上這一家
華麗的蘋果滋味
關於感知演繹的單純驅力
透過直觀,試著動用極不熟練的身體
屎沆仔
跟上時代翻轉人生?
火的文明起點
經由任意微系統開始啟動的生活觀察基礎,多少都能貼緊本能
不退老派的「決定性瞬間」
嘉義福音堂教會裡的異教徒
屢敗屢戰的家庭投資履歷
局部實木配上局部膠合的雕花柚木方盒子
「崎腳變電所」
百多年前,化學知識隨著日本帝國緩步進入島嶼
《勇士們》
其來有自的古早生存學
以拋擲作為湧現
終於到來的阿里山首遊
周仔與茂林仔
B to C的源起
大同牌
豪賭運氣
社會化的演練路徑
民族國小大禮堂
以認同流變為師
基樺師木作工坊
鋪上草蓆靜躺在石板中庭裡,仰望星空的高爽快意
極權總是在靜默裡伺機變化並且藉著異端轉向
關於人種的新視野
「老母雞」
周太太
那些年的私微節奏
地景裝置的本能起點,同時也正是藝術人生地景裡的始源想像
「香蘭」
一璐冰
少棒隊
有意識的告別,就足以向世界說出什麼
停不下來的空間異動
「美國」
軍緣二三事
自己的房子自己蓋
到底要怎麼樣調整,才能跟得上時代?
青少年的不舒適性
影像叢集生活
被詛咒之域
島嶼的第二次一道黑
以迂迴作為進路
諧擬桃花源
凝視陰極射線管螢幕,西格式的夜想畫(Nocturne)
清淤的自然反覆
混合型力比多?
童軍社團的經營
受制於原來就不可見的存在波動
黑色鋼筆桿
「傾斜、再傾斜、一直傾斜、不斷傾斜、直到傾斜」
「葡萄成熟時」
沉潛速度的極限
想像著瞬間成為他人
一年生活:二十四坪
違建麵攤們正作勢展現不同的都會慾望
永誌之物
偶遇的強度訓練
經常不由自主地就會浮現亂錯的離散想像
麟洛營區
為什麼會在軍事基地裡生成擺脫紀律的異質場所︖
日日流洩的日常
關於反轉未來的預置脫鉤
島嶼的可能性
終究是個只能與地球同框的島嶼
後記
附錄:
空間性靈的游絲若離:一個短舞作劇場
序
後記
試著透過超長時延跨了世紀相關起落的虛實人物,書寫一本關於某種成年以前由少年到青年時期量測生活──可逆旅時空──的庶民備忘,讓五歲到任何成年歲數的人都得以重新進入生活歷史的差異比對與緬懷回顧。因為無論如何,那個時期都是每個人成年之後難以忘懷的高感度人生歷程,如果無法反覆面對將無以為繼;不論值得與否,它都曾經是密集成長的高強度過去。
兀自就把開放性書寫都納集了進來,對於一個非文學圈子的分子來說:真實世界自有其揭露深層非虛構欲念的乖張虛構;於是,它竟自動漫溢成了有小說感、帶點散文式、詩化的,一個跨文類的跨域書寫實驗──它自動找上了我,於是便成為刻意的跨年計畫──流瀉成千高台式的百花齊放,也自然匯聚成為一條書寫的曲折小徑,這對於試圖進入書寫世界的我來說,的確是個保存有限記憶、紛亂情愫與思緒的必然,幾乎沒有被迫要從過多的選項裡做出任何困難的選擇。
事實上,我也不清楚在書寫世界裡,到底能夠擁有如何的選擇性。一旦下定阿甘式書寫決心的第一時間,似乎所有直觀的感知便自動湧現將近上百個靈動畫面對於這個依戀的重重包圍。然後,感覺上只需要對著這些不等程度晃動的游移畫面進行縝密的對話,便得以自在地生成書寫;而這些靈動畫面的確流竄著濃厚如動畫分鏡般的非現實意味!
縱然如此,卻完全沒有任何一點預先的意圖想去碰觸所謂祖父悖論或平行宇宙;也不是要處理或回應有時會被多人分享的虛假記憶:所謂的「曼德拉效應」;儘管主流科學界認為此效應只是另異錯誤記憶的一種體現。
或許可以帶點無懼的聲稱:「這是一部跨域式小說的實驗書寫!」只因為它完全是承接自生命過程綿密起落的斷裂感造化—銜著不斷積累堆置的生命懸宕狀態,既是個體也是島嶼集體──生成聳動半透明關節化的書寫呈現,卻又害怕這樣的書寫足以引發從此便不再能以身體所能支配局部器官的自由行動而焦慮不已──於是開始了先是器官記憶的濃烈反覆、反噬,如噬尾蛇一樣貪婪不分頭尾地吞噬自身感受裡的魯莽──這個跨年的跨域書寫歷程也同時試煉著如何掙扎以預作垂死的準備,那是所有生命源頭必然伴隨的警示。如此宣示更多的是因為再不試著說服安頓自己,它將難以繼續往下一個未來時間邁進。
一旦意識到了,它就會變成一道不太容易越過的關卡。因此,無論如何這都足以讓人冒著與這名為「小說」的書寫一起死去的風險,來進行這個書寫的實驗之路。
試著同步展開透明距離的理論性描述,純然是基於全球災難時代對世界的必要回應。多少有種救贖心態:因為世界性的武漢疫病──恆常的反覆慘烈形同文明生活的逐步滅絕,於今沒有人會再噤聲,隨時都該滑移進時間所掩護著已然凹陷的失落內裡──避免感染籠罩的擾動,卻在看似沒有距離的間離化阻隔中持續斷鏈。
所有似 Jelly 狀色彩的奇形物質,能見度或許還要能再好上許多才行,它從來都不是主動式的對著世界進行任何形式的阻絕,在看似空氣般的物態裡,卻無法直接接觸、連結、跨越,而是硬生生的、可見的斷裂成為無法滲透的分立──但是必須盡量排除關係的局部化──以保有常態的有機與持續可逆。
噢!你總還是能看見整個事件的生發過程甚至是結果的如何到來,卻無法嘗試著透過什麼物質介面而得以讓它們絕對化的連結為一體。可見與不可見在此都偏移為超過物理事態常軌所能解釋的辯證或對立關係。不論如何,我都想試著述說些什麼。「成為光、成為書寫的焦聚」,或許終究也會成為一種極度深切又具有島嶼在地庶民特徵的終極訴求。它不僅能穿透自身,還能折射明晰的圖像、伴隨不斷的隱隱音聲,驅動能量鎔鑄一切的偶然與必然。它看似虛擬,卻能緊緊追索著如雷射光的擊打般,連續地一擁而上,好更趨近成為光的終極可能。
一直有兩個不同年齡的西格以及改名後的啟煌交錯在與哈古棯之間進行著不甚同調的交互對話與談論。或者這整個事態就像是實體與虛擬之間的試圖跨接。但可以立即確認的這可不是數個鬼魅間的談話──卻更像是重現過往又酷似夢境交錯的幻覺一般──表象上看似無礙的現實已經全面脫軌,並且不再以現實的線性時空被認知。它們藉由完全不同的存有載體來示意並揭露它們實存上的必要。不斷地岔出、意外取代規律、交疊纏祟出逐漸逼向清朗透亮的可辨識符號──圖像──形體與回音:西格與其自身啟煌。因為西格從小家裡所有的事情,幾乎都只能是他自己片面單向理解到的,而且經常是各種外人對他的道聽塗說!
互為虛構且相互對應的持存時空:雜多歪斜、偏移、函化的疊置。得以不斷演繹、夾敘的時間與空間──想像著與宇宙論對位修正的當代負人類世本體隱喻──此刻能回應的,似乎就只是世界現實裡一切無止境紛雜實存的消耗性選項。如果這是需要被迫做出即時的選擇,它的確總是能在關鍵時刻裡被重新決定、改變路徑成為無法預期的生成。想想個體生命,絕處逢生、隨機又任意性的可能寓意便能了解。
聽著他人的生命歷程來轉置成為故事的起點。對我來說,小說書寫的某種潛隱定義似乎就已經在那裡萌發。
如果試著「回到母親……」永遠是一條活路:那麼回到哈古棯母親黃素柳水上鄉柳仔林的故居,勢必成為進擊頹敗家族必要的地方誌與庶民歷史的繞道之路。試著返回西格的母親美玉的獨特
日治年代困窘,讓時代集體的生活曲折因而得以平復、得以成為生命的常態。即便那種時間越來越在感受上有著更為清淡的過往羈絆,也自然是滄海桑田後的殘破現實。是無人歡娛的時間軸線裡所牽動的消逝場域,獨留個人的唏噓與哀嘆。一切原來我們所不知道的變徵之貌,悵然之餘竟也開始充盈起古怪的絕對性格。
試著想像,或許所有的小說創作都必然是透過個別生命的微觀盡述,好沾染一點文學性的驅力強化,才足以傳遞深度感知上的巨觀鋪陳而藉以開拓人生、得以舒化生活,生成面對未來繼續生存的能力。這聽起來,十足就已經是個有點年紀的人才該會說的話!
試著透過這本被我名之為小說的書寫以及它從當代視覺藝術觀念上轉置的真實來消敉虛構──非虛構間的無意義爭端,這一切也無非都只是自己的多慮。全文人物都是夾雜真實或虛構的姓名與歷程,但是卻未必都循著他們的現實人生作為書寫的底蘊。
如果詩正在遠離世界或者正在極端地透明化、黑化──未來的世界,以後會否突兀的將只剩下「小說家」?
二○二一年五月中旬之後島嶼的武漢肺炎疫情狀況開始急遽惡化,它正試著反轉幾年之間的偶然平靜,趨向世界的絕對化不幸、或者那已經逝去生命的數千萬人的無辜?慘烈程度──跨了西班牙流感百年之後──只有二○二二年「島上都死光了」的假設性概念推演,足堪比擬!
多少開始懷疑這部「小說」書寫,真能有機會出版問世?或者只能成為某種下一輪頹世人類考古的潛隱遺誌?說穿了,難免有種深沉難鳴的莫名感:跨年裡很多個天剛蒙亮的清晨,總能在非預期瞬間便看見窗外無聲息的遠處,光亮弧線裡滑溜過一列五節的騰空輕軌車;窗外近處園子裡的蟲鳴似乎也都會切換距離般地配合著那樣的不真實感,好讓僅有的書寫能夠更全面地沉浸在非現實的世界之中!
本書的出版,除了兄姊、Jeanette、Didier……的鼎力支持,琇媛貼心的讀者角度。翊峰老師的專業提點……全都提供了莫大的幫助,謹此獻上衷心致謝。
試著透過超長時延跨了世紀相關起落的虛實人物,書寫一本關於某種成年以前由少年到青年時期量測生活──可逆旅時空──的庶民備忘,讓五歲到任何成年歲數的人都得以重新進入生活歷史的差異比對與緬懷回顧。因為無論如何,那個時期都是每個人成年之後難以忘懷的高感度人生歷程,如果無法反覆面對將無以為繼;不論值得與否,它都曾經是密集成長的高強度過去。
兀自就把開放性書寫都納集了進來,對於一個非文學圈子的分子來說:真實世界自有其揭露深層非虛構欲念的乖張虛構;於是,它竟自動漫溢成了有小說感、帶點散文式、詩化的,一個跨文類的跨域書寫實驗──它自動找上了我,於是便成為刻意的跨年計畫──流瀉成千高台式的百花齊放,也自然匯聚成為一條書寫的曲折小徑,這對於試圖進入書寫世界的我來說,的確是個保存有限記憶、紛亂情愫與思緒的必然,幾乎沒有被迫要從過多的選項裡做出任何困難的選擇。
事實上,我也不清楚在書寫世界裡,到底能夠擁有如何的選擇性。一旦下定阿甘式書寫決心的第一時間,似乎所有直觀的感知便自動湧現將近上百個靈動畫面對於這個依戀的重重包圍。然後,感覺上只需要對著這些不等程度晃動的游移畫面進行縝密的對話,便得以自在地生成書寫;而這些靈動畫面的確流竄著濃厚如動畫分鏡般的非現實意味!
縱然如此,卻完全沒有任何一點預先的意圖想去碰觸所謂祖父悖論或平行宇宙;也不是要處理或回應有時會被多人分享的虛假記憶:所謂的「曼德拉效應」;儘管主流科學界認為此效應只是另異錯誤記憶的一種體現。
或許可以帶點無懼的聲稱:「這是一部跨域式小說的實驗書寫!」只因為它完全是承接自生命過程綿密起落的斷裂感造化—銜著不斷積累堆置的生命懸宕狀態,既是個體也是島嶼集體──生成聳動半透明關節化的書寫呈現,卻又害怕這樣的書寫足以引發從此便不再能以身體所能支配局部器官的自由行動而焦慮不已──於是開始了先是器官記憶的濃烈反覆、反噬,如噬尾蛇一樣貪婪不分頭尾地吞噬自身感受裡的魯莽──這個跨年的跨域書寫歷程也同時試煉著如何掙扎以預作垂死的準備,那是所有生命源頭必然伴隨的警示。如此宣示更多的是因為再不試著說服安頓自己,它將難以繼續往下一個未來時間邁進。
一旦意識到了,它就會變成一道不太容易越過的關卡。因此,無論如何這都足以讓人冒著與這名為「小說」的書寫一起死去的風險,來進行這個書寫的實驗之路。
試著同步展開透明距離的理論性描述,純然是基於全球災難時代對世界的必要回應。多少有種救贖心態:因為世界性的武漢疫病──恆常的反覆慘烈形同文明生活的逐步滅絕,於今沒有人會再噤聲,隨時都該滑移進時間所掩護著已然凹陷的失落內裡──避免感染籠罩的擾動,卻在看似沒有距離的間離化阻隔中持續斷鏈。
所有似 Jelly 狀色彩的奇形物質,能見度或許還要能再好上許多才行,它從來都不是主動式的對著世界進行任何形式的阻絕,在看似空氣般的物態裡,卻無法直接接觸、連結、跨越,而是硬生生的、可見的斷裂成為無法滲透的分立──但是必須盡量排除關係的局部化──以保有常態的有機與持續可逆。
噢!你總還是能看見整個事件的生發過程甚至是結果的如何到來,卻無法嘗試著透過什麼物質介面而得以讓它們絕對化的連結為一體。可見與不可見在此都偏移為超過物理事態常軌所能解釋的辯證或對立關係。不論如何,我都想試著述說些什麼。「成為光、成為書寫的焦聚」,或許終究也會成為一種極度深切又具有島嶼在地庶民特徵的終極訴求。它不僅能穿透自身,還能折射明晰的圖像、伴隨不斷的隱隱音聲,驅動能量鎔鑄一切的偶然與必然。它看似虛擬,卻能緊緊追索著如雷射光的擊打般,連續地一擁而上,好更趨近成為光的終極可能。
一直有兩個不同年齡的西格以及改名後的啟煌交錯在與哈古棯之間進行著不甚同調的交互對話與談論。或者這整個事態就像是實體與虛擬之間的試圖跨接。但可以立即確認的這可不是數個鬼魅間的談話──卻更像是重現過往又酷似夢境交錯的幻覺一般──表象上看似無礙的現實已經全面脫軌,並且不再以現實的線性時空被認知。它們藉由完全不同的存有載體來示意並揭露它們實存上的必要。不斷地岔出、意外取代規律、交疊纏祟出逐漸逼向清朗透亮的可辨識符號──圖像──形體與回音:西格與其自身啟煌。因為西格從小家裡所有的事情,幾乎都只能是他自己片面單向理解到的,而且經常是各種外人對他的道聽塗說!
互為虛構且相互對應的持存時空:雜多歪斜、偏移、函化的疊置。得以不斷演繹、夾敘的時間與空間──想像著與宇宙論對位修正的當代負人類世本體隱喻──此刻能回應的,似乎就只是世界現實裡一切無止境紛雜實存的消耗性選項。如果這是需要被迫做出即時的選擇,它的確總是能在關鍵時刻裡被重新決定、改變路徑成為無法預期的生成。想想個體生命,絕處逢生、隨機又任意性的可能寓意便能了解。
聽著他人的生命歷程來轉置成為故事的起點。對我來說,小說書寫的某種潛隱定義似乎就已經在那裡萌發。
如果試著「回到母親……」永遠是一條活路:那麼回到哈古棯母親黃素柳水上鄉柳仔林的故居,勢必成為進擊頹敗家族必要的地方誌與庶民歷史的繞道之路。試著返回西格的母親美玉的獨特
日治年代困窘,讓時代集體的生活曲折因而得以平復、得以成為生命的常態。即便那種時間越來越在感受上有著更為清淡的過往羈絆,也自然是滄海桑田後的殘破現實。是無人歡娛的時間軸線裡所牽動的消逝場域,獨留個人的唏噓與哀嘆。一切原來我們所不知道的變徵之貌,悵然之餘竟也開始充盈起古怪的絕對性格。
試著想像,或許所有的小說創作都必然是透過個別生命的微觀盡述,好沾染一點文學性的驅力強化,才足以傳遞深度感知上的巨觀鋪陳而藉以開拓人生、得以舒化生活,生成面對未來繼續生存的能力。這聽起來,十足就已經是個有點年紀的人才該會說的話!
試著透過這本被我名之為小說的書寫以及它從當代視覺藝術觀念上轉置的真實來消敉虛構──非虛構間的無意義爭端,這一切也無非都只是自己的多慮。全文人物都是夾雜真實或虛構的姓名與歷程,但是卻未必都循著他們的現實人生作為書寫的底蘊。
如果詩正在遠離世界或者正在極端地透明化、黑化──未來的世界,以後會否突兀的將只剩下「小說家」?
二○二一年五月中旬之後島嶼的武漢肺炎疫情狀況開始急遽惡化,它正試著反轉幾年之間的偶然平靜,趨向世界的絕對化不幸、或者那已經逝去生命的數千萬人的無辜?慘烈程度──跨了西班牙流感百年之後──只有二○二二年「島上都死光了」的假設性概念推演,足堪比擬!
多少開始懷疑這部「小說」書寫,真能有機會出版問世?或者只能成為某種下一輪頹世人類考古的潛隱遺誌?說穿了,難免有種深沉難鳴的莫名感:跨年裡很多個天剛蒙亮的清晨,總能在非預期瞬間便看見窗外無聲息的遠處,光亮弧線裡滑溜過一列五節的騰空輕軌車;窗外近處園子裡的蟲鳴似乎也都會切換距離般地配合著那樣的不真實感,好讓僅有的書寫能夠更全面地沉浸在非現實的世界之中!
本書的出版,除了兄姊、Jeanette、Didier……的鼎力支持,琇媛貼心的讀者角度。翊峰老師的專業提點……全都提供了莫大的幫助,謹此獻上衷心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