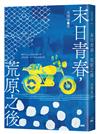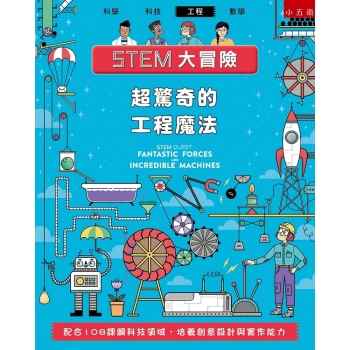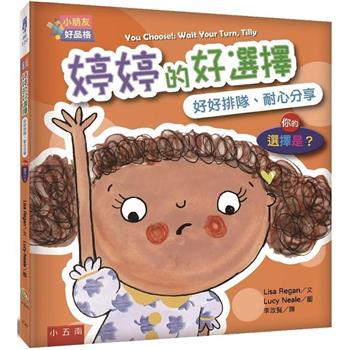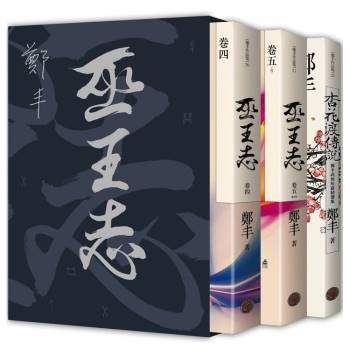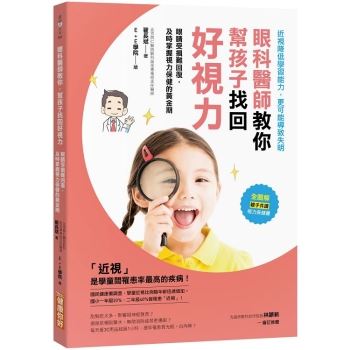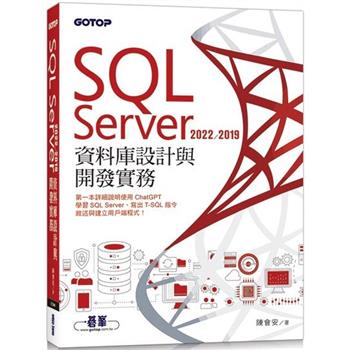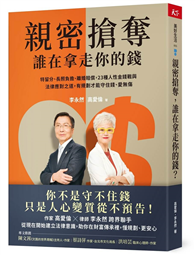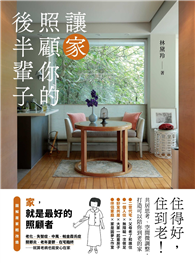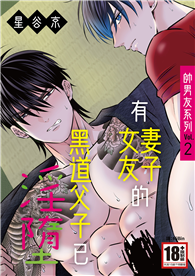騎著Desire穿梭在城市裡,迎風面海,並不都是浪漫的事。
一段無聲無光的青春末日 從中北部走向南方的自我放逐
留下的還剩什麼?
周芬伶──專序
任何舊時代的結束,都是為了新階段的開始。
當世界瀰漫末日倒數,抗議議題充斥虛擬社群與實體街道,
青春究竟應該是何模樣?
以大學生「我」之視角觀點,一輛命名為「Desire」的機車,啟動了三段時間軸,述說經歷學生運動、疫情與AI興起的種種過往回憶及想法,交織出童年時代隱晦的家族暴力、對愛的各種渴望,以及成長過程中所累積的創傷感。
看青春一代在失語和幻滅中,於島嶼移動的過程裡,如何面對三十歲前後追尋自我認同與慾望探索的各種遲疑、感傷及無奈,找出屬於自己的聲音並錨定存在的意義。
二○二五年,又迎來一場末日。
網路上集體歇斯底里,預言家紛紛把末日地點指向了我們周圍的海。
這些日子,我們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封鎖,隨後步入了人工智慧迅速發展的時代。
我經常思考未來人KFK五年前的話,想著他說對了什麼,說錯了什麼。以及他有找到他想找的人嗎?
如果我能成為未來人,我會不會想回到那個世界本應結束的二○一二年,回到荒原,然後告訴那時的自己,將來會發生什麼?
作者簡介:
高博倫
1992年冬季生於台北盆地,桃園人。畢業於東海大學外文系,並取得中文系碩士學位。寫作啟蒙於大度山,在台中的歲月裡完成第一本書《其實應該是壞掉了》。之後帶著寫作計畫移居台南與高雄,用心生活,終於得以常去看海、聽海、摸海,第二本書因此誕生。成書之際,即將前往美國堪薩斯大學(KU)英文系攻讀文學創作博士學位,也許會遇見通往奧茲世界的龍捲風。
章節試閱
Desire
「我不要現實,我要魔法!」
—白蘭琪,《慾望街車》
二○一二年,世界沒有迎來末日,但是回過頭去看,會發現那是個前爆炸時代。
❖
荒原裡散落著學生駐紮的帳篷,像是遊牧民族,我們來了,然後也去了。
某天早晨,我碰見從帳篷走出來,黑白長髮摻雜卻整齊梳綁的秀如。我們站在濕冷的毛毛細雨中。她剛從醫學系休學,加入我們,「切是什麼樣的人?」她問我。
我說,我第一次看見切,是看他在禮堂的話劇表演。那時他還短髮,演一個純情高中男孩,追不到愛慕的女生所以使出渾身解數的故事。
現在的切呢,明明是資工系,卻是中長髮,抽菸喝酒的左翼讀書會會長,整天馬克思來馬克思去的。
「你也是這樣嗎?」她問。
我想著冬天,說起我們認識時,是我參加話劇社的寒訓。我們繞著舞蹈教室練習走路,忽然大家小跑了起來,他一直跟在我後面,踩到我的後腳跟。中間休息時,我們在外頭晴朗乾燥的溪谷,對面的廟在誦經,他遞水給我。他說他看了我在文學獎上的小說,雖然我是佳作,但他很喜歡我在小說裡處理的勞動心理問題。我那時才知道,切就是那屆小說首獎。
後來讀書會愈來愈多工作,我們就離開話劇社了,也說好一起互相評論對方的小說。
❖
我還沒擁有機車以前,都是切載我。我們和幾個社會系學長一起住在夜市街裡的小別墅,院子走可食地景風,高麗菜九層塔、地瓜香蕉樹,門廊有圖書館不要的舊書及撿來的藤椅,窗掛彩虹旗,儘管除了我以外,每個人都直到不行的直。
他常載我穿過擁擠的夜市北街去大學。我們的大學對比居住的夜市街過於寬敞而古老,那鮮明的對比只靠一條小溪及森林區隔。
我們也常鑽入夜市南街更加交錯混亂的巷弄,那裡庭院處處綠蔭,初秋海吹來的風已經很冷,我必須瑟縮在他的背後,我們騎去斷崖看夕陽,眺望海。我們一路騎,充滿自信、能量,還有二十幾歲的厭世、傲慢。
「幹,你趕快買車啊。」切對我說。
我說我一直在打工存錢,快了。
「到時候換你載我了。」
奶奶小時住過的濱海小城在荒棄半世紀後,迎來了許多帳篷,學生陸續進駐,想要守護這片荒原。潟湖、野鳥、泡在海裡的建築殘骸,我最初不明白這裡被剷除開發有什麼不好,但還是跟著讀書會,坐在切的機車上,蹺課去荒原。
夜深,大學依舊喧譁,讀書會裡,簡報、傳單宣傳著荒原要如何消失:濕地將統統填平,筆直寬敞的道路將取代這裡的河道及森林,死寂的鄉野很快就要為我們的城市帶來假想的財富及科技生活。
二○一二前後那幾年,人們確實由上而下做起新荒原的夢:
荒原要拔出更多的樹木,安插一株又一株的綠建築生於其中,有影城、美術館,也有醫學大學的新校區、科學園區,朵朵綻放。
荒原要蛻變為整齊綠洲,自行車道、輕軌電車串起幾座新興濱海住宅社區,還有共融式遊戲場,結合百貨、市集,荒原裡將長出五分鐘步行生活圈。
荒原會是我們做過最大,關於海邊的夢。
美夢成真有數個步驟,只要拆除荒原已經沒住人的老屋,反正這些廟、民宅早已被海水泡爛。只要說服黑面琵鷺找到新的棲地,甚至說服這些北亞候鳥加入荒原的夢:鳥群可以自在棲息於生態公園,可以融入嶄新的荒原。只要一切順利,新荒原會逐漸浮現。只要我們相信,有天我們張開雙眼,荒原將不再只是荒原。
文學院樓梯口下的地下教室擠滿了人,冬天很冷,裡面異常溫暖潮濕,眾人討論著追求新荒原的先驅者。當時不是每個人都有智慧型手機,桌上堆滿文宣、書籍及資料,眾人議論著先驅者的夢想,建立新的住宅基地,是為了讓更多的錢湧入荒原,年輕人永遠買不起。他們夢想著新的濱海城區可以吸引更多錢潮,想像其如海水潮湧淹腳目。然後年輕人、藍領人都要被驅逐在外。
地底下的讀書會鼓譟四起,眾人提議阻擋這些先驅者,不曉得怎麼回事,我從角落抬起頭來時,切已經站在木桌上激動地說了些什麼。
幾天的時間,活動在社群平台上發酵,他們搖旗吶喊,來自各大學的機車蜂擁而至。二○一二年進入尾聲,世界沒末日。占領荒原的行動,竟即將進入第二個月。切和我約定要寫小說,只有我寫完。
荒原呀。
奶奶過世前的暑假,我們從舊城家裡叫了部計程車,說要去吃炒米粉。一路上她和司機像熟識的老友聊著他們互相推薦各種城裡城外的中醫師,有幾度我還以為他們要吵了起來。
炒米粉攤的對街是海的方向,就是荒原了。
現在回想,那炎熱的中午奶奶不是要去吃炒米粉的吧,她可能就是要找個藉口再回荒原看看,至少吃到她心心念念的米粉。
可能睡前一直想著奶奶的事情,夢裡忽然一隻黑麻雀撲來,張口要把我吃掉。奶奶過世前說自己很常看到黑麻雀。我冒著汗,但不覺得這與死亡有關。
醒來後,我和切急忙出門。
秋天的季風猛烈吹襲,我把手伸進切的口袋,他飆著白色的光陽機車,時速七十有時八十,我瞇著眼看著儀表板以及路上快速流逝的風景:漢堡店、報廢的汽車、鐵皮屋上的鴿子、土地公⋯⋯我們奔馳過中午前還沒什麼人車的夜市街。很快我們來到海風直吹的公路,更冷了,我有點後悔太晚起床,出門前沒有多帶條圍巾。
那天我們這麼急,是收到簡訊荒原出了事。電腦網路不穩,我們的手機都還是按鍵式,只隱約知道凌晨失火了,而火已經撲滅了,沒人傷亡,但警察希望學生帶著帳篷離開荒原。
奶奶愛吃的米粉攤沒有開,兩條防水布用紅磚塊壓著,掩蓋堆放街邊的鐵桌椅。
我們騎入破碎的柏油小徑,這條路從來沒被養護過的模樣,到處都是坑洞,雜草橫生。我尋著可能的黑煙,但此時晴朗乾燥,藍天白雲,冷冽的風吹得我什麼也聽不見。
還得穿過一處小村子,這裡還有零星居民,白日大門深鎖,有些屋舍年久失修,老人只有在溫暖的天氣才會出門閒晃。過了個急彎,隱約能聞到海水,終於看見下坡處聚集的帳篷,有浪濤聲,不見警察。幾個人或蹲或站於路邊抽菸。陸續有人上前跟切說明,荒原裡有好多東西正同時交換著:眼神、手、香菸、情報,有人很久沒洗澡的氣味。
燒掉的是海神廟。
雖然廟早就荒廢了,但有人說是古蹟,有人說正是如此所以才有人放火燒了。火是在接近天亮時燒,守夜的學妹也不曉得怎麼燒起來的,海神廟接近海灘處,離他們的帳篷太遠。宿醉中,他們還以為是前一夜未熄的篝火。
海神廟燒成焦黑的骨架,矗立在濕地與海灘交界處,像是剛經歷一次未被記錄的戰爭。現場沒有火,也沒有警察,只剩幾條還在冒煙的繩索和潮濕地上的腳印。有人的帳篷不見了,或許是被風捲走了,或許是誰在半夜收起帶走了。總之,只剩痕跡。
切把機車停在一塊還冒著蒸氣的泥地上,低頭看著它,像在看某種錯過了的東西。他穿著那件深色風衣,帽子沒戴好,海風吹得他頭髮全亂。他用鞋尖踢了一下地上的燒焦塑膠,冒出一股刺鼻的味道。
「今年真的是馬雅末日了。」我想起來。
切沒反應,只是轉頭看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剛從夢裡醒來。他走過焦土邊緣,踩過一片軟爛的紙板,彎腰撿起一張燒掉一半的影印紙,紙上還看得出是某次會議的工作分配表。
「他們應該是凌晨撤的。」他說。
他們,指的是其他人。
我想說些什麼,像是「還好沒人受傷」,或「我們至少還有這塊地」,但話卡在喉嚨。
切轉身走向海神廟的殘骸,他站在那塊燒黑的入口處,靜靜地看著廟內。
我走近他。他的背影站在煙霧與陽光之間,身影斷斷續續,像是從舊錄影帶裡撕裂出來的一格畫面。
「我們是不是來太晚了?」我輕聲問。
切沒有回我。但我知道,他也在問自己。
風愈來愈大,我和切走回到更高的崖邊,吃了頓野鳥觀察小組準備的飯糰。
吃完後,我們又出來看海神廟,外皮焦黑,後方是灰色的海。這樣看下去,那其實是很有力量、生氣的黑,還有熱氣,我能從風裡感覺到海神廟黑色的肌膚存在著新生的溫度。萬里無雲,廟就是剛誕生的黑色海神,沐浴在秋日的光裡。
我想像著奶奶在年輕時,曾經對海神說過的話。隱約之中,我發現廟裡有人影。
切說我應該是看錯了。但後來廟裡真的走出了一個人,他走了出來,拍了拍手上的黑燼,緩緩走向海。
「喔是他呀,國際生。」切說,「他是建築系的國際生。」
他側著臉,身影瘦長,戴眼鏡,還有一頭凌亂金髮、汙髒的襯衫及牛仔褲。
國際生拿出單眼相機,對黑色的海神廟拍照,然後瞄準大海。
我想像他的攝影成品:黑白的荒原、火燒過後的海神廟、老漁夫的滿臉皺紋的特寫、抽菸的海邊少女,還有海中載浮載沉的洋娃娃。他將累積豐富的攝像作品,在某個美國城市的藝廊展出,侃侃而談他的遠東見聞,他的叛逆,他如何踏出舒適圈然後遇到挫折,最終成長,在海神廟獲得媽祖的啟示。我想像藝廊中的眾人舉起酒杯,其中一幅牆面作品上,筆直的新公路,一個發愁的老太太坐在米粉攤。
我和國際生對到視線,他放下相機,揮了揮雙手,有自信的高加索笑容,正如大部分的美國白人,活在迪士尼世界。我好像能聽見背景的罐頭噪音,看不見的觀眾,大家都在觀賞一場由他主演的美國青春電視喜劇。我還不認識他,但我直覺他是個習慣全宇宙繞著他打轉的人。
我假裝沒有看見他,別過頭要和切說話。切倒是也對他揮揮手。
這裡的海水每年都在上升,海神廟早晚要被吞沒,很多人不懂縱火的理由。
切說,警察要學生們這週撤離,因為要調查縱火。
「可是我們的帳篷不在廟旁,不影響他們調查吧?」我說。
我們都沒說什麼話,大約猜測得到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清場理由,我們遲早要從荒原撤退。
我想到了撤退這個詞時,心裡浮現了種感覺,覺得海神才剛從燃燒的黎明那刻誕生,我感覺世界將有所不同,我將有所不同。
國際生正朝著我們走了回來,樹叢邊有許多麻雀,一點一點的。我仔細瞧牠們,想著奶奶死前說的黑麻雀,以及我昨晚夢到的黑麻雀。國際生小心翼翼經過牠們,輕輕跳起舞。我再次迎上他的目光。
「黑麻雀嗎?你應該要幫忙找找黑面琵鷺的蹤跡吧。」切說著,今年黑面琵鷺還沒從西伯利亞下來,他希望能多一點照片才能引起大眾對荒原更大的關注。
後來我才知道,那晚其實還有一場節目。
反媒體壟斷的浪潮下,幾個高中及大學生組成的素人電台準時在八點開播,風還沒把天線吹斷,延長線也還沒燒。
他們照常在節目開始時播了一小段重複播放的海濤聲,然後,是一個女生的聲音開始朗讀。
她說得慢,一個字一個字像是從帳篷的縫裡滲出來的:
「我們記錄海及島嶼的聲音。我們不是大電台,沒有廣告,也不是主流媒體……
我們只是在記錄。記錄那些沒人記得的聲音,沒人要聽的故事。
如果你正在聽,請知道你不是一個人。
我們正在抵抗一種失語的現代性。」
她停了一下,風聲從麥克風裡捲進來。
「今晚我們不會播放新聞。
今晚我們只會播出火。
是的,那場火……
我們讓它被聽見,在我們心裡的某塊地方,還有一團火。」
我記得那時我正坐在山坡邊,看著焦黑的海神廟。
他們說這是一場草根實驗,說這只是學生的短暫占據。
但在那一刻,我覺得真的可以相信,他們,我們真能打破什麼。
我甚至想把耳朵貼在荒原的泥土地上,去聽那句話怎麼滲進濕地裡,怎麼穿過愈來愈低的地下水,傳到某個也一樣失語的地方。
❖
其實一開始,切也根本不打算在荒原留下。
他說只是來看看,看看荒原會變成這樣、看看帳篷裡的人是不是和讀書會裡那些人一樣愛講幹話,看看他們能這樣克難玩多久。他甚至覺得搞學運的人都太天真,怎麼可能改變世界。
可是第一個晚上,也許是因為他看見了秀如吧,他就沒回夜市街了。
他睡在已經失去神像、失去香火的海神廟後方,一處樹叢邊,那條祕密小路通往潟湖灘地,有防空洞,只有幾個人知道。
後來有人發現他早起幫大家煮水,還撿了幾塊廢棄木板釘了一個物資架,上面貼了一張寫著「你需要就拿,拿了也不必還」的紙條。那句話從來沒有開過會,也不是哪個小組決定的,但就這樣流傳下來了,像咒語。
接下來的幾天他沒說什麼話,只是不斷幫人補帳篷、接電線、搬水桶、修工具。有幾次志工在清晨觀鳥時不小心踩進很深的泥灘,是切拿著繩子爬過去拉人。他也幫電台重新接線,讓大家晚上能聽見詩歌朗讀、音樂和物資公告。有人問他是不是專業技工,他說他只是學過一點電機。後來他們才知道他是資工系的。
荒原放映會本來只是放幾部網路上抓來的紀錄片,是切第一次放了自製的剪接。他拿手持錄影機錄了黑面琵鷺飛翔的樣子、農田裡破裂的水泥路、還有一位撿破爛的老奶奶站在媽祖塗鴉下等垃圾車。他說這才是這裡的影像。他還找人錄音,用收音筆收海的聲音、廟牆的風聲、大家開會、唱歌的模樣。
沒有人叫他「負責人」,但所有的設備、時間表、物資清單最後都由他確認。可能,後來有人說他是獨裁者,後來有人說他太固執、太完美主義,但仔細想想,只要東西壞了、氣氛鬧翻、食物短缺,大家還是會去找他。
月圓的那晚,篝火旁的小音樂會剛結束,我看見他一個人坐在海神廟旁發呆。他手裡捏著一張剛打印的會議流程表,風把它吹起來,黏在他臉上。他沒生氣,只是慢慢把紙抓下來,用夾子夾回筆記本裡。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見到他,他背著光,滿頭大汗,一頭熱追求自己喜歡的事。切就是那種人。你永遠不知道他在幹嘛,但他早就準備好一切,讓你可以留下來。
幾乎是玩累了,切才肯跟我回到夜市街的家裡。
❖
我在自己的系館裡再次遇到國際生,不曉得為什麼加深了我對他的反感。事情還是要從劇場說起。
教現代戲劇的老師被我們稱「X教授」,他也許少了一點誇張的漫威感,但神韻及威嚴頗近。我們的X教授是密西根人,光頭、有點嚴肅不好招惹,只是不但行動敏捷,還熱愛運動,尤其熱衷橄欖球,早些年他還指導過我們大學的校隊。他的戲劇課一直很熱門,上課從不需要點名,甚至會邀請學生參加他課後的劇場活動。而這是我第一次被他邀請,我們要研讀田納西.威廉斯的《慾望街車》。
星期四晚上,劇場教室的光照亮外文系中庭,X教授訂了披薩、汽水招待這期第一次聚會。
總共十五人,X教授坐在舞台前緣,幾個高年級的人圍著他熱絡聊著,忽然我就看見那荒原到處拍照、和麻雀跳舞的建築系國際生。他和X教授像是熟識那樣,坐在一起,講到了某個我沒聽清楚的事,兩人抓著披薩捧腹大笑,像極了父子溫馨聚餐的畫面。也許待會就要一起去沙發坐著看超級盃了。
吃完餐點,大家開始在觀眾席前坐下瀏覽劇本。選角還沒完全確定,但X教授已經宣布了史丹利這個角色。
「史丹利.考瓦斯基,」X教授摸了摸他堅挺的鼻梁,「和我們熟悉的威廉.福克納筆下的南方男人會是很好的對比,福克納小說裡寫的那些南方沒落貴族的壓抑、憂鬱及脆弱,你們會發現和這位史丹利截然不同。首先他是波蘭裔工人,你們可以想像他是個情緒化的肌肉男,他沒有任何一點優雅或是憂鬱的氣質,而是一種原始充滿力量的存在⋯⋯」
X教授看了國際生一眼,「我上週下午在牧場旁看到一個年輕人踢足球,小聊了下,發現這年輕人以前也是高中話劇社的演員。他的氣質,我必須說,和史丹利.考瓦斯基那種生猛、暴躁的性格很不一樣,我甚至覺得他戴著眼鏡的模樣,更適合演我們在夏天前演出的《推銷員之死》中的伯納德。但我想讓這位年輕人來自我介紹一下,讓各位聽聽他的嗓音,也許大家就會同意我這次的選角了。讓我們歡迎建築系的史丹利。」
Desire
「我不要現實,我要魔法!」
—白蘭琪,《慾望街車》
二○一二年,世界沒有迎來末日,但是回過頭去看,會發現那是個前爆炸時代。
❖
荒原裡散落著學生駐紮的帳篷,像是遊牧民族,我們來了,然後也去了。
某天早晨,我碰見從帳篷走出來,黑白長髮摻雜卻整齊梳綁的秀如。我們站在濕冷的毛毛細雨中。她剛從醫學系休學,加入我們,「切是什麼樣的人?」她問我。
我說,我第一次看見切,是看他在禮堂的話劇表演。那時他還短髮,演一個純情高中男孩,追不到愛慕的女生所以使出渾身解數的故事。
現在的切呢,明明是資工系,卻是中長髮,...
目錄
前言 白蘭琪的詩意追尋
尼佛拉佐娃
黑麻雀
後記 必須踏上的旅程
前言 白蘭琪的詩意追尋
尼佛拉佐娃
黑麻雀
後記 必須踏上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