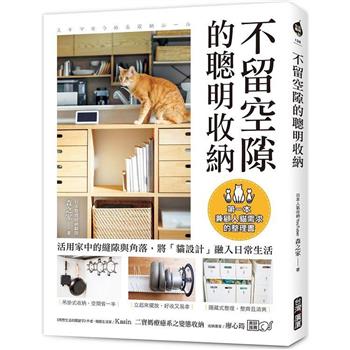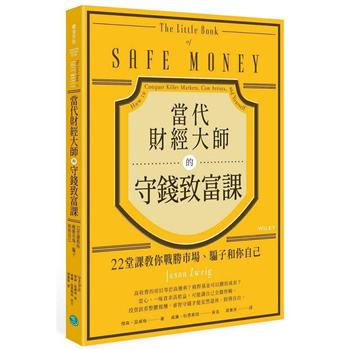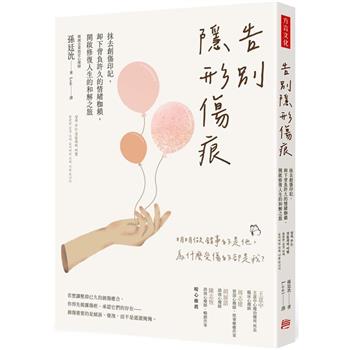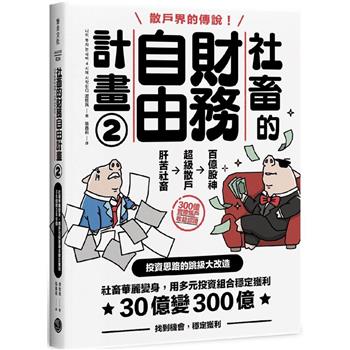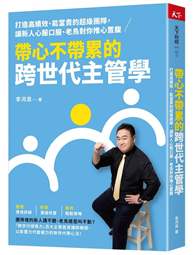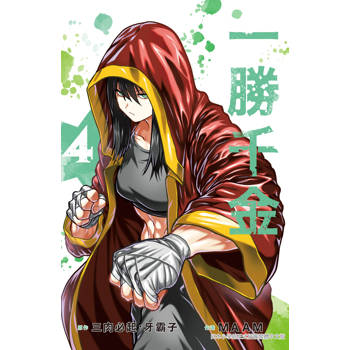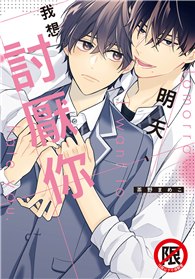說家奴與長隨
還是從《水窗春囈》所講的戶部小吏向大帥福康安要錢的故事說起:在這個故事中,小書吏要把一張名片遞到福大帥手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為此前後花了十萬兩銀子,這可不是個小數目。那麼,他這些錢花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就涉及到了清代政治體制中另外一類人,就是官員的家人與長隨了。他要見這位炙手可熱的大帥,要把名片遞上去,先要過的就是家人、家丁這一關。這裡,從最外層的家丁,比如門子,到帥府的管事,再到大帥的貼身跟班,也要過無數的關口,而紅極一時的福康安,身邊的人層層疊疊,不在少數,所以他才要花費十萬兩之巨。
要說官員的家人與長隨,其實有兩個不同的層次,是一個很容易混淆的內容,第一個層次是真正的家下奴僕,是侍候官員家庭或家族的人,他們照料官員及家屬在家中的生活起居, 與外界一般聯繫不多,其中有些人成為歷史上有名的豪奴;第二個層次就與政治體制掛鉤了,他們是隨主人赴任到官衙的長隨、家人、門子、跟班等等。以地方州縣官府來說,官衙分為內外兩個部分,外部主要是三班六房和差役等人,內部則主要是官員與師爺所在的地方。內外兩個部分怎樣聯通呢?就要靠這些所謂長隨、家人、門子了。一縣之中,有那麼多吏胥,縣令不可能一一去指揮他們,就用這些自己帶來的或衙門中原有的長隨之類來傳達指令,同時也由他們把外面吏胥差役等的情況報告給縣令。有時,縣令所請的師爺有指揮書吏們辦文案的情況,但大多數時候,家人、長隨之類才真正內外溝通的橋樑。性質上他們雖屬於「官員僕隸」之列,卻也在官僚體制中佔有一席之地。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六,講了一個「冥間」故事,說陰間也有共識:在人世上,關係民生最多的,當然還是當官的,這些人對於百姓來說「造福最易,造禍亦深。」但世上最為民害者有四種人: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這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作官的人也許還要顧忌自己的官聲與業績,但這四種人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四大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故事雖是冥間神道所言,卻也貼近清代社會的現實。1 四種人中,前兩者,就是我們上面講到的吏胥,後一種就是我們要說的家人、長隨了。清代,家人、家丁、長隨、跟班這類人圍繞在官員周圍,關聯著官衙內外,「無官之責,有官之權」, 是地方行政的有機組成部分。簡單直接的理解,這些人是官府主官從家中帶來或雇傭來僕役。趙翼《廿二史劄記》說:「今俗所謂『長隨』,則官場中雇用之僕人,前明謂之『參隨』」。前面提到的段光清,赴浙江上任,只帶了貼身家人一人,其他的就只有到地方再考慮雇傭或在前任的人中挑選留用了。而《紅樓夢》中賈雨村到應天府上任,一個隨從也沒帶,那個在案前給他遞眼色、打招呼,後來又給他講「護官符」的「門子」, 也是前任留下的。
家奴雖然與長隨不是同一類人,卻以其特殊身份危害社會。清代京城中王公貴族、高官顯貴之家的奴僕,影響惡劣;地方上則是官員們身邊的長隨、家丁等,有世為其業者,是雇傭而來,也有官員從家中帶來赴任的,其影響與吏胥類似。長隨之類因為與官員本人更接近,有時,其惡劣作用甚至會超過吏胥。清王朝對這兩類人的限制大體上是兩方面,一是限制家奴的行為,貶低其身份;二是限制長隨、家丁的數量。制度規定:布政使、按察使准帶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帶三十名,州縣只准二十名,州同、縣丞及以下官員只能帶十名。一般講,武職官員所帶會略多於文職人員,而旗人官員則較漢員加倍。乾隆時定制,旗下將軍可帶家人一百五十名之多。而事實上,官員上任,所用長隨家人的數量,從來就超出制度限額,有的一州縣, 長隨數往往有數十百人之多,衙門裡的所有事務,無不參與, 從職司上講,他們是吏胥與官員之間的媒介,但實際中,他們又往往以官員的傳言者出現,成為吏胥的監督者。多數情況下, 長隨與吏胥沆瀣一氣,為害一方。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細說清人社會生活(下冊)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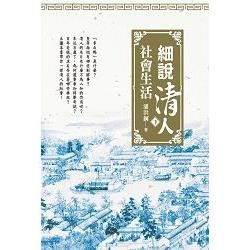 |
細說清人社會生活(下冊) 出版日期:2015-06-03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Others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 272 |
科學科普 |
$ 282 |
文化研究 |
$ 282 |
文化研究 |
$ 288 |
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細說清人社會生活(下冊)
本書內容涉及清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吃飯穿衣、抽煙喝酒、社會交往、官場百態、婚姻禮俗、文化傳承等。圖文配合,相映成趣,不少圖片具有史料價值。
此書基本以清人入關至清帝遜位為時間斷限,比較細緻、風趣地介紹了清代從宮廷到民間、從漢民到旗人、從南方到北方的社會生活,包括最基本的衣、食、行,到婚姻、歡場、官場、科舉,以及匾額、印章、名片、手紙,可以說應有盡有。
本書不像其他專著那樣通篇都是抽象的理論和枯燥的論述,作者筆調輕鬆閒適,用細節還原歷史。
作者簡介:
潘洪鋼
男,滿族,1960年生。1983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現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明清史與近代社會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工作。曾在《民族研究》、《光明日報》、《民族譯叢》等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及譯文60餘篇,主要著述有《明清宮廷疑案》、《細說清人社會生活》、《官商兩道——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商人與官場》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八旗駐防族群的社會變遷研究」,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多項。
章節試閱
說家奴與長隨
還是從《水窗春囈》所講的戶部小吏向大帥福康安要錢的故事說起:在這個故事中,小書吏要把一張名片遞到福大帥手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為此前後花了十萬兩銀子,這可不是個小數目。那麼,他這些錢花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就涉及到了清代政治體制中另外一類人,就是官員的家人與長隨了。他要見這位炙手可熱的大帥,要把名片遞上去,先要過的就是家人、家丁這一關。這裡,從最外層的家丁,比如門子,到帥府的管事,再到大帥的貼身跟班,也要過無數的關口,而紅極一時的福康安,身邊的人層層疊疊,不在少數,所以他才要花...
還是從《水窗春囈》所講的戶部小吏向大帥福康安要錢的故事說起:在這個故事中,小書吏要把一張名片遞到福大帥手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為此前後花了十萬兩銀子,這可不是個小數目。那麼,他這些錢花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就涉及到了清代政治體制中另外一類人,就是官員的家人與長隨了。他要見這位炙手可熱的大帥,要把名片遞上去,先要過的就是家人、家丁這一關。這裡,從最外層的家丁,比如門子,到帥府的管事,再到大帥的貼身跟班,也要過無數的關口,而紅極一時的福康安,身邊的人層層疊疊,不在少數,所以他才要花...
»看全部
目錄
下冊
前言
說清代的吏胥
清代地方官判案二三事
說家奴與長隨
說清代官場稱謂與變遷
清代的諡法
福建的宰白鴨
科舉概說
說大挑與丑官
科場如遊戲
高齡考生趣聞
神童善對與背誦
話說旗人
一、滿族人口之謎
二、旗人性情
三、旗人生活的貧困化
四、經商等謀生手段在旗營中悄然出現
清代地方官判案二三事
說清代的冷僻姓氏
說說清代的謠諺
一、民諺也能反映官場情況
二、歌頌清官與譏諷貪官
三、民諺作為一種輿論的作用
清人的名片
店名匾額拾趣
清人閒章拾趣
從墟市說到超市
一、墟、市釋名
二...
前言
說清代的吏胥
清代地方官判案二三事
說家奴與長隨
說清代官場稱謂與變遷
清代的諡法
福建的宰白鴨
科舉概說
說大挑與丑官
科場如遊戲
高齡考生趣聞
神童善對與背誦
話說旗人
一、滿族人口之謎
二、旗人性情
三、旗人生活的貧困化
四、經商等謀生手段在旗營中悄然出現
清代地方官判案二三事
說清代的冷僻姓氏
說說清代的謠諺
一、民諺也能反映官場情況
二、歌頌清官與譏諷貪官
三、民諺作為一種輿論的作用
清人的名片
店名匾額拾趣
清人閒章拾趣
從墟市說到超市
一、墟、市釋名
二...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潘洪鋼
- 出版社: 龍圖騰文化 出版日期:2015-06-03 ISBN/ISSN:978986388017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8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