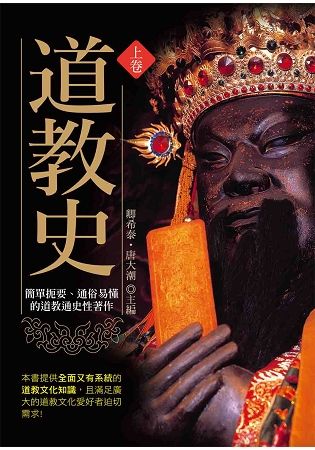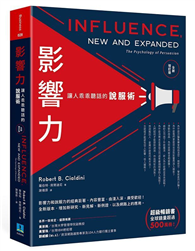序
引言
在中國歷史上,「道教」一詞曾被賦予過廣泛的含義。它最初的意思是指以「道」來教化眾生的各種理論學說和實踐方法,諸子百家都曾以「道」來稱呼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儒家、墨家、道家、陰陽家以及佛教等,都曾自命或被認作是「道教」,但這種意義上的「道教」顯然不是我們要談的。
我們所說的「道教」,是指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上,沿襲方仙道、黃老道的某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漸形成,以「道」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過某種實踐經過一定修煉有可能長生不死、成為神仙的中國本民族的傳統宗教。它尊老子為教主,奉老子的著作《道德經》為主要經典,並對其進行了宗教性的闡釋。它在創始之初主要流傳於民間,曾同當時的農民起義相結合。魏晉以後,封建統治者出於某種需要對其扶植、利用,使流傳於民間的道教逐漸上層化並與儒家綱常名教相結合,在有些朝代還捲入了宮廷政治活動。在民間,則繼續流傳著通俗形式的道教,從中還演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組織,在一些農民和平民的起義鬥爭中,成為發動和組織民眾的旗幟和紐帶。道教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籍書文,後多被編入《道藏》。道教對於中國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哲學、文學、音樂、藝術、醫學、藥物學、養生學、化學、天文、地理以及社會心理、社會習俗、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都有過不同程度的影響,有過一定的貢獻,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部分内容
第一章道教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
第一節秦漢社會危機與統治思想宗教化
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道教,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關於此,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例如:《魏書•釋老志》稱:「道家之原,出於老子。」葛洪《枕中書》認為道教起源於「二儀未分」之時的「元始天王」。《隋書•經籍志》則雲:「道經者,雲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以為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天仙上品……諸仙得之,始授世人。」《隋書》,第1091—1092頁,中華書局,1973。如果說《魏書•釋老志》的說法還多少有點根據的話,那麼,《隋書•經籍志》的說法則完全是荒誕無稽之談了。然而,這也反映出道教的起源問題確有其錯綜複雜的特點。
宗教同其他社會歷史現象一樣,其產生總是與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相聯繫,有其產生、發展的過程。道教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亦不例外。當然,道教與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相比,在起源上有它的特殊性,這表現在:它不是由某個教主在短時期內創建的,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醞釀過程。
具體說來,道教的正式形成是在東漢的中後期,促使其產生的客觀歷史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深重的社會危機。
西元前230年到西元前221年,秦國連續吞併了韓、魏、楚、趙、燕、齊六個大國,中國社會由戰國進入秦漢時代。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但是,秦漢社會的發展,又受到封建生產方式的制約,呈現出時起時伏的波浪式發展特徵。即使在秦漢鼎盛時期,社會矛盾依然十分尖銳,在封建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對廣大農民的剝削和壓迫是殘酷的,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被大量兼併,出現「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的局面。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日漸嚴重,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反抗也日益增多,終於引發了以陳勝、吳廣為首的農民大起義,秦王朝在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走向滅亡。襲承秦制的漢王朝,十分迫切的任務就是如何鞏固地主階級的政權,防止農民起義再發生。秦王朝是以法家思想作為指導的,實行的是嚴刑峻法,借暴力鎮壓以維護其統治,而且秦統治者又十分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希圖能永久統治下去。不過,卻並不能如其所願,轉瞬之間,即為農民大起義的怒濤所覆沒。這強烈地震撼了地主階級,從而迫使繼起的西漢王朝的統治者們,不得不從中汲取教訓,結合實際情況制定新的治國理民的統治理論和策略。這樣,漢初的統治者在思想上就推崇以「清靜無為」為特徵,以「無為而治」為原則的黃老思想,並把它作為統治術的指導思想,實行約法禁省、與民休息的「黃老政治」,以此來安定社會秩序。結果使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地恢復和發展,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景象。司馬遷記述說:「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民富國強,說明漢初統治者的治國措施有了一定成效。可是,講清靜無為、倡仁義道德的說教,仍未能阻止封建社會固有矛盾的發展,至漢武帝劉徹繼位後,他雖然憑藉前幾代經營積蓄的雄厚資財,連連發起反擊北方匈奴的侵擾及開拓西南疆域的大規模戰爭,擴大和鞏固了疆界,使秦漢社會空前強盛。但是,在繁榮昌盛的背後,卻又顯現出另一種場景:「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豪富兼併土地,橫行鄉裡,官家「爭於奢泰」,揮霍無度,司馬遷對此敏銳地指出:「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隨著沉重的租賦、徭役,及「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隱伏於繁榮景象之中的深重社會危機便逐漸顯露出來。
自漢初以來一直在發展著的土地兼併之風,造成大量無地的赤貧農民,加之頻頻發生而無法克服的水旱等自然災害,使得人民的生活日益貧困,流離失所,迫使他們「轉為盜賊」,「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獄以千萬數」。社會矛盾日漸加劇,整個社會都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到漢武帝晚年,已是「郡國盜賊群起」。這種情況,僅據《史記•酷吏列傳》載:「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裡者,不可勝數也。」《史記》,最後,一場醞釀已久的農民大起義終於爆發。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西漢王朝也由盛而衰,步秦王朝之後塵,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西漢滅亡後,光武帝劉秀號稱中興,建立了東漢政權。劉秀實際上是利用農民起義的成果而登上皇帝寶座的,他還在戰爭期間就採取了一些措施以圖緩解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但東漢王朝是建立在農民起義的火山之上的,政治基礎極其脆弱,只有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代,皇權比較穩固。從和帝劉肇開始,豪強地主勢力便迅速膨脹,政治上逐漸形成外戚與宦官兩大集團,彼此間激烈爭奪政治權力,把持朝政,使本來就不穩定的東漢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朽黑暗,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莫大的痛苦。在外戚、宦官兩大集團激烈爭奪政權的過程中,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之風也愈演愈烈,一方面土地和社會財富高度集中,以致「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後漢書》。另一方面,廣大農民喪失土地,一部分淪為依附于豪強地主的佃農或雇傭,受著極其殘酷的剝削,而更多地則變成無家可歸、輾轉道路的流民,處境尤其悲慘。在安帝、順帝之後,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勢力更是惡性發展,統治階級內部兩大集團之間的權力爭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同時,地方官吏亦「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潛夫論箋》,致使吏治愈益腐敗,搜刮更為猖獗,人民無法生活,被迫起為「盜賊」。而在官軍對這些所謂盜賊進行圍剿時,竟出現了「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見)[視]分裂」等慘絕人寰的駭人景象。加之當時頻頻發生的自然災害、疫病流行,以致「死者相枕于路」、「民相食」,廣大人民深陷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他們在渴望擺脫苦難,獲取幸福,而又找不到行之有效的出路之時,就常常幻想能有一種超於人間之上的力量來替他們伸張正義,從而使自己獲得拯救,使不幸的處境能夠得到改善,這個超人間的力量就是人們想像中的神靈。換句話說,人們是把希望寄託在神靈身上,祈求神靈的庇佑。仲長統在其著述《昌言》中說「農桑失所,兆民呼嗟於昊天」,正是對這種祈求的最好寫照。
綜上所述,就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有接受宗教影響的內在條件。此外,就統治階級而言,在嚴重的社會危機、統治危機面前,他們也竭力想利用宗教來消弭隨時可能發生和已經發生的反抗鬥爭。同時,也希望利用宗教來為他們的統治祈求長治久安和個人的延年益壽,在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中「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一句話,深重的社會危機使得宗教成為了社會的需要,道教就是在這種社會危機的催化下應運而生的。
第二, 漢代統治思想的宗教化。
秦王朝的覆滅,表明了單靠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是不能使社會矛盾得到解決而達到國治民安的;而漢初所奉行的具有兼采各家思想特點的黃老之術,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使社會矛盾有所緩和,但也未能使矛盾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和防止封建社會固有矛盾的發展。所以,到漢武帝時,又面臨「盜賊群起」,農民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不可勝記」的嚴重局面。為了在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中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統治者借鑒歷史上「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徐子宏:《周易全譯》的治民經驗,企圖借鬼神的威力來加強「文武並用」的「長久之術」,使黎民百姓成為俯首貼耳的順民。《淮南子》就明確提出:「因鬼神祥,而為之立禁。」漢武帝更是身體力行,「尤敬鬼神之祀」,並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祀神求仙活動。當時的思想家董仲舒的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宗天神學理論亦應運而生,得到統治者的賞識,並被加以提倡,從而成為統治人民的重要思想工具。
董仲舒,生於漢文帝元年(前179),卒于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廣川(今河北棗強廣川鎮)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而著名,是西漢主要唯心主義哲學家。漢武帝即位後,在建元元年(前140)下詔郡國諸侯推選賢良博士,回答「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的問題。董仲舒連立三論,得到武帝重視,「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董仲舒的著述,現存的主要有《舉賢良對策》三篇、《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他的主要思想觀點,是援引陰陽五行學說來重新解釋儒家傳統經典,用「天人感應」的思想和「天人比附」的手法,將造成人類自身、君主地位、三綱五常、主德輔刑事、災異得失等原因都歸結於至高無上的「天帝」或「天命」,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相提並論、混為一談,建立起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體系。在他的這個神學體系中,最富宗教色彩的乃是天人感應論、善惡報應說,以及祈求「昊天」降雨、止雨的法術和儀式。
首先,董仲舒賦予「天」以政治的、道德的屬性,將自然之天人格化,把天說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夠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無與倫比的權威,是「百神之大君」,無論自然界日月星辰的運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還是人類社會的治亂興衰、個人的死生禍福,都是由這個「大君」的意志所決定的。他說:「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複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又說:「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類天也。」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人的形體構造、精神面貌、思想感情、道德品質等等,都是「天」按照自己的特點塑造出來的,即他所謂的「人副天數」。人被創造出來,就是為了體現天的意志。總之,通過一系列的牽強附會,董仲舒得出了「天人一也」的結論,「天」與人之間有一種相互感應的關係,體現為「天」對人有著決定作用,同時人的行為又可影響天。這就是他的「天人感應論」,直接為其「君權神授」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董仲舒認為,君主是受命于天的,他說:「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為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這樣,人類社會國家政權的建立就不是人所為,乃是由「天」賜予的。而受命于天的君主,能夠體察和代天行使「天意」,他說「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帝王是「承天意以從事」。天是仁善慈愛的,當帝王的行為體現了天的意志,積善累德,天就會降符瑞任命他、嘉獎他,讓其長久統治下去。他說:「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複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反之,當統治者的行為違反了天的意志,有了過失,天就會降下災異以示警告,讓其改過,如果屢告不改,就會受到天的懲罰,取消其統治權力。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董仲舒認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總之,董仲舒是把《春秋》中記載的大量自然現象、神話傳說都加以神秘主義的解釋而附會到社會人事之上。這種以「天人感應」為理論基礎的「災異譴告」說,實際上是一種善惡報應思想的反映,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它既為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為宗教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董仲舒之後,言災異者大有人在,諸如夏侯始昌、睦弘、夏侯勝、李尋等。這種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的思想,一直貫穿于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漢王朝的政治生活中起著支配作用。如:漢明帝即因日食而下詔罪責自己,認為日食的出現是「無有善政」的緣故,要求「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漢章帝因日食而下詔,稱「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責令「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漢和帝因日食而「引見公卿問得失,令將、大夫、禦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又因京師出現蝗災,詔令:「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漢安帝亦因日食「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當京師等地出現大風大水、雨雹成災時,下詔要求博選人才,廣開言路,「冀獲嘉謀,以承天誡」。有關這一類的記載,不絕於漢代史書。
董仲舒不僅是一個宣揚「天人感應」、陰陽災異譴告說的宗天神學家,而且還是神仙方術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中,除以神秘的陰陽五行學說附會儒家經典,還創造了一套求雨、止雨的儀式。據記載,他本人還親自登壇祈禱作法,弄神作怪,使人分辨不出他到底是儒生還是巫師、方士。章太炎先生曾對此說:「及燕齊怪迂之士興於東海,說經者多以巫道相糅。故《洪範》舊志之一耳,猶相與抵掌樹頰,文為抽繹。伏生開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時適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以推驗火災,救旱止雨與之較勝。以經典為巫師豫記之流,而更曲傳《春秋》,雲為漢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棼政紀;昏主不達,以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屍解之倫。讖緯蜂起,怪說布彰,……則仲舒為之前導也。……夫仲舒之托於孔子,猶宮崇、張道陵之托於老聃。」說明在漢代儒學已經宗教化,儒生與方士開始合流。
以董仲舒把《春秋》學說與陰陽五行家的陰陽五德終始說的神學觀念相結合,將大量天象變化和超自然現象加以全面的歪曲和神秘化為前導,在漢王朝的支持下,混合封建宗教神學和庸俗經學而成的讖緯之學漸漸興起,逐步成為兩漢之際宗教神學思想的主導。所謂「讖」,是假託神意製造的一種預言,即「詭為隱語,預決吉凶」,源出於巫師和方士,由來已久。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所載秦朝流行的「亡秦者胡也」,即是這樣的預言。「緯」是以神意來對儒家經典進行闡釋,把儒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宗教化,將孔子神化為超人的教主、神人。如《孝經鉤命訣》就把孔子描繪成海口、牛唇、虎掌、龜脊、輔喉、駢齒;《春秋演孔圖》則說,孔子的頭像尼丘山,長有十尺,大有九圍。總之,通過種種誇張,把孔子描繪成是一個不同凡人的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評價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讖合而為一。」即是說,原本不同於「讖」的「緯」,在以後的發展中,變得愈來愈荒誕怪異,與「讖」相融。
雖說「讖」與「緯」在形式上是有區別的,但就其宗教神秘主義的實質而言,則完全一樣。「讖緯」所反映的宗教神學思想是多方面的,諸如天人感應、星象預示吉凶、善惡報應、巫術、呼神劾鬼、仙山聖地、仙人神人、經籍圖籙等等。西漢末年,這種讖緯之學極為盛行,後來的漢光武帝劉秀就依靠這種讖緯之學而起家,並奪得統治權。《後漢書•光武帝紀》說:「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複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裡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眾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光武帝即位後,對讖緯之學大加提倡,據《隋書•經籍志》稱:「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自劉秀依靠圖讖建立起了東漢王朝後,東漢的統治者們都把它作為官方之學而盡力使其完善,以便更符合自己統治的需要。建初四年,在漢章帝的主持下,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經學討論會。會議記錄由班固進行整理,編輯為《白虎通德論》,以法令的形式使讖緯之學定型化,緯書被提到與正統經學具有同等權威的地位。《白虎通德論》實際上成為一部官方神學法典,整個社會都籠罩在濃厚的宗教神秘主義氣氛之下。
固然,讖緯之學給傳統儒學染上了濃厚的宗教神學色彩,儒家之祖孔子也被賦予教主的神光,有利於統治者維護其權力。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讖緯之學並不能化解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它不僅遭到古文經學派的反對,在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副作用,各種政治勢力都可以按各自的需要來利用它。自光武帝到獻帝,社會上利用讖緯符命起事者一直絡繹不絕,經過漢章帝欽定的讖緯之學並未能成為行之有效的治國之術,儒學轉化為宗教的希望破滅,但當時社會的宗教神學氛圍,卻為道教的孕育提供了合適的土壤和條件。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道教史 上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42 |
道教總論 |
$ 476 |
宗教命理 |
$ 493 |
道教 |
$ 493 |
道教 |
$ 504 |
宗教類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道教史 上卷
道教是以「道」為最高信仰的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宗教。它是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上,沿襲方仙道、黃老道的某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而於東漢中後期逐漸形成,相信人經過一定修煉有可能長生不死,成為神仙。將老子及其《道德經》加以宗教化,稱老子為教主,尊為神明;奉《道德經》為主要經典,並對它做了宗教性的闡釋。
研究道教思想史有助於深入認識道教文化的歷史價值與社會作用,了解我國傳統文化的構成因素及其相互關係。
【本書特色】
簡單扼要、通俗易懂的道教通史性著作,提供全面又有系統的道教文化知識,且滿足廣大的道教文化愛好者迫切需求!
《道教史》是一部道教通史,以時間為經,以教派分化為緯,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道教產生、發展和流傳的歷史。
全書所記時限始於道教產生前的秦漢社會狀況和思想淵源,止於當代道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所記內容涉及道教及各支派的經籍、教義、人物、教制、教職等等,同時兼及道教的節日、禮俗、聖地、遺跡、建築、文學、藝術等等。在對道教作全面考察的同時,書中還對道教與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的關係,作了深刻的分析,對一些重要史事和學術問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
作者簡介:
卿希泰
教授。四川三台人,1951年畢業于四川大學法律系。1954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歷任四川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哲學系副主任、教學研究所所長、專于道教史,對道教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國道教思想史綱》(第一、二卷),主編《中國道教史》。
唐大潮
湖南澧縣人,生於1956年7月,1982年於四川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1988年於四川大學獲哲學宗教學碩士學位,1994年於四川大學獲哲學宗教學博士學位。現為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哲學、宗教學、中國道教的教學及科學研究工作。
TOP
章節試閱
序
引言
在中國歷史上,「道教」一詞曾被賦予過廣泛的含義。它最初的意思是指以「道」來教化眾生的各種理論學說和實踐方法,諸子百家都曾以「道」來稱呼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儒家、墨家、道家、陰陽家以及佛教等,都曾自命或被認作是「道教」,但這種意義上的「道教」顯然不是我們要談的。
我們所說的「道教」,是指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上,沿襲方仙道、黃老道的某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漸形成,以「道」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過某種實踐經過一定修煉有可能長生不死、成為神仙的中國本民族的傳統宗教。它尊老子為教主,奉老子的著...
引言
在中國歷史上,「道教」一詞曾被賦予過廣泛的含義。它最初的意思是指以「道」來教化眾生的各種理論學說和實踐方法,諸子百家都曾以「道」來稱呼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儒家、墨家、道家、陰陽家以及佛教等,都曾自命或被認作是「道教」,但這種意義上的「道教」顯然不是我們要談的。
我們所說的「道教」,是指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礎上,沿襲方仙道、黃老道的某些宗教觀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漸形成,以「道」為最高信仰,相信人通過某種實踐經過一定修煉有可能長生不死、成為神仙的中國本民族的傳統宗教。它尊老子為教主,奉老子的著...
»看全部
TOP
目錄
引言
作者的話
第一章 道教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
第一節 秦漢社會危機與統治思想宗教化
第二節 各種思潮的湧出與融攝
第二章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
第一節 民間興起的漢代道教
第二節 魏晉道教的分化和發展
第三節 南北朝道教的改造和充實
第三章 隋唐五代北宋道教
第一節 隋代道教的轉折
第二節 盛唐道教的鼎興
第三節 中、晚唐及五代十國道教的低落
第四節 北宋道教的高漲
第四章 南宋金代道教
第一節 符篆派統領和金丹派興起
第二節 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的創立
附錄
一 道教大事記
二 主要參...
作者的話
第一章 道教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
第一節 秦漢社會危機與統治思想宗教化
第二節 各種思潮的湧出與融攝
第二章 漢魏兩晉南北朝道教
第一節 民間興起的漢代道教
第二節 魏晉道教的分化和發展
第三節 南北朝道教的改造和充實
第三章 隋唐五代北宋道教
第一節 隋代道教的轉折
第二節 盛唐道教的鼎興
第三節 中、晚唐及五代十國道教的低落
第四節 北宋道教的高漲
第四章 南宋金代道教
第一節 符篆派統領和金丹派興起
第二節 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三大道派的創立
附錄
一 道教大事記
二 主要參...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卿希泰、唐大潮
- 出版社: 龍圖騰文化 出版日期:2018-09-05 ISBN/ISSN:978986388068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32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道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