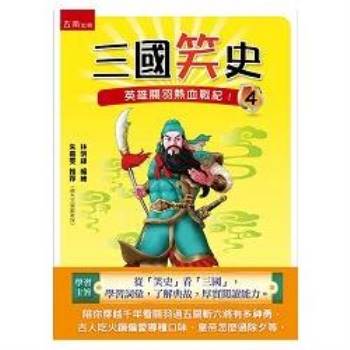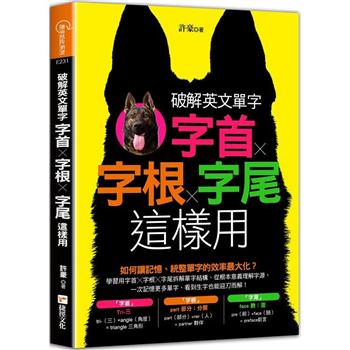本書充分參考近代以來新發現的敦煌文獻等禪宗史料,從佛教中國化的角度,對中國禪宗思想之源、東土五祖禪法之展開、禪宗的創立與南北禪宗之分化、六祖惠能的禪學思想特色、五家七宗之禪,以及禪宗與中國哲學的關係等,都做了深入細緻的辨析與探討,特別是對惠能禪宗以空融有、空有相攝的禪學心論以及在佛教基點上的三教合一,提出了獨特的見解。是研究中國禪宗和禪學思想史的重要參考書。
本書特色
本書繁徵博引,對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作了條分縷析的深刻闡述,論證充分、可靠。它的重要特點之一是視野開闊、視角新穎。作者堅持歷史的與邏輯的辯證統一,從外來佛教與傳統哲學文化的相互關係中探討佛教的中國化過程,並從佛教中國化這個大背景下來考察禪宗的形成與分化發展。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70 |
二手中文書 |
$ 474 |
中國哲學總論 |
$ 510 |
宗教命理 |
$ 528 |
中國哲學 |
$ 528 |
中國哲學 |
$ 540 |
宗教類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洪修平
一九五四年生,江蘇蘇州人。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年就讀於南京大學哲學系,先後獲學士和碩士學位。一九八八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赴美國作訪問學者一年。現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西北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兩百部)副主編等。專著有《中國禪學思想史綱》、《中國佛教文化歷程》、《肇論注譯》;合著有《十大名僧》、《禪學與玄學》、《如來禪》和《惠能評傳》,並參著《中國宗教史》等;譯著有《禪宗與精神分析》。
洪修平
一九五四年生,江蘇蘇州人。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四年就讀於南京大學哲學系,先後獲學士和碩士學位。一九八八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赴美國作訪問學者一年。現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中國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西北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宗教學會理事、《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兩百部)副主編等。專著有《中國禪學思想史綱》、《中國佛教文化歷程》、《肇論注譯》;合著有《十大名僧》、《禪學與玄學》、《如來禪》和《惠能評傳》,並參著《中國宗教史》等;譯著有《禪宗與精神分析》。
目錄
序 任繼愈
序 嚴北溟
緒論
第一章 人心與止觀:禪宗思想溯源
第一節 早期禪學概觀
第二節 般若與禪觀
第三節 人心、佛性與解脫
第二章 心境與心性:達摩禪之展開
第一節 藉教悟宗與安心符道
第二節 身佛不二與息妄顯真、任性逍遙
第三節 隨心自在、無礙縱橫
第四節 東山法門與禪宗初創
第三章 無心與觀心:南能北秀之分化
第一節 心境本寂、絕觀忘守
第二節 南北禪宗對立之形成
第三節 觀心看淨、方便通經
第四章 佛性與實相:曹溪的頓悟禪(上)
第一節 惠能與《壇經》
第二節 以空融有、空有相攝
第五章 識心與見性:曹溪的頓悟禪(下)
第一節 即心即佛、自在解脫
第二節 識心見性、頓悟成佛
第六章 超佛與越祖:南宗禪的繁盛
第一節 超佛任運與無心自然
第二節 越祖分燈與五家宗風
第三節 楊岐黃龍與宋代禪學
第七章 禪宗與中國哲學
第一節 三教合一與農禪並作
第二節 傳統哲學發展的環節
附錄
一主要閱讀書目
二主要參考書目
三人名索引
四名詞索引
後記
修訂後記
序 嚴北溟
緒論
第一章 人心與止觀:禪宗思想溯源
第一節 早期禪學概觀
第二節 般若與禪觀
第三節 人心、佛性與解脫
第二章 心境與心性:達摩禪之展開
第一節 藉教悟宗與安心符道
第二節 身佛不二與息妄顯真、任性逍遙
第三節 隨心自在、無礙縱橫
第四節 東山法門與禪宗初創
第三章 無心與觀心:南能北秀之分化
第一節 心境本寂、絕觀忘守
第二節 南北禪宗對立之形成
第三節 觀心看淨、方便通經
第四章 佛性與實相:曹溪的頓悟禪(上)
第一節 惠能與《壇經》
第二節 以空融有、空有相攝
第五章 識心與見性:曹溪的頓悟禪(下)
第一節 即心即佛、自在解脫
第二節 識心見性、頓悟成佛
第六章 超佛與越祖:南宗禪的繁盛
第一節 超佛任運與無心自然
第二節 越祖分燈與五家宗風
第三節 楊岐黃龍與宋代禪學
第七章 禪宗與中國哲學
第一節 三教合一與農禪並作
第二節 傳統哲學發展的環節
附錄
一主要閱讀書目
二主要參考書目
三人名索引
四名詞索引
後記
修訂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