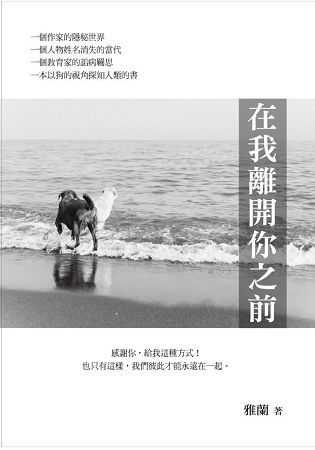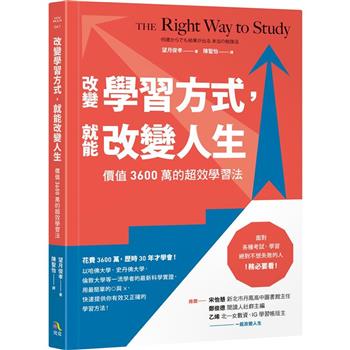1.在大自然面前,你和我都是樹葉,是兩片不同的樹葉
開始,你聽說我自己出去沒回來,你沒怎麼當回事,甚至你還用調侃的口吻,說我是不是看上誰家小妞了。第二天,你聽著同樣的話,起初你也還是沒在意,你只隨意地笑了一下,但笑容並沒有向下延伸,就像盛開的花朵,突然被投放在冰冷的器具裡,你的笑容瞬間凝固了起來。你意識到出了問題,而且問題很嚴重。
與你在一起十五年,你太過熟悉於我,如果是我自己出去,我一定是能回來的,哪怕是路途再遙遠。你神情凝重地去問阿姨,到底怎麼回事?阿姨吞吞吐吐的,似乎說話有點隱藏,你緊追不放,繼續問阿姨,我是在什麼時間出去的?多長時間才發覺我沒回來?儘管阿姨語塞,但迫於壓力,還是不得不完整地將情況說了出來。
那些天,阿姨都會趁你不在家時,去大潤洋超市後面,幾天前有一幫外地人租了那裡場地,專門賣各種養身保健品,雖然你曾經也提醒過,那些都是唬弄人的,但阿姨還是喜歡往那裡跑,如果不是我不回家,你還以為阿姨與那超市沒啥關係。沒等阿姨說完,你轉身就走。從我的角度來說,你轉身,是急於尋找我,從你的角度來說,你根本不想聽阿姨再為自己辯白或推卸責任。阿姨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出門後,你騎上自行車,繞過社區,飛快地騎向地鐵口,沿途路旁及綠化叢的縫隙處,你絲毫都沒放過。你一路騎車,一路喊著我的名字。地鐵口,是我經常送你的地方,當那些跳著廣場舞的大媽們聽到你的叫喊聲時,她們當中有的人在納悶,誰家丟了孩子?看這媽媽急的真讓人心疼。
找了近一個小時,你推著自行車回家了。回到家,你顧不上喝水以及上廁所,你以最快的速度拿起手機,打開微信,你想將我丟失的資訊傳播出去,你是多麼希望能找到我啊!文字,對於你來說沒有任何阻礙,要找到我,最好還要有照片,哪怕一張也行。
在這個速食時代,已經沒有多少人能靜下心來閱讀文字了,這一點,你比誰都清楚,所以你急於需要找到我的照片。平常你用的手機裡沒有我的照片,你只得在另一個手機的相冊裡努力地翻找,所有的照片都翻過了,只有兩張我吃西瓜的照片,那是夏天時,你為我拍的。那天很熱,整個天地都像悶在一個大蒸籠裡,你從外面回來後,就在廚房裡剖了西瓜,第一片,你是拿給我的,看著我很快吃完了,你又給了我第二片。就在我津津有味地吃西瓜時,你悄悄地從我的脊樑上方為我拍了照片。一連幾張照片,雖然不是正臉,但在沒有任何照片的情況下,也只能利用它了。
確定我丟失的當晚,你徹夜無眠,你的頭腦裡都在設想能找到我的種種可能性,找不到我是你最不願意去面對的,但你仍然還為自己保持一點理性,就那麼零星丁點的,你也要往最壞處去考慮,萬一真的找不到我了,你的內心深處還能有接受和支撐。
是的,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任何絕對的。要麼找到我,要麼找不到我,兩種境地都會有結果。如果一個星期找不到,希望就很渺茫了,相反,則是能找到,說不定兩三天就能找到。你但願是這樣。
第二天的凌晨,窗內的物件能看見輪廓時,你就起床了。你只喝了一杯水就出門了。
社區的後面有一條大路,與地鐵相反方向,那裡過了紅綠燈,能到達大潤洋超市。你猜測,我應該是在那裡丟失的。紅綠燈右邊有一個社區,社區裡的樓房不高,假六層真七層,最底層是車庫。每幢樓都呈現長方形,長的部分非常長,長的誇張,若不是找我,你是根本不會到那裡的。
在樓體狹窄的側面,是車庫的入口處,從一頭望向另一頭,裡面黑漆漆的,猶如被惡魔掌控在手中。光影從另一頭打過來,冒著寒顫顫的光,你是為了找我,才用相聚時的喜悅沖散了心頭的膽怯,說不定,我就在裡面。之所以你這樣想,是因為昨晚你在網上搜了很多跟我類似的文字,其中一頁的內容就跟你現在的情形差不多,說在陰暗無人的地方或許能找到丟失的小狗。
你想,是否我如文字裡寫的一樣,也是膽小,不敢出來,你必須喊著我的名字,還要大聲地喊,你得讓我聽到,得讓我感受到你的焦慮、你的渴盼、你的熱切,你對我急迫的不可無一日的重新擁有,你是這般的,我就一定會出來,會像一根離弦的箭一樣,從深重陰滯的光影裡飛射出來,你是我的目標,我是奔向你而來的,除了你,任何人任何聲音都無法召喚我。於是,你的聲音比昨晚還大,你讓十一月的風帶上我的名字,從車庫入口的一頭穿透到另一頭。
每喊一聲,你的腦海裡都會浮現我衝出來的情景;這一聲結束,下一聲緊跟而上,你就擔心我聽不到似的。這一頭往另一頭喊,喊了約有十分鐘,不見我的蹤影,你不妥協這無聲的黑暗。
你到了另一頭,有可能我靠近另一頭的某間車庫,而這間車庫又是不能順風聽清任何聲響,哪怕還有一絲的希望,你都在嘗試。
你小小的身影站在車庫的另一頭,這時你的聲音嘶啞了,但你仍然在大聲喊著的名字,喊了兩聲後,陰暗的通道裡有了聲響,那個聲音不是我發出的。聲音是從通道中間發出的,聲音傳出的位置你能確定,但你卻不能辨別那是什麼聲音,你多麼希望那是我的聲音,我就在通道中間的某個車庫裡。
你疲憊的目光投在聲音傳出的地方,通道裡,依然是伸手不見五指。
你佇立著,儲存在腦海裡的各種可能性依稀再次浮現,每出現一次,都能給你增加一份追索和探究的力量。然後,你蹲了下去。低傾著頭,你心裡想,也許這樣能有新的發現。
事實如你所料,在通道中間,也就是發出聲音地方的正前方,有一攤明亮的不成形的光澤,雖然你有淺微的懼怕,但你還是決定往那個明亮的地方邁開腳步。我知道,你的絲毫不放棄都是因為我。
你剛走幾步,吱呀一聲清冷地滑過通道,你聽到了,不由得停住腳步,一股涼氣從腳底順著脊樑迅速往上衝,你的手心也涼了起來。你打了哆嗦。你在猶豫,是否還要往前走?如果你的周遭都是風平浪靜,無論如何你都是不可能再往前走一步的,可你現在是為了我!你仍然選擇著前行。
你冰涼的腳謹慎地走在通道裡,為了壯膽,你不時地喊著我的名字。在你還沒走到那個光澤的地方,有個蒼老渾濁的聲音,從之前發出聲響的地方傳了出來,這是一個老婦人的聲音。
她在問你,找誰?
一個活生生的人突然出現你面前,使你手足無措。你有了慌亂,但很快,你調整了過來。
你問她,你住在這裡嗎?她回答道,是呀?她的回答讓你覺得不可思議。這麼雜亂陰暗、不見天日的地方,怎麼能住人?而且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
她住的地方有十幾平米,典型的車庫結構,就像超大型的火柴盒子,堅固而穩妥地躺在黑暗的世界裡。一束光從車庫的上方不情願地向四周瀰散著,慵慵懶懶的,就跟她的被時光剝離了的面容似的,讓人提不起一點精氣。
你在此的目的是為了找我,因為詫異,你還是對她開了口。你問她,為什麼住在這裡?你的兒女呢?她跟你說,她沒有女兒,她的兒子住在樓上,她老了,腿腳不好,爬不了樓,她只能住在那裡。
你的目光將車庫裡的擺設掃括了一遍。你問她,沒有衛生間,洗澡解手的話,你怎麼辦?她沒回答你的問題。她倒過來問你,你找什麼人?這裡,一般沒有人來。
她這樣,讓你更心酸。酸的你要掉下眼淚。
在你找我之前,你的心頭偶爾掠過你最不願意面對的情景,那就是如何與我道別,是那種真正意義上的道別,也就是生離死別。我知道,我活不過你,所以,我將你生命中的一年光景,當成我生命中的八年。我不忍心目睹你的年華漸失,但也不得不殘忍地,讓你看著我日復一日地蒼老而去。
你和我,終有一個先行老去。生命都會這樣,猶如樹上的樹葉,無論陽光和土地如何供養,到了秋冬,必有垂落。在大自然面前,你和我都是樹葉,是兩片不同的樹葉。
你是很少看電視的人,碰巧看到電視上播放的紀錄片,那次你看的較為用心。紀錄片的製片人是外國人,內容講述一個行動不便的人與一隻服務犬。
服務犬的前半生在照料行動不便的人,服務犬的後半生由行動不便的人照料著,尤其是紀錄片後面的內容,你都是在淚眼中看完的。你一邊看,一邊在想著我。
服務犬老了,得了關節炎,視力也不如從前,上下顎的牙齒也脫落了幾顆,稍微硬的食物,服務犬都吃不下,行動不便的人就用攪拌機攪碎各種食物,加熱後再給服務犬食用。服務犬知道自己給行動不便的人增添了麻煩,白天,服務犬幾乎都是爬在地上不動,到了要吃食物和大小便時,服務犬才顫顫巍巍地挪動身子,行動不便的人滿面都是淚水,他深知服務犬不想連累自己。
行動不便者專門聯繫了動物心理學家,也就是所謂的動物通靈師。據說通靈師能聽懂所有臨終動物的語言,因為行動不便的人與服務犬之間,無法架通語言的交流,只能求助於通靈師。
通靈師單獨與服務犬在一個房間,房間裡到處都是白顏色,只有服務犬和通靈師的身上有著其他色系。一塊厚重的毛毯鋪在房間的正中央,風,穿過樹林,將窗簾吹颳的肆意翻捲,就跟白色的巨浪一樣,要將整個房間連同服務犬和通靈師都要吞噬似的,勢頭銳可不擋。
服務犬彎曲著脖子趴在地毯上,通靈師盤腿坐在服務犬的對面,相互之間沒有聲響,他們的語言都是無聲的。他們用眼睛在對視彼此。他們看待對方時間的長短,眼皮如何眨的,眼睛睜的大小等,這些都是他們在交流的方式。
通靈師將服務犬需要傳遞的資訊收集起來,每隔一段時間,通靈師都要走向另一個房間,那裡的輪椅上坐著行動不便的人。
一開始,行動不便的人接受通靈師的傳話後,還能冷靜地將自己要說的話託付給通靈師,以便通靈師再翻譯給服務犬。來回走的次數多了,通靈師轉過來的話讓行動不便的人泣不成聲,原來服務犬心裡最大的擔憂是行動不便的人。
服務犬讓通靈師告訴主人,與主人相處十三年了,過去有它的陪伴,主人才能安然度日,如果它不在了,它最放不下的就是主人了。主人穿衣刷牙洗臉做飯出門去醫院等等,誰能如它一樣,對待主人無微不至。
行動不便的人聽到這裡,掙扎從輪椅上站起。嗵得一下,行動不便的人跌倒了,他連滾帶爬朝服務犬匍匐而去。通靈師的眼圈也紅了。由於動作慌亂,行動不便的人舉措聲音較大,服務犬伸直了脖子,努力抬起頭,眼簾抬得也比以往高了。
服務犬的眼睛晶亮著,從它瞳孔的反射中,能看出行動不便的人離它越來越近。服務犬也試圖站起來迎接主人,無奈,它的腫大的關節不聽它的思維使喚,它只能對著房頂搖晃自己的尾巴。
當它與主人抱作一團時,它都不知道自己即將徹底離開這個世界。它的主人,行動不便的人已經為它安排了安樂死,執行的時間是在一個小時後。
看過這場訣別的那幾天,你的心情都是不好的,可能是因為服務犬而聯想到我。
你就是這般心底柔軟的人。通道裡的風比之前更大了,你將領口的拉鍊往上拉了一下,你沒有立刻離去的意思。你伸開臂膀,左手在右手比擬著長短。
你問老婦人,請問這幾天,你有沒有看見過這麼大的一隻狗,不大,只有半條手臂長,棕色的,它的前胸和兩個前爪是白色的,還有它的嘴邊也是白色。為了加深印象,你又補上一句,它的牙也掉了幾顆。
老婦人弓著背,從車庫裡面跺挪著碎步,她認真地對你說,這裡沒有狗來,這幾天都沒有狗。她的態度就跟學生回答老師問題一樣。
超大型的火柴盒子裡,沒有我的任何音訊,那次,你帶著失望。推著自行車上了寬闊的馬路。你去往其他地方,只要是你能想到我會去的地方,你都去了。這個火柴盒子,在幾天後,你又再次風塵僕僕地騎著自行車朝它而來。
附近的幾個工地,周圍社區,你都來回騎了一圈又一圈,白天黑夜的,其中兩天還下著小雨。你就任著小雨打濕你的頭髮和衣服,你沒有打傘和穿雨衣,與我相比,我是大於一切的。
你的信念就是要找到我,你不能去想我挨餓的樣子、我口渴的樣子,被雨淋濕的夜晚,我又睡在哪裡呢?想多了,你的眼睛就跟天空一樣會潮濕,你的心裡就會有揪心的痛。
在我離開你之前,我身上的毛沒有以前濃密了,背部鬆舒的毛體間夾雜著些許白毛,那裡,曾經都是棕色的,躺在陽光下,就像背部長著一根根閃亮的棕針。
記得你還笑著對我說過,你長這麼帥幹什麼呀?可不能隨隨便便喜歡什麼小狗。你一直將我與社區裡的其他同類分開,特別是異性,你儘量減少我與它們接觸的機會,你認為它們都配不上我。
被你寵了十幾年,多少我也有了傲肆,這份性情只能用在對付外面的同類,對於你,我是超級親近溫和的。
剛到你身邊,我的膽子還是小的,逐漸地,我就放開爪子到處竄謀了。
我不僅跳到沙發上,還會在你睡著時,鑽進你的被子裡,然後將身體縮成圓圈,蜷在你腳下。有時趁你不注意,我會叼起你的拖鞋,藏到沙發下,被你找到後,我還會將拖鞋藏到床肚下。
那個淡紫色的枕套和被套,它們的角都是被我咬爛的。
你晚上睡覺時,發現枕套的角有不規則的齒印,還有稀稀拉拉的缺口,你就喊我趕快過來。喊了幾聲,我都沒過去。其實我都聽到了,是我不敢過去。你躺下去的時候,發現被角跟枕套一樣,你就又喊了我。同樣,你沒有喊到我。
那以後,我乖了幾天。你待我,就像待孩子一樣。
還記得剛到你身邊不久,我病了。我不吃不喝,肚子憋得像一個空口袋。我的嘴裡還往外面吐著黃綠色的水,你嚇的不敢靠近我。吐了後,我的腿抽搐了起來。我用哀憐的眼睛望著你,你沒有辦法抱起我,髒是一個原因,主要是你無從下手,不知該如何對待我。
你在院子旁邊的小樹上折斷了一根小樹枝,你右手拿著它,在我吐的水漬上划動了幾下。僅是幾下,你丟下了它,因為你看到了幾條如絲般的紅色蟲子在游動著。你驚恐把我抱起來,你不顧我那副邋遢糟糕的狼狽樣,你對我說,我帶你去醫院。
你說的醫院在河對岸,你帶我去的那天是一個秋天。
我渾身顫抖著縮在你的臂彎裡,你是怕我冷,出門時,用你的上衣包裹了我。醫生不能馬上為我做診斷,你得等前面人走了,才能抱著我坐在醫生跟前。終於輪到我時,醫生用一根冰涼的器具貼在我的胸前,醫生聽了一會兒,接著用手翻起我的眼皮,與你做了簡短的對話後,醫生建議你放棄我。醫生說,不用治了,治也治不好。
你沒有聽從醫生的話,出了醫院的門,你沒有把我丟在小河邊。過了橋,你抱著我往家的方向走去。回家後,你把我放在沙發上,你進了書房。你打開電腦,在百度裡輸入關鍵字,是跟我症狀相關的。你按下滑鼠,電腦顯示幕上迅速出現幾條類似的頁面。你逐一去閱讀,幾分鐘後,你決定去藥店買藥。你認為,這是救活我的唯一途徑。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在我離開你之前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在我離開你之前
一個作家的隱秘世界 一個人物姓名消失的當代
一個教育家的詬病羈思 一本以狗的視角探知人類的書
感謝你,給我這種方式!也只有這樣,我們彼此才能永遠在一起
《在我離開你之前》,以狗的視角打開人類的世界。(寫作靈感來自於美國著名作家加思‧斯坦的長篇小說《我在雨中等你》)
從尋找出發。字字句句,溢滿深情。
當狗成為了敍述的主角,人類便自覺的往後退卻。(性靈裡的善得到推崇,是一種「在、有」。人性中的惡被隱匿或被消失,是一種「失、無」)。而作者遭遇現實是殘酷的:人,在,有;狗,失,無。
人類退卻,便淡化稱謂。所以,文字裡的人物都沒有姓名。同時也在隱喻人類存在的狀態。
整篇文字在回憶裡進行,逐步遊歷於文學和教育之間。並透過小我的思考,輕叩著當下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著重引發讀者去思考「有與無」。
作者簡介:
雅蘭,著名作家,社會學家,以思想敏銳、文字敏銳、視角獨特著稱,遊離於言論、散文、小說、詩歌等諸多文體,在公開發行的刊物及相關網頁開設各版《雅蘭專欄》。著書《中國很高興》、《性殤》、《從壓抑到氾濫》、《斷裂的後現代》。
TOP
章節試閱
1.在大自然面前,你和我都是樹葉,是兩片不同的樹葉
開始,你聽說我自己出去沒回來,你沒怎麼當回事,甚至你還用調侃的口吻,說我是不是看上誰家小妞了。第二天,你聽著同樣的話,起初你也還是沒在意,你只隨意地笑了一下,但笑容並沒有向下延伸,就像盛開的花朵,突然被投放在冰冷的器具裡,你的笑容瞬間凝固了起來。你意識到出了問題,而且問題很嚴重。
與你在一起十五年,你太過熟悉於我,如果是我自己出去,我一定是能回來的,哪怕是路途再遙遠。你神情凝重地去問阿姨,到底怎麼回事?阿姨吞吞吐吐的,似乎說話有點隱藏,你緊追不放...
開始,你聽說我自己出去沒回來,你沒怎麼當回事,甚至你還用調侃的口吻,說我是不是看上誰家小妞了。第二天,你聽著同樣的話,起初你也還是沒在意,你只隨意地笑了一下,但笑容並沒有向下延伸,就像盛開的花朵,突然被投放在冰冷的器具裡,你的笑容瞬間凝固了起來。你意識到出了問題,而且問題很嚴重。
與你在一起十五年,你太過熟悉於我,如果是我自己出去,我一定是能回來的,哪怕是路途再遙遠。你神情凝重地去問阿姨,到底怎麼回事?阿姨吞吞吐吐的,似乎說話有點隱藏,你緊追不放...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我知道雅蘭是筆名,但我真的不知道她的真名。我從沒有問過她,也沒有問過她的朋友,直到寫這篇代序,想在網上查一下真名,但我沒有查到,只在一個跟帖裡,見讀者稱呼她為「徐家妹子」,如此說來,她姓徐。
我與雅蘭的聯繫,緣起微型小說。因為寫微型小說的緣故,凡見到江蘇發表微型小說、小小說的作家,我就記錄在案。雅蘭一度寫過小小說,就進入了我的視野。怎麼開始聯繫的,我已記不得了。只記得二○ ○五年時,一位四川的作家朋友到南京市溧水縣來掛職縣長助理,我們約好了在南京見面。我就邀請了幾個南京微型小說圈子的朋友,有凌煥新...
我與雅蘭的聯繫,緣起微型小說。因為寫微型小說的緣故,凡見到江蘇發表微型小說、小小說的作家,我就記錄在案。雅蘭一度寫過小小說,就進入了我的視野。怎麼開始聯繫的,我已記不得了。只記得二○ ○五年時,一位四川的作家朋友到南京市溧水縣來掛職縣長助理,我們約好了在南京見面。我就邀請了幾個南京微型小說圈子的朋友,有凌煥新...
»看全部
TOP
目錄
一:在大自然面前,你和我都是樹葉,是兩片不同的樹葉
二:那個夜晚發生的慘烈
三:留檢所裡的殘忍是外人所不知的
四:除了飛機以外,沒有比我更高的了
五:任何一種,都有可能是我最終的遭遇
六:永不停歇,是在證明自己還活著
七:魚貫而入的,都是佇立在文壇上鼎鼎大名的人
八:這是一個誠信嚴重匱乏的社會
九:十幾年,在於人類,是跨過一個時代
十:死,是一種消失,是一種存在後的虛無
十一:換了一種方式,你採用啟迪式思維
十二:你就像從傳說中飄溢出來的
十三:每一種傷情和絕望,都猶如一塊塊青黑的仿古磚
十四:...
二:那個夜晚發生的慘烈
三:留檢所裡的殘忍是外人所不知的
四:除了飛機以外,沒有比我更高的了
五:任何一種,都有可能是我最終的遭遇
六:永不停歇,是在證明自己還活著
七:魚貫而入的,都是佇立在文壇上鼎鼎大名的人
八:這是一個誠信嚴重匱乏的社會
九:十幾年,在於人類,是跨過一個時代
十:死,是一種消失,是一種存在後的虛無
十一:換了一種方式,你採用啟迪式思維
十二:你就像從傳說中飄溢出來的
十三:每一種傷情和絕望,都猶如一塊塊青黑的仿古磚
十四:...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雅蘭
- 出版社: 福隆工作坊(水星文化) 出版日期:2018-08-07 ISBN/ISSN:978986390136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8頁 開數:25開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