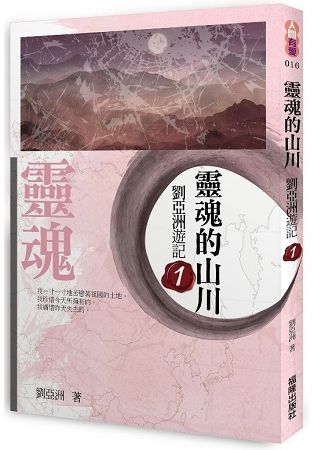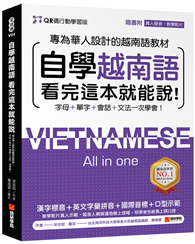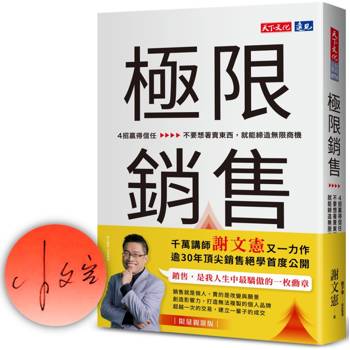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靈魂的山川:劉亞洲遊記 1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8 |
中國政治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政治 |
$ 252 |
政治評論 |
$ 252 |
社會人文 |
$ 252 |
歷史 |
$ 450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靈魂的山川:劉亞洲遊記 1
我一寸一寸地苦戀著祖國的土地。我珍惜今天所擁有的。我痛惜昨天失去的。
這是一篇篇審視歷史後擬就的思辨性、批判性極強的檄文。他不僅將現代史中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作了某些精闢的論斷,而且將各個時期獨領風騷的領軍人物,作了一些新穎的評價。
全篇沒有口號,更無咄咄逼人的語氣,娓娓而談,最後筆鋒一轉,以其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道出今日直奔「深化改革」主題的真諦!
【作者簡介】
劉亞洲
大陸著名作家,一九五二年生於浙江寧波,畢業於武漢大學外語系,曾任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成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空軍紀委書記兼副政治委員,國防大學政治委員,上將軍銜。臺灣曾出版他的《廣場》、《胡耀邦之死》、《六四實錄》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