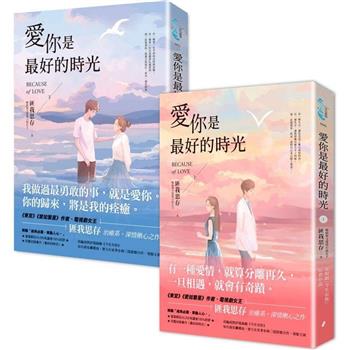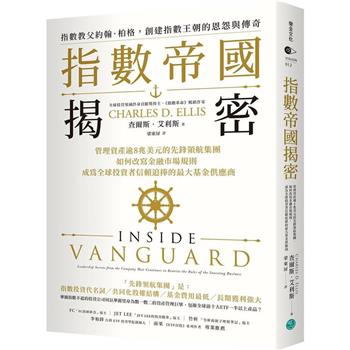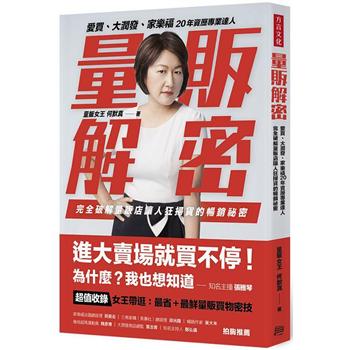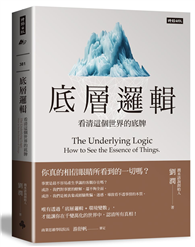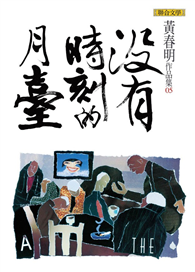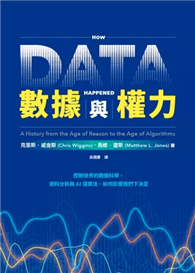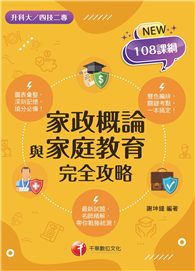★★《金融時報》 最佳10部金融作品之一
★★《財富》雜誌 75本商務必讀書之一
★★《富比士》雜誌 與投資業務相關的最重要著作
★★《財富》雜誌 75本商務必讀書之一
★★《富比士》雜誌 與投資業務相關的最重要著作
只要如此愚蠢的行為可以繼續存在下去,一個真正理性的投資者始終有望利用大眾的瘋狂為自己謀利。具有常識的個體很容易察覺到集體的瘋狂,個體將會藉此獲取巨額的利潤。——查爾斯‧麥凱
◎ 金融投資領域的【超級經典】,全球投資者奉為必讀的「聖經」
在本書中,麥凱第一次運用心理學剖析人們在金融、市場、戰爭、時尚多個領域的群體性行為。
本書出版以後引起巨大轟動,不僅多次再版,
還影響包括伯納德‧巴魯克、約翰‧坦伯頓以及彼得‧伯恩斯坦在內的金融投資界人士。
本書入選《財富》雜誌鼎力推薦的75本商務必讀書,
也被《金融時報》評選為史上最佳10部金融作品之一。
◎ 無刪減收藏版,詳細敘述驚世駭俗的經濟騙局和大眾狂熱
本書不僅是金融投資領域的超級經典,也是對人類社會群體迷失現象的總記錄,
例如:十字軍東征、聖物崇拜、決鬥風潮、女巫、煉金術士等歷史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集體妄想與群眾狂潮在現代也是不斷掀起:
網路泡沫、股市泡沫、金融海嘯,甚至房地產及商品狂潮。
◎ 群體心理學大師古斯塔夫‧勒龐點評,讓我們在群體瘋狂中保持清醒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在古代還是現代,
人們對金錢的追求、對宗教的膜拜、對時尚的尊崇,曾經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狂潮。
很多時候,這種狂熱伴隨著爭鬥、群體性瘋狂、巨大的財富流失,甚至是流血與殺戮。在現在看來,當時人們的這些狂熱行為可能是難以理解和荒唐可笑的,
但是歷史已經向我們證明:如果人們內心的欲望被一些特定的情境激發,
瘋狂仍然會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