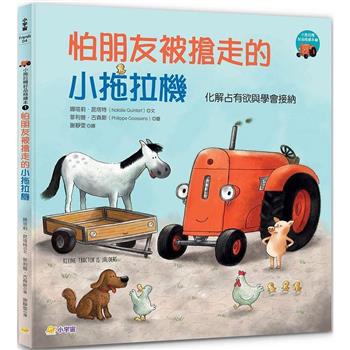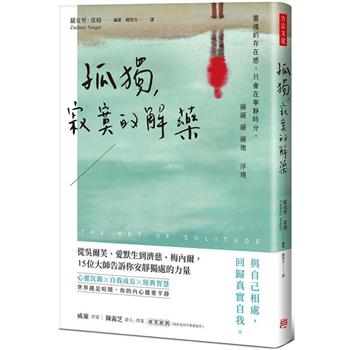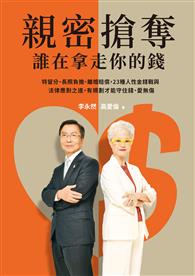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融合、交流和對話之路,近兩千年以來,為人類的共同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絲綢之路見證了西元前2世紀至西元16世紀期間,亞歐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之間的交流,尤其是遊牧與定居文明之間的交流;它在長途貿易推動大型城鎮和城市發展、水利管理系統支撐交通貿易等方面是一個出色的範例;它與張騫出使西域等重大歷史事件直接相關,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等宗教和城市規劃思想等在古代中國和中亞等地區的傳播。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660 |
中文書 |
$ 660 |
中國歷史 |
$ 675 |
中華文化/民族 |
$ 675 |
歷史 |
$ 67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趙豐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研究員,中國紡織品鑒定保護中心主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國際古代紡織品研究中心(CIETA)理事,東華大學(原中國紡織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理工大學(原浙江絲綢工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出版著作有《絲綢藝術史》、《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織繡珍品:《圖說中國絲綢藝術史(中英對照)》、《遼代絲綢(中英對照)》等,主編有《中國絲綢通史》、《紡織品考古新發現》、《敦煌絲綢與絲綢之路》等。
趙豐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研究員,中國紡織品鑒定保護中心主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國際古代紡織品研究中心(CIETA)理事,東華大學(原中國紡織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理工大學(原浙江絲綢工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出版著作有《絲綢藝術史》、《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織繡珍品:《圖說中國絲綢藝術史(中英對照)》、《遼代絲綢(中英對照)》等,主編有《中國絲綢通史》、《紡織品考古新發現》、《敦煌絲綢與絲綢之路》等。
目錄
自序/001
第一章 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中國絲綢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一、絲綢的起源/002
二、早期絲綢的考古學證明/009
三、蠶的一生/014
四、桑林和扶桑/017
五、事鬼神而用之/021
六、絲綢使用的三個階段/024
第二章 翻越阿勒泰:早期的草原絲綢之路
一、東周錦繡/031
二、冰封石塚/035
三、太陽塚及其他/040
四、阿爾泰山南北的紡織品/043
五、草原母題/052
六、歐洲的絲綢傳說/055
第三章 漢錦出陽關:漢晉時期中國絲綢的西傳
一、官營織造/062
二、西漢絲綢的考古發現/064
三、從樓蘭到帕爾米拉/070
四、漢錦的圖案/077
五、五行與五色/086
六、刺繡雙頭鳥/091
第四章 西風遠來:希臘化藝術對紡織品的影響
一、亞歷山大東征/096
二、尼雅出土的蠟染棉布/098
三、緙毛武士的來歷/108
四、錦上天使/112
五、太陽神赫利俄斯/118
第五章 胡錦初成:新疆和費爾幹納的絲織品
一、早期絲綢的傳播/126
二、新疆的綿線織錦/130
三、模仿漢錦和西錦/135
四、長絲類平紋緯錦/137
五、蒙恰特佩出土的絲織品/139
六、絲路上的野蠶絲/144
第六章 尋訪贊丹尼奇:中亞粟特織錦的探討
一、壁畫上的織錦圖案/150
二、贊丹尼奇名物考/154
三、吐魯番和都蘭的中亞織錦/159
四、敦煌藏經洞發現的粟特錦/162
五、尋訪贊丹那村/166
第七章 從何稠到竇師綸:盛唐織錦風格的形成
一、北朝時期的胡風/173
二、何稠生平/180
三、仿波斯的中原織錦/185
四、竇師綸生平/188
五、陵陽公樣/190
六、團窠寶花/195
第八章 大唐新樣:敦煌和法門寺的絲綢
一、唐詩說新樣/199
二、敦煌莫高窟/203
三、敦煌絲織品/208
四、法門寺地宮/214
第九章 長河東到海:中國絲綢向日本的傳播
一、從聖德太子到聖武天皇/221
二、遣隋使和遣唐使/223
三、法隆寺和東大寺/225
四、正倉院寶物/227
五、整理和研究/233
六、風從西方來/234
七、五彩的夾纈/240
第十章 北國風光:契丹、西夏、回鶻之間的絲綢交流
一、北國群雄/245
二、一國兩制/247
三、遼代絲綢考古發現/252
四、遼代絲綢風格/256
五、賀蘭山闕/265
六、西化的回鶻/269
七、最後的於闐/271
第十一章 蒙古與高麗:中國與朝鮮半島的絲綢交流
一、金元與高麗/274
二、《老乞大》和《樸通事》/276
三、高麗佛腹藏/279
四、東方織金系統 /283
五、《出獵圖》中的服裝/286
六、胸背西傳/292
第十二章 金色納石失:蒙元時期中國與波斯織工的交流
一、五大汗國和馬可·波羅/301
二、納石失局/307
三、納石失與織金/310
四、納石失的考古發現/314
五、納石失的圖案/320
六、撒答剌欺/328
第十三章 大洋花:明清之際的東西方絲綢交流
一、傳教士和西洋布/333
二、天鵝絨/339
三、宮中西洋錦/344
四、西方中國風/350
五、中國大洋花/352
第一章 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中國絲綢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
一、絲綢的起源/002
二、早期絲綢的考古學證明/009
三、蠶的一生/014
四、桑林和扶桑/017
五、事鬼神而用之/021
六、絲綢使用的三個階段/024
第二章 翻越阿勒泰:早期的草原絲綢之路
一、東周錦繡/031
二、冰封石塚/035
三、太陽塚及其他/040
四、阿爾泰山南北的紡織品/043
五、草原母題/052
六、歐洲的絲綢傳說/055
第三章 漢錦出陽關:漢晉時期中國絲綢的西傳
一、官營織造/062
二、西漢絲綢的考古發現/064
三、從樓蘭到帕爾米拉/070
四、漢錦的圖案/077
五、五行與五色/086
六、刺繡雙頭鳥/091
第四章 西風遠來:希臘化藝術對紡織品的影響
一、亞歷山大東征/096
二、尼雅出土的蠟染棉布/098
三、緙毛武士的來歷/108
四、錦上天使/112
五、太陽神赫利俄斯/118
第五章 胡錦初成:新疆和費爾幹納的絲織品
一、早期絲綢的傳播/126
二、新疆的綿線織錦/130
三、模仿漢錦和西錦/135
四、長絲類平紋緯錦/137
五、蒙恰特佩出土的絲織品/139
六、絲路上的野蠶絲/144
第六章 尋訪贊丹尼奇:中亞粟特織錦的探討
一、壁畫上的織錦圖案/150
二、贊丹尼奇名物考/154
三、吐魯番和都蘭的中亞織錦/159
四、敦煌藏經洞發現的粟特錦/162
五、尋訪贊丹那村/166
第七章 從何稠到竇師綸:盛唐織錦風格的形成
一、北朝時期的胡風/173
二、何稠生平/180
三、仿波斯的中原織錦/185
四、竇師綸生平/188
五、陵陽公樣/190
六、團窠寶花/195
第八章 大唐新樣:敦煌和法門寺的絲綢
一、唐詩說新樣/199
二、敦煌莫高窟/203
三、敦煌絲織品/208
四、法門寺地宮/214
第九章 長河東到海:中國絲綢向日本的傳播
一、從聖德太子到聖武天皇/221
二、遣隋使和遣唐使/223
三、法隆寺和東大寺/225
四、正倉院寶物/227
五、整理和研究/233
六、風從西方來/234
七、五彩的夾纈/240
第十章 北國風光:契丹、西夏、回鶻之間的絲綢交流
一、北國群雄/245
二、一國兩制/247
三、遼代絲綢考古發現/252
四、遼代絲綢風格/256
五、賀蘭山闕/265
六、西化的回鶻/269
七、最後的於闐/271
第十一章 蒙古與高麗:中國與朝鮮半島的絲綢交流
一、金元與高麗/274
二、《老乞大》和《樸通事》/276
三、高麗佛腹藏/279
四、東方織金系統 /283
五、《出獵圖》中的服裝/286
六、胸背西傳/292
第十二章 金色納石失:蒙元時期中國與波斯織工的交流
一、五大汗國和馬可·波羅/301
二、納石失局/307
三、納石失與織金/310
四、納石失的考古發現/314
五、納石失的圖案/320
六、撒答剌欺/328
第十三章 大洋花:明清之際的東西方絲綢交流
一、傳教士和西洋布/333
二、天鵝絨/339
三、宮中西洋錦/344
四、西方中國風/350
五、中國大洋花/352
序
推薦序
認識趙豐有十多年了,還記得初見時,他三十歲出頭,俊朗颯爽,說話的口氣有點急切,有一種青年學者對學術追求的激動。他說起他的專業中國絲綢史,特別是絲綢之路上出土的古代絲綢,臉上隱隱泛出紅暈,就像沉迷於球賽的球迷,說到自己擁戴的球隊,在上一季的錦標賽中,是如何從後場一個長傳,展開了扣人心弦的攻勢,經過連番閃避,最後是以幾乎不可能的角度射進了球門。他給我的深刻印象,是對學術的熱情與執著,談起絲綢就像說到自己的情人,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光輝。於是,我陸陸續續請他來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前後做了十多場講座,給香港的大學生講解中國絲綢的歷史,敘述中國絲綢是如何作為物質文明的載體,傳佈到世界各地,促進人類文明的進展,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
趙豐從小就接觸到絲綢製造業,父母都是絲綢廠的工人,上大學他主修絲綢工業技術,又轉而研究中國絲綢史,是兼具絲綢工藝專業知識及物質文明史知識的專家。在研究文化史的圈子裡,這種兼通科技工藝與歷史文化的學者,是極為少有的。我還記得,曾參觀他策劃設計的絲綢博物館,他給我講解繅絲、紡絲、織綢的過程,講如何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復原古代織機的構想。他還為我一一解釋綢、緞、錦、綾的細微差別,其關鍵在於絲織工藝的複雜多端的變化。有許多過去從文獻上無法得到確切解釋的絲綢知識,一直令我感到困惑,經他對工藝實物的分析指點,終於撥雲見日,得到明確的理解。我曾請過許多絲綢之路的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如王炳華、樊錦詩、林梅村、榮新江、齊東方等,安排各種關於絲綢之路考古發現及東西文化交流的講座,呈現了這條大漠上駝鈴叮噹的古道,如何經歷著雨雪風沙,聯繫起古代相對隔絕的東方與西方。我請趙豐講絲綢史,更從絲織品的實物以及每件絲綢反映出的工藝來講,讓古代織工的心血與智慧,通過具體的歷史細節,重新浮現在我們眼前,使我們更清楚地理解每一片在沙漠中發現的絲綢,其中承載了多少文明的累積。
趙豐把他在中國文化中心的講稿整理成書,題作《錦程》。該書不僅展示了絲綢之路的錦繡路途,也顯示了學術研究的錦繡前程。書中講到在中國絲綢起源時期,因為絲綢是貴重珍稀的物品,與祭祀和生死觀念相關,是作為喪服、祭服及祭品的。其中反映了原始人對死後世界的想像與期望,觀察到蠶化為蛹,再由蠶蛹化蛾飛升的轉化過程,從中推想自然大化的歷程,以為這是從生到死,再由死轉化飛升的途徑。而蠶絲的重要作用,就理解為包裹死去蠶蛹的神奇衣裳,有一種還魂回生的神力,可以讓僵死的蠶蛹化為翩翩升空的飛蛾。因此,人死了也要穿上費盡心血織就的珍貴絲綢,作為靈魂飛升的導引,讓亡者可以登抵上界。這個絲綢起源的解釋,配合早期文獻對蠶蛹轉化的敘述,提供了古神話學的研究思路,解釋了遠古時期為什麼人們不憚其煩,創造出如此繁複精密的絲綢工藝程序。
趙豐的絲綢史研究,借助大量考古發現的絲綢,對過去考古工作中難以處理的絲織品進行詳細探究,補充了絲綢之路研究的「絲綢」部分。由於涉及紡織工藝,他也探討出土的毛織品、麻織品以及刺繡工藝,全面描繪人類生活最基本的「衣」的歷史進程。他從草原文明的庫爾幹文化遺址的發現,講到漢晉時期墓葬出土的絲綢,再講到西方紋飾對中國絲綢設計的影響,還講到西域中亞地區的絲綢製品,更詳細討論了唐代絲綢的輝煌成就。對於唐代以後絲綢文化如何影響日本,如何在塞北的遼金王朝也得以發展,如何因女真與蒙古的崛起而影響高麗,因蒙古帝國的拓展而與波斯在絲織技術上有所交流,一直到明清時期西洋錦的傳入,趙豐都在書中做了詳細的敘述。
這是一部優秀的人類文明史,我樂於為之作序。
鄭培凱
自序
錦繡前程,一直是人們對美好前途的一種嚮往。而我實是三生有幸,一路走來,錦繡相伴。
我的家鄉是浙江海寧的長安鎮,長安雖小,卻是京杭大運河和滬杭鐵路線上出杭之後的第一處交通要道。杭州的上塘河通到這裡後,水面開始改變它的高低,於是有了長安堰和長安壩。據說這長安堰和長安壩的原理,竟然和都江堰及葛洲壩相似,由此還建起了上、中、下三閘。下閘旁邊,就是浙江曾經最大的繅絲廠——當年被稱為「浙江制絲一廠」。絲廠是這個小鎮的重心,鎮上幾乎所有的人都和這個絲廠有關。我媽媽是這個廠裡的繅絲女工,由於技術比較好,後來成為講授繅絲技術的老師。爸爸則是廠裡的機械工人,經常為廠裡的機器折騰些小革新、小發明。我在廠裡的衛生總站出生,三歲開始在廠裡的托兒所過夜,六歲開始在絲廠的子弟學校上學,放學回來就在媽媽身後的凳子上做作業,有時也會幫媽媽在繅絲車上索緒添緒。我們的學校是由一幢天主教的小教堂改建而成,十九世紀二〇年代由在絲廠女工中傳教的中國神父們集資建造。從這裡經過日占時期建成的巨大繭庫,穿過滬杭線的鐵路洋旗,就到了長安鎮上唯一一條窄窄的長街,整個小鎮就沿著運河邊的這條長街排布展開。我家從街的東橫頭又搬到西橫頭,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我都不曾離開這個繅絲業興盛的小鎮,直到1977年高中畢業,我來到離絲廠北面不遠的七里亭下鄉插隊。這也是海寧的一個桑麻之鄉。半年之後,我通過了「文革」後的第一屆高考,進入了位於省會杭州的浙江絲綢工學院。本科畢業後又師從蠶桑絲綢界的老前輩朱新予和蔣猷龍學習絲綢歷史,直到今天,我仍以絲綢之路沿途出土的絲綢作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近年來,我一直在鼓吹被稱為「絲路之綢」(Silk Road Textiles)的研究合作專案。所以,我所走過來的路,確是一條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錦繡之程,這足以令我迷戀一生。由於絲織品這種有機物對保存環境有特殊要求,古代絲綢總是在中國的大西北地區出土,因此我這輩子的研究都與西出陽關的沿途結緣。記得第一次去西北是在1985年的夏天,那是一次背包旅行。第一次接受寫作《中國絲綢史》魏唐部分的重任,我隻身一人登車西行。近兩個月的行程,到西安,出開遠門,經蘭州,又去西寧,再沿河西走廊赴嘉峪關,直到敦煌。參觀莫高窟之後便是新疆,三山夾兩盆的新疆實在過於遼闊,我無法一次完成所有的考察,只能在烏魯木齊和吐魯番逗留之後就踏上歸途。歸途上又一次前去西寧尋找研究青海都蘭絲織品的機會,雖然我的停留因遇竊賊而被迫中止,但我和考古所的隔年之約已經啟動。後一次重要的新疆之行是1989年為籌建中的絲綢博物館徵集文物,足跡到達和田和喀什。再後一次更為重要的新疆之行,是2006年作為副隊長與東華大學、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一起進行的環塔克拉瑪干絲綢之路服飾文化考察。持劍出天山,劍繞大漠還。風雪過焉耆,明月宿樓蘭。於闐觀錦繡,龜茲訪伽藍。一月三千里,聖誕猶未返。從頭算來,1985年以來,我赴新疆平均不下每年一次,直到2011年,我們在新疆博物館建成紡織品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的新疆工作站,我又算是在絲綢之路沿途有了自己真正的據點。
這二十多年幾乎就是我的整個學術生涯。期間我還去過塞北內蒙古的草原絲綢之路十多次,去過跨越歐亞大陸的一些絲綢之路的重點國家和地區,如俄羅斯、日本、韓國、烏茲別克斯坦、印度等,去過收藏或展示大量絲路之綢的博物館和研究機構。從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絲如金時》和《走向盛唐》展覽,到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的中亞絲綢之路的世紀學術年會,從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吉美博物館、聖彼德堡愛米塔什博物館等地觀摩敦煌織物直到主編《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最令人難忘的還是2006年和2008年,在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的兩次旅行,以及在亞美尼亞葉裡溫的意外逗留。在昭武九姓的故地,在布哈拉和撒瑪爾罕之間,我懷揣James Elroy Flecker 的小詩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一路走來,風餐露宿。
欲從未知求真知,故縱金旅下康城。
For lust of knowing what should not be known
We make 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
我於是一直在絲綢之路上行走,在錦繡之程中徘徊,直到今天形成了這本集子。書名既是對我的學術旅程的概括,也是對我的學術領域的描述:錦程,一路絲綢,遍地錦繡。
在整理書稿的過程中,我的博士生蔡欣根據我的幻燈片和錄音資料,為我初步錄入了十二講的文字稿,為我編輯此書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後來在文物照片和圖片的資料整理中,還得到了所有收藏單位的大力支持,特別是來自絲綢之路沿途的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內蒙古等地的文博單位,以及國外收藏絲綢之路沿途絲綢文物的大英博物館、吉美博物館、愛米塔什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阿貝格基金會等,一些私人藏家也慷慨地同意我使用他們的藏品。本人所就職的中國絲綢博物館更是提供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我的同事們以及學生們包括薛雁、徐錚等也提供了各種幫助,在此一併感謝!
趙豐
2012年3月29日於杭州凍綠齋
認識趙豐有十多年了,還記得初見時,他三十歲出頭,俊朗颯爽,說話的口氣有點急切,有一種青年學者對學術追求的激動。他說起他的專業中國絲綢史,特別是絲綢之路上出土的古代絲綢,臉上隱隱泛出紅暈,就像沉迷於球賽的球迷,說到自己擁戴的球隊,在上一季的錦標賽中,是如何從後場一個長傳,展開了扣人心弦的攻勢,經過連番閃避,最後是以幾乎不可能的角度射進了球門。他給我的深刻印象,是對學術的熱情與執著,談起絲綢就像說到自己的情人,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光輝。於是,我陸陸續續請他來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前後做了十多場講座,給香港的大學生講解中國絲綢的歷史,敘述中國絲綢是如何作為物質文明的載體,傳佈到世界各地,促進人類文明的進展,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
趙豐從小就接觸到絲綢製造業,父母都是絲綢廠的工人,上大學他主修絲綢工業技術,又轉而研究中國絲綢史,是兼具絲綢工藝專業知識及物質文明史知識的專家。在研究文化史的圈子裡,這種兼通科技工藝與歷史文化的學者,是極為少有的。我還記得,曾參觀他策劃設計的絲綢博物館,他給我講解繅絲、紡絲、織綢的過程,講如何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復原古代織機的構想。他還為我一一解釋綢、緞、錦、綾的細微差別,其關鍵在於絲織工藝的複雜多端的變化。有許多過去從文獻上無法得到確切解釋的絲綢知識,一直令我感到困惑,經他對工藝實物的分析指點,終於撥雲見日,得到明確的理解。我曾請過許多絲綢之路的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如王炳華、樊錦詩、林梅村、榮新江、齊東方等,安排各種關於絲綢之路考古發現及東西文化交流的講座,呈現了這條大漠上駝鈴叮噹的古道,如何經歷著雨雪風沙,聯繫起古代相對隔絕的東方與西方。我請趙豐講絲綢史,更從絲織品的實物以及每件絲綢反映出的工藝來講,讓古代織工的心血與智慧,通過具體的歷史細節,重新浮現在我們眼前,使我們更清楚地理解每一片在沙漠中發現的絲綢,其中承載了多少文明的累積。
趙豐把他在中國文化中心的講稿整理成書,題作《錦程》。該書不僅展示了絲綢之路的錦繡路途,也顯示了學術研究的錦繡前程。書中講到在中國絲綢起源時期,因為絲綢是貴重珍稀的物品,與祭祀和生死觀念相關,是作為喪服、祭服及祭品的。其中反映了原始人對死後世界的想像與期望,觀察到蠶化為蛹,再由蠶蛹化蛾飛升的轉化過程,從中推想自然大化的歷程,以為這是從生到死,再由死轉化飛升的途徑。而蠶絲的重要作用,就理解為包裹死去蠶蛹的神奇衣裳,有一種還魂回生的神力,可以讓僵死的蠶蛹化為翩翩升空的飛蛾。因此,人死了也要穿上費盡心血織就的珍貴絲綢,作為靈魂飛升的導引,讓亡者可以登抵上界。這個絲綢起源的解釋,配合早期文獻對蠶蛹轉化的敘述,提供了古神話學的研究思路,解釋了遠古時期為什麼人們不憚其煩,創造出如此繁複精密的絲綢工藝程序。
趙豐的絲綢史研究,借助大量考古發現的絲綢,對過去考古工作中難以處理的絲織品進行詳細探究,補充了絲綢之路研究的「絲綢」部分。由於涉及紡織工藝,他也探討出土的毛織品、麻織品以及刺繡工藝,全面描繪人類生活最基本的「衣」的歷史進程。他從草原文明的庫爾幹文化遺址的發現,講到漢晉時期墓葬出土的絲綢,再講到西方紋飾對中國絲綢設計的影響,還講到西域中亞地區的絲綢製品,更詳細討論了唐代絲綢的輝煌成就。對於唐代以後絲綢文化如何影響日本,如何在塞北的遼金王朝也得以發展,如何因女真與蒙古的崛起而影響高麗,因蒙古帝國的拓展而與波斯在絲織技術上有所交流,一直到明清時期西洋錦的傳入,趙豐都在書中做了詳細的敘述。
這是一部優秀的人類文明史,我樂於為之作序。
鄭培凱
自序
錦繡前程,一直是人們對美好前途的一種嚮往。而我實是三生有幸,一路走來,錦繡相伴。
我的家鄉是浙江海寧的長安鎮,長安雖小,卻是京杭大運河和滬杭鐵路線上出杭之後的第一處交通要道。杭州的上塘河通到這裡後,水面開始改變它的高低,於是有了長安堰和長安壩。據說這長安堰和長安壩的原理,竟然和都江堰及葛洲壩相似,由此還建起了上、中、下三閘。下閘旁邊,就是浙江曾經最大的繅絲廠——當年被稱為「浙江制絲一廠」。絲廠是這個小鎮的重心,鎮上幾乎所有的人都和這個絲廠有關。我媽媽是這個廠裡的繅絲女工,由於技術比較好,後來成為講授繅絲技術的老師。爸爸則是廠裡的機械工人,經常為廠裡的機器折騰些小革新、小發明。我在廠裡的衛生總站出生,三歲開始在廠裡的托兒所過夜,六歲開始在絲廠的子弟學校上學,放學回來就在媽媽身後的凳子上做作業,有時也會幫媽媽在繅絲車上索緒添緒。我們的學校是由一幢天主教的小教堂改建而成,十九世紀二〇年代由在絲廠女工中傳教的中國神父們集資建造。從這裡經過日占時期建成的巨大繭庫,穿過滬杭線的鐵路洋旗,就到了長安鎮上唯一一條窄窄的長街,整個小鎮就沿著運河邊的這條長街排布展開。我家從街的東橫頭又搬到西橫頭,整個童年和少年時期,我都不曾離開這個繅絲業興盛的小鎮,直到1977年高中畢業,我來到離絲廠北面不遠的七里亭下鄉插隊。這也是海寧的一個桑麻之鄉。半年之後,我通過了「文革」後的第一屆高考,進入了位於省會杭州的浙江絲綢工學院。本科畢業後又師從蠶桑絲綢界的老前輩朱新予和蔣猷龍學習絲綢歷史,直到今天,我仍以絲綢之路沿途出土的絲綢作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近年來,我一直在鼓吹被稱為「絲路之綢」(Silk Road Textiles)的研究合作專案。所以,我所走過來的路,確是一條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錦繡之程,這足以令我迷戀一生。由於絲織品這種有機物對保存環境有特殊要求,古代絲綢總是在中國的大西北地區出土,因此我這輩子的研究都與西出陽關的沿途結緣。記得第一次去西北是在1985年的夏天,那是一次背包旅行。第一次接受寫作《中國絲綢史》魏唐部分的重任,我隻身一人登車西行。近兩個月的行程,到西安,出開遠門,經蘭州,又去西寧,再沿河西走廊赴嘉峪關,直到敦煌。參觀莫高窟之後便是新疆,三山夾兩盆的新疆實在過於遼闊,我無法一次完成所有的考察,只能在烏魯木齊和吐魯番逗留之後就踏上歸途。歸途上又一次前去西寧尋找研究青海都蘭絲織品的機會,雖然我的停留因遇竊賊而被迫中止,但我和考古所的隔年之約已經啟動。後一次重要的新疆之行是1989年為籌建中的絲綢博物館徵集文物,足跡到達和田和喀什。再後一次更為重要的新疆之行,是2006年作為副隊長與東華大學、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一起進行的環塔克拉瑪干絲綢之路服飾文化考察。持劍出天山,劍繞大漠還。風雪過焉耆,明月宿樓蘭。於闐觀錦繡,龜茲訪伽藍。一月三千里,聖誕猶未返。從頭算來,1985年以來,我赴新疆平均不下每年一次,直到2011年,我們在新疆博物館建成紡織品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的新疆工作站,我又算是在絲綢之路沿途有了自己真正的據點。
這二十多年幾乎就是我的整個學術生涯。期間我還去過塞北內蒙古的草原絲綢之路十多次,去過跨越歐亞大陸的一些絲綢之路的重點國家和地區,如俄羅斯、日本、韓國、烏茲別克斯坦、印度等,去過收藏或展示大量絲路之綢的博物館和研究機構。從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絲如金時》和《走向盛唐》展覽,到瑞士阿貝格基金會的中亞絲綢之路的世紀學術年會,從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吉美博物館、聖彼德堡愛米塔什博物館等地觀摩敦煌織物直到主編《敦煌絲綢藝術全集》。最令人難忘的還是2006年和2008年,在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干納的兩次旅行,以及在亞美尼亞葉裡溫的意外逗留。在昭武九姓的故地,在布哈拉和撒瑪爾罕之間,我懷揣James Elroy Flecker 的小詩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一路走來,風餐露宿。
欲從未知求真知,故縱金旅下康城。
For lust of knowing what should not be known
We make the Golden Journey to Samarkand.
我於是一直在絲綢之路上行走,在錦繡之程中徘徊,直到今天形成了這本集子。書名既是對我的學術旅程的概括,也是對我的學術領域的描述:錦程,一路絲綢,遍地錦繡。
在整理書稿的過程中,我的博士生蔡欣根據我的幻燈片和錄音資料,為我初步錄入了十二講的文字稿,為我編輯此書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後來在文物照片和圖片的資料整理中,還得到了所有收藏單位的大力支持,特別是來自絲綢之路沿途的新疆、甘肅、青海、陝西、內蒙古等地的文博單位,以及國外收藏絲綢之路沿途絲綢文物的大英博物館、吉美博物館、愛米塔什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阿貝格基金會等,一些私人藏家也慷慨地同意我使用他們的藏品。本人所就職的中國絲綢博物館更是提供了大量的相關資料。我的同事們以及學生們包括薛雁、徐錚等也提供了各種幫助,在此一併感謝!
趙豐
2012年3月29日於杭州凍綠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