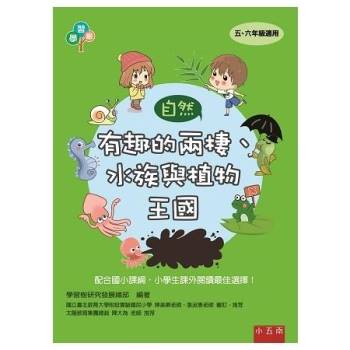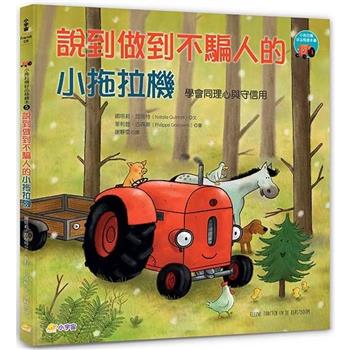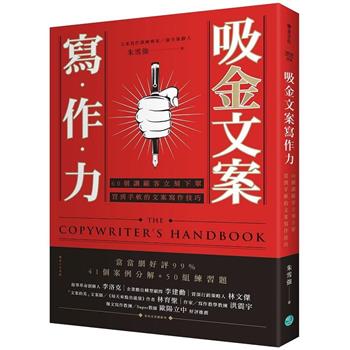1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一日的晚上,紐約市警理查.艾軒鮑爾警督為了拿自己忘在警局的傘,折回他那玻璃帷幕的個人辦公室,抓起自己桌子抽屜裡的折疊傘後又回到走廊上。外頭正飄著濛濛細雨,不得不再跑回來一趟。
經過刑事部的辦公室前,剛好看見羅恩.摩根警監正一臉嚴肅地講著電話。只見他拿起原子筆,打算在手邊的便條紙上寫筆記時,卻又放棄這個念頭,將筆放了下來。
從他凝重的表情可以想見電話那頭肯定發生了什麼重大案件。不料下一瞬間,警監鬍子底下的嘴唇浮現笑意,這讓艾軒鮑爾警督不禁停下原本要直接走過去的腳步。
他和羅恩是老交情了,深知這個人的習性。羅恩剛才的表情無疑是接獲重大刑案的報告時會出現的模樣,恐怕是兇殺案吧。就算不是兇殺案,肯定也是非同小可的案件。但他臉上卻浮現了笑意,表示電話另一邊的應該是熟人。既然如此,他勢必得親力親為,今晚大概要徹夜工作了吧。
其他人似乎都回去了,辦公室裡空蕩蕩的。羅恩掛斷電話,和一旁還沒走的部下丹尼爾.卡登說了些什麼,想必是在轉述剛才電話的內容。只見丹尼爾聽得臉色大變,果然是非比尋常的案件。與羅恩討論了幾句後,丹尼爾便衝向了走廊。他要去的地方應該是鑑識調查科吧。
視線回到刑事部的辦公室,羅恩按下內線電話,大概是要請鑑識調查科幫忙。講完電話,他又按下另一組內線電話。不用想也知道電話那頭的人是誰。從羅恩這一連串的舉動看下來,肯定是打給公關負責人。都猜到這一步了,艾軒鮑爾警督隨即走進刑事部辦公室。
「警督。」
羅恩看到他之後便喊了一聲。
「您還沒走啊。」
「大案子嗎?」
艾軒鮑爾問道。
「是的。」
羅恩急切地回答,一副想要盡快破案的樣子。
「你要出動嗎?」
「對。」
「往中央公園的方向嗎?」
艾軒鮑爾又問。
「如果是沃爾菲勒中心,我們的方向一樣。可以在西街一一四號的轉角放我下車嗎?」
聽到這裡,摩根警監臉色丕變,目瞪口呆地當場愣住了。因為他一句話都沒回應,艾軒鮑爾只好又接著問下去。
「我猜錯了嗎?」
「您怎麼知道?」
眼前的警監大驚失色地反問。
「很簡單啊。你剛才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通知你發生了重大刑案。可是打電話告知的應該是你熟識的朋友。從你的態度和丹尼爾後來驚慌失措的模樣,可以看出這個案子的事態嚴重到必須要請公關部門準備召開記者會的地步,於是我想起你有個名叫史考特.漢米爾頓的朋友是劇場導演。而他目前正在沃爾菲勒中心五十樓的芭蕾舞劇場執導《史卡博羅慶典》的公演吧。」
羅恩放棄掙扎似地點了點頭。
「不愧是被大家譽為福爾摩斯的警督啊。《史卡博羅慶典》的主角法蘭契絲卡.克雷斯潘死了。」
「什麼!你是說克雷斯潘嗎?」
這次換成艾軒鮑爾大吃一驚。
「她可是舉世聞名的芭蕾舞者。這下子真的碰上大案了。」
「《史卡博羅慶典》一共有四幕。第二幕與第三幕之間有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克雷斯潘小姐會利用那段時間在自己位於同一層樓的專用休息室裡休息。」
「那就是案發時間嗎?」
「是的。」
「是他殺嗎?」
「看起來是的。因為頭部有很深的傷口,額頭淌著血,人就倒在休息室裡。」
「被打死的。」
「是的。」
「這可是歷史性的重大刑案,可能會引起大騷動呢。」
「就是說啊。」
「畢卡索、克雷斯潘、伯恩斯坦可是連我也認識的名人。凶手呢?」
「還沒抓到。首席舞者休息室裡面設有安裝全身鏡的更衣室、洗手間、浴室,但是並沒有人躲在裡面。發現屍體的工作人員們好像都檢查過了。」
「工作人員?」
「公演的工作人員現在全都聚集在案發現場的房間裡。包括劇場老闆、經紀人、交響樂團的指揮家、與死者共演的男舞者、導演……」
「五個人啊。」
「他們號稱是克雷斯潘的五位騎士。」
「那間休息室只有一個出入口嗎?」
「只有一扇通往走廊的門。聽說堅固的橡木門從內側鎖上了,打不開。」
悶哼一聲後,警督微微一笑。
「密室嗎?」
羅恩無言頷首。
「看來媒體要樂壞了。」
「因為主角遲遲不見人影,所以騎士們就破門而入了。」
「窗戶呢?」
「畢竟是五十樓,窗戶是固定式的。」
「打不開啊。」
「打不開。玻璃很厚,聽說就連子彈也射不穿。我們要現在出發嗎?」
「走吧。」
丹尼爾.卡登刑警負責開車,一行人前往現場。
「如果看到一半就要他們回家,劇場現在肯定亂成一團吧。」
「可以想像呢。」
「門票錢能退嗎?至少退一半。」
「這我就不清楚了。」
「傳說的芭蕾舞者,人生最後的舞台竟然是演出到一半就謝幕了嗎。」
「這應該也會成為傳說吧。」
羅恩.摩根警監說道。
理查.艾軒鮑爾警督用車上的電話打給紐約芭蕾振興財團的理事。他與理事比爾.休瓦茨是多年好友。警督心想,這次或許能打聽到一些只有自己能問到的內幕。
他在秘書接起電話後報上了名字,被告知理事現在應該在一一一號的可納爾。可納爾是他常去的會員制酒吧。因此艾軒鮑爾要丹尼爾在西街一一一號的十字路口讓自己下車。
「您不去現場嗎?」
被羅恩一問,他搖搖頭。
「我先去向芭蕾舞界的大老打聽消息。」
艾軒鮑爾回答。
下了公務車,濛濛細雨雖然淋濕了頸項,所幸雨勢不大。艾軒鮑爾關上車門,微微舉起右手向他們道別,隨即轉身走向位於老舊大樓裡的酒吧。距離很短,穿過馬路就到了。因此他沒有撐傘,只是加快了腳步。
酒吧在三十一樓,印象中天氣好的時候可以遠眺帝國大廈和克萊斯勒大廈,但今晚下雨又起霧,能見度大概沒有那麼高吧。
酒吧取名可納爾,或許是因為嚮往西海岸吧。東岸其實也沒那麼多雨,只不過他每次來這裡,通常都會碰上這種陰雨綿綿的夜晚。不知何故,下雨的夜晚總是讓他想來杯蘇格蘭威士忌。是因為英國人的血統作祟嗎。
走進英國風的木造室內空間,沙發座位只有小貓兩三隻,客人主要都坐在吧檯前。將大衣交給服務生後,他在吧檯席的中央發現比爾.休瓦茨理事穿著粗花呢外套的修長背影。
「比爾。」
艾軒鮑爾警督走向友人,出聲叫喚。
或許是在模仿錢德勒,他啜飲著雞尾酒――應該是螺絲起子。
理事抬起頭,慢慢地轉了過來,看著艾軒鮑爾。
「哎呀,我還以為是誰呢,居然是警察的大人物大駕光臨啊。但願不是有什麼壞消息要告訴我。」
你的預感沒錯。警督心裡這麼想著,然後問他:
「你一個人嗎?」
警督顧慮著朋友身旁的人問道。但他們顯然不認識。
「對啊……」
朋友意興闌珊地回答,看來已經有些醉意。
「要不要換去沙發那邊聊?」
警督單刀直入的邀請好像令理事大吃一驚。只見他看著警官朋友的臉,眼神充滿不安。警督點頭示意。
「你猜對了,比爾。不是好消息。」
警督附在他耳邊低語,小聲地接著說:
「我不想讓其他人聽見。」
理事放棄掙扎,搖搖晃晃地站起來。
「我要一杯蘇格蘭威士忌。」
警督對站在吧檯裡的酒保說道。
「再給他一杯螺絲起子。」
警督低頭看著這位嬌小朋友的肩膀,邊走邊告訴友人:
「或許你會覺得我是不速之客,但這是大家今晚的命運。」
接著兩人面對面坐在空蕩蕩的沙發席。望向窗子,果然起霧了,除了隔壁的建築物,什麼也看不見。
「這種下雨的晚上……」
休瓦茨理事坐下後就慢條斯理地說了起來。
「有些事我還真不想知道。」
什麼事?警督想問,但是又把話吞了回去。他自己也很疲勞,情緒上不是很想說話。不過理事自顧自地開口了。
「像是要開始打仗了,又或者是總統死了……」
警督聽了之後點點頭。他想附和,卻又沉默不語。
「也別提醒我什麼『你已經上了年紀,差不多該讓出理事的職位了』。我不想再喪失更多活力了。」
「不是那種事……」
警督說道,旋又喃喃自語起來。
「不過或許也差不多。」
「說吧。我已經做好覺悟了。」
理事的語氣不失男子氣概。
克雷斯潘死後,紐約的芭蕾舞界將會岌岌可危,那麼與他卸下理事一職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休瓦茨理事受到的衝擊都差不多。無論如何,他現在所屬的世界將土崩瓦解。一旦失去了克雷斯潘,芭蕾舞界的魅力將大打折扣。不,影響可能更加深遠。
「就在剛才,法蘭契絲卡.克雷斯潘過世了。」
警督開門見山地告訴他。兜圈子的說法只會讓他失去耐性。
他沒聽見嗎?起初警督心中浮現了這個疑問。因為休瓦茨那張百無聊賴的臉沒有絲毫變化。
然而,衝擊的波紋開始慢慢地在他的表情浮現,可以感受到萬念俱灰的強烈失落感。接下來,表情逐漸垮在臉上,了無生氣,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理事就像是變成了人偶。整整三分鐘,他就像一具木雕人偶那樣持續癱坐在沙發上。
這個時候,酒保送上螺絲起子、冰塊和蘇格蘭威士忌。等到他將東西放到桌上並轉身離去後,理事才軟弱無力地幽幽開口。可以的話,他絕對是不想開口的,肯定今天一整個晚上都不想說半句話。
「真正的絕望就是這麼回事吧,理查。」
感覺他好不容易才從擠出這句話,嗓音沙啞,完全就是老人的樣子。
「我這才知道,再也沒有比冷冷雨夜的曼哈頓更適合作為聽到這個噩耗的舞台了吧。我用一生守護的就是芭蕾舞的世界,而她的才能則是支撐世界的頂梁柱。所以當我知道這個支柱已經不存在了……」
警督默默地啜飲蘇格蘭威士忌。
「她才三十多歲啊,死得太早了。」
「就是說啊。」
「我還無法相信這件事是真的。她還正值鼎盛,精力充沛,接下來才是大放異彩、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的劇場創造傳說的時候。」
「確實如此呢。」
「她的舞蹈自由奔放。彷彿什麼動作都難不倒她,如果是天鵝的角色,活像下一秒就要破空而去。那個在全世界火裡來、水裡去的女性竟然就這麼死了?」
「這麼厲害嗎?」
「就是這麼厲害。真希望你能告訴我這個噩耗是騙人的,但你大概無意撤回前言吧。」
警督默認。
「很遺憾。」
「沒有人會相信這個噩耗喔,無論你問誰都一樣。只要是對芭蕾舞有一點點概念、只要是看過她跳芭蕾舞的人,沒有人會相信的。」
「嗯嗯。」
「如果不是你,我也不會相信這種鬼話。此時此刻,她應該正在沃爾菲勒中心跳《史卡博羅慶典》吧。我記得今天晚上是最後一場演出。所以呢,她到底是怎麼死的?」
「是在四幕芭蕾中的……」
「啊,對了,那齣芭蕾舞劇一共有四幕。」
理事似乎逐漸感到憤怒。
「第二幕與第三幕之間的休息時間,她在自己專用的休息室被人打了頭部。」
「頭?被打了嗎?你的意思是被毆打致死?」
「我們家的員警正趕過去。確切的情況目前還在調查,所以暫時還說不準。不過,至少看起來是這樣的。而且現場是密室。」
理事甚至忘了要喝螺絲起子。
「密室?」
「休息室從裡面鎖上了。」
「這個晚上到底怎麼了!」
理事像是在宣洩恨意般說道。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難得我們生長在芭蕾舞界發展得如日中天的時代,誰能料到居然會以這種方式畫下句點。」
他說得痛苦萬分。
「就算知道凶手是誰,也絕對不要告訴我。一想到那傢伙破壞了多麼珍貴的人事物,我就氣得渾身發抖。我永遠不會原諒那個人。」
接著,理事提出一個乍看之下毫無關係的問題。
「理查,你年輕時想過要闖出一番名堂嗎?」
「我早忘了……」
警督回答。
「我高中成績意外不錯,所以大家都對我充滿期待。」
理事點點頭,開始說道。
「我有想過喔,希望能夠功成名就。我也跳過芭蕾舞,大家都說我很有天分。因為在故鄉拿過好幾次冠軍,所以我也曾深信不疑,認為自己將來必定能成為背負起這項文化的人。」
說到這裡,他似是忍不住噗哧一笑。
「結果卻變成這副德性。每晚流連酒吧,不是猛灌波本酒,就是喝螺絲起子。我還真是沒用啊,就連今晚聽到法蘭契絲卡.克雷斯潘的死訊,也完全束手無策。」
這時,他仰頭凝視了天花板片刻。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迷迭香的甜美氣息的圖書 |
 |
迷迭香的甜美氣息 作者:島田莊司 / 譯者:緋華璃 出版社:瑞昇 出版日期:2024-11-2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656頁 / 14.8 x 21 x 3.5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60 |
日本文學 |
$ 632 |
日本推理/犯罪小說 |
$ 632 |
文學作品 |
$ 704 |
中文書 |
$ 720 |
推理/驚悚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迷迭香的甜美氣息
傳說的芭蕾舞者竟然在死後依舊登台起舞!?
神所派遣的名偵探「御手洗潔」
深入時間與歷史的夾縫、開啟塵封二十年的迷宮入口
挑戰極其美麗的奇蹟之謎
探索被不可思議的時空迷霧所籠罩的真相、破解20年「前」與「後」的謎團。
洋溢奇想、揉合歷史情懷與幻想元素的「御手洗潔系列」第31作!
一位傳奇芭蕾舞者光鮮亮麗的背後,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過往?
在廣大業界人士與支持者們沉浸在悲戚與惋惜的情緒時,還尚未有人能意識到,這起令人匪夷所思的命案,將於日後帶領眾人深入時光洪流,踏進一段跨越國境、連結歷史脈絡以及許許多多人們複雜情感的波瀾萬丈故事。
◆特別收錄◆
★島田莊司老師致繁體中文版讀者專文⸺〈《迷迭香的甜美氣息》誕生緣由〉
☆推理作家•評論人冒業專文解說⸺〈奇想與救贖⸺重嚐二十世紀本格的芬芳〉
◆名家推薦◆
冬陽/推理評論人•原生電子推理雜誌《PUZZLE》主編
寵物先生/推理作家•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首獎得主
呂尚燁/千魚出版發行人•資深編輯
冒業/推理作家•評論人
======================================================
島田認為「本格Mystery」是兼備「幻想氣氛」和「邏輯性」的混種小說:前半有難以用科學說明的華麗謎團,後半則運用邏輯推理跟科學為謎團提供解答,驅逐「幻想氣氛」從而營造出「反差的美感」。《迷迭香的甜美氣息》正是這種「雙重性格」的示範作。
——冒業(節錄自本書解說文〈奇想與救贖——重嚐二十世紀本格的芬芳〉)
======================================================
【劇情簡介】
1977 年10 月的紐約曼哈頓,名作《史卡博羅慶典》正在沃爾菲勒中心五十樓的芭蕾舞劇場上演最終公演。
演出中,被譽為「芭蕾舞界傳奇」的舞者法蘭契斯卡•克雷斯潘就此殞落了。
根據調查,她是在第二幕與第三幕的幕間於專用休息室裡被毆打致死,現場處於完全的密室狀態。
然而,當天蒞臨現場的觀眾,都親眼看到法蘭契斯卡在第三幕開始後也登上了舞台,並且一路舞到公演的最後一刻……
20年後,遠在大海另一頭的瑞典斯德哥爾摩,剛觀賞完電影《法蘭契斯卡•克雷斯潘的奇蹟》的御手洗潔也在友人海因里希的引導下,正式踏上破解當年奇案的旅程。
【推薦文】
閱讀島田莊司的作品,往往給予我「科學除魅」的淋漓暢快,這本《迷迭香的甜美氣息》也不例外。看御手洗潔施展身手之前得先體會事件的離奇不可解,再結合歷史事件、各式雜學、腦科學及醫學、甚至帶點時事批判的國際關係援引,在層層疊疊的故事中感受推理解謎的迷人滋味,不能不佩服作家一路走來的堅持,也嘆服他持續探究書寫可能性的熱情。
推理評論人•原生電子推理雜誌《PUZZLE》主編/冬陽
島田莊司的推理作品,往往將謎團套用童話/神話/傳說的情境,使其染上華麗、壯闊的史詩色彩,待讀者醉心於迷人的幻想氛圍之際,最終讓謎團收束於科學理論、邏輯的範疇。本書作為謎團的框架舞劇《迷迭香的甜美氣息》除了上述用途外,甚至還映照出悲劇女主角一生的曲折故事,虛實互相烘托,體現極致的人文關懷。
推理作家•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首獎得主/寵物先生
本書在御手洗潔的長篇當中,算是相當平易近人的一本,從書名和開頭的事件,可以很順暢銜接案件、傳說、背後隱喻的人事物。故事裡除了依然有基於邏輯的離奇謎團,佐以幾段歷史與社會反思的描寫,正是島田莊司對本格推理深奧理解之處。
千魚出版發行人•資深編輯/呂尚燁
島田莊司是極少數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本格推理作家,四十三年以來一直堅持著自己的創作理念。《迷迭香的甜美氣息》是御手洗潔久違七年的全新故事,帶領讀者造訪七〇和九〇年代的紐約,以目擊者足足有二千人的迷人奇觀「死者之舞」為故事揭開序幕,讓人重嚐新本格萌芽破土時的感動。
推理作家•評論人/冒業
作者簡介:
島田莊司
1948 年出生於廣島縣。武藏野美術大學畢業。1981 年以《占星術殺人事件》出道。於2008 年獲頒日本推理文學大獎。其筆下於《斜屋犯罪》、《異邦騎士》等作品中登場的偵探‧御手洗潔,以及於《奇想天慟》等作品中登場的刑警‧吉敷竹史所開展出的兩大系列享譽海內外,博得廣大的支持。
【封面繪師】
MOS
是喜歡畫圖和畫速寫的人。
https://iammovan.weebly.com
譯者簡介:
緋華璃
不知不覺,在全職日文翻譯這條路上踽踽獨行已十年,未能譯作等身,但求無愧於心,不負有幸相遇的每一個文字。
歡迎來【緋華璃的一期一會】坐坐:
www.facebook.com/tsukihikari0220
章節試閱
1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一日的晚上,紐約市警理查.艾軒鮑爾警督為了拿自己忘在警局的傘,折回他那玻璃帷幕的個人辦公室,抓起自己桌子抽屜裡的折疊傘後又回到走廊上。外頭正飄著濛濛細雨,不得不再跑回來一趟。
經過刑事部的辦公室前,剛好看見羅恩.摩根警監正一臉嚴肅地講著電話。只見他拿起原子筆,打算在手邊的便條紙上寫筆記時,卻又放棄這個念頭,將筆放了下來。
從他凝重的表情可以想見電話那頭肯定發生了什麼重大案件。不料下一瞬間,警監鬍子底下的嘴唇浮現笑意,這讓艾軒鮑爾警督不禁停下原本要直接走過去的腳步。
他和羅恩是...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一日的晚上,紐約市警理查.艾軒鮑爾警督為了拿自己忘在警局的傘,折回他那玻璃帷幕的個人辦公室,抓起自己桌子抽屜裡的折疊傘後又回到走廊上。外頭正飄著濛濛細雨,不得不再跑回來一趟。
經過刑事部的辦公室前,剛好看見羅恩.摩根警監正一臉嚴肅地講著電話。只見他拿起原子筆,打算在手邊的便條紙上寫筆記時,卻又放棄這個念頭,將筆放了下來。
從他凝重的表情可以想見電話那頭肯定發生了什麼重大案件。不料下一瞬間,警監鬍子底下的嘴唇浮現笑意,這讓艾軒鮑爾警督不禁停下原本要直接走過去的腳步。
他和羅恩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死者之舞
第二章 天鵝之歌
第三章 猶太人與日本人
第四章 十等分主義王國
第五章 愛麗絲時間
第六章 鐵幕的另一側
第七章 七點之門
第八章 天鵝迴廊
尾 聲 勿忘草
致繁體中文版的讀者朋友們⸺《迷迭香的甜美氣息》誕生緣由
解說 奇想與救贖⸺ 重嚐二十世紀本格的芬芳
第二章 天鵝之歌
第三章 猶太人與日本人
第四章 十等分主義王國
第五章 愛麗絲時間
第六章 鐵幕的另一側
第七章 七點之門
第八章 天鵝迴廊
尾 聲 勿忘草
致繁體中文版的讀者朋友們⸺《迷迭香的甜美氣息》誕生緣由
解說 奇想與救贖⸺ 重嚐二十世紀本格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