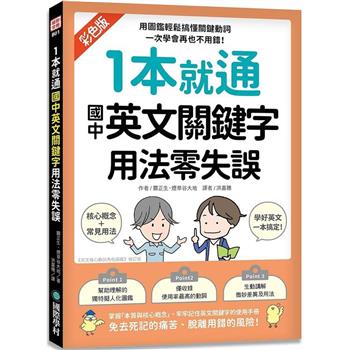1
「我正在埋葬琢磨。」
曬成小麥色的額頭浮現豆大的汗珠,昭紀靑年停下手中的鏟子說道。
「這傢伙死掉了,明明前天還活蹦亂跳的。」
「所以是昨天去世的?」
「突然就癱軟下來,才說要帶去給醫生看,在那之前就走了。」
寬敞的庭院裡長滿了杜鵑花和桃花樹,未經修剪的枝葉恣意伸展。春天呈現七彩斑斕的艷麗光景,如今已是盛夏,翠綠的葉片反射著陽光,貢獻滿眼綠意。此刻的溫度是三十五度。之前的氣象報告還預測今年夏天不會太炎熱,如今已被酷暑蒸發到一點影子都不剩,原本應該風和日麗的庭院如今只剩下悶熱的感覺。
庭院四周長滿雜亂無章的樹木,昭紀穿著T恤,正在有如RPG遊戲的存檔點般形成死角的角落挖洞。
這裡是我住的公寓隔壁,亦即房東家的庭院。從我位於二樓的房間往下可以稍微看到一隅,因為看到昭紀詭異的行動,我才撥開樹籬來問他。
「是生病了嗎?」
「不曉得,一切都發生得太突然了。天氣這麼熱,也可能是中暑了。」
昭紀埋怨道,抬頭仰望毫不留情地把地上的水分全部蒸發的艷陽。圍在脖子上的毛巾早已被汗水濡濕得跟抹布沒兩樣,我不禁擔心他可能也要中暑了。
「會不會是食物中毒?住在對面的濱爺爺上週好像就因為食物中毒住院了。」
昭紀好像也認識濱爺爺,聽我這麼說,手肘靠著插進土裡的鏟子握柄附和:
「這麼熱的天氣,聽說他居然把買回來的壽司放了兩天才吃。還自稱是壽司專家呢,居然沒發現味道已經變了,眞是太搞笑。」
不知他們有什麼過節,只見昭紀撇著嘴角,笑得很是不以為然。
「濱爺爺與其說是壽司專家,不如說是看到跟壽司有關的東西就顧不得其他了。」
「不過如果是鮪魚生魚片,就算有一點變色,我也照吃不誤,所以也沒資格說別人。」
「我也是啊。冰箱裡多的是已經過期的食物。」
回顧自己一窮二白的飮食生活,我不禁有些唏噓。蛋和納豆、火腿、牛奶,還有其他一堆有的沒的。買回來囤積的糧食絕大部分都已經過了保存期限,幸好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吃壞肚子過。
「所以你要把琢磨埋在這裡啊?」
我看了一眼琢磨躺在旁邊的可憐遺體問道。正如昭紀所說,前天牠還很有精神地坐在玄關,就連我在二樓的房間裡都能聽見叫聲。如今卻在蟬聲的護送下緊閉雙眼,化為一具冰冷的遺體。
「對,因為是多美姊交代的。」
他口中的多美姊是公寓的房東,年方三十,是一位妖艷美麗的未亡人。
昭紀則是住在隔壁的大學生,經常受多美姊之託做一些雜事。不知是人本來就好,還是對未亡人有意思,總是二話不說地一口答應,在這個家忙進忙出。
「可是要埋這麼大一隻狗,保健所1不會有意見嗎?」
「我也不知道。」昭紀歪著頭想了一下。「不過五年前死掉的智也是埋在庭院裡。聽說是因為想永遠在一起,不想葬在墓園裡。很浪漫吧。」
昭紀指著他剛才挖的洞旁邊。覆蓋著雜草的地面有如長瘤般微微隆起。沒有任何墓碑之類的東西,應該就是智的墓了。四年前才搬來的我不淸楚智是條什麼樣的狗,但是從墳墓的大小來看,應該跟琢磨一樣,都是大型犬。
「上次也是你幫忙埋的?」
「不是,當時八尾先生還在。」
八尾是多美的丈夫,兩年前去世。我幾乎沒和他打過照面,只知道是很厲害的投資客。除了這棟上百坪的房子和隔壁的公寓外,還有好幾筆土地及商業大樓等資產。
「不過,你看起來好累啊。」
「因為最近一直都是晴天,土都被曬乾了,所以硬邦邦的。大概還得花一個小時以上吧。」
昭紀故作困擾地用腳踢了踢鏟子,但臉上沒有一絲嫌麻煩的表情。反而像是從為女主人服務的行為中找到被虐的喜悅。我對他與未亡人的關係頓時充滿興趣,但事關他人隱私,最好別再追究下去。就算是推理小說作家,若因此被鎭上的人貼上愛探人隱私的標籤可就得不償失了。
「那你加油吧。」
正要轉身離去時,多美端著裝了可爾必思的玻璃杯迎面而來。
「哎呀,美袋先生。」
年方三十的美貌遺孀以充滿女人味的嬌媚嗓音叫住我。眉淸目秀的臉上浮現笑意,妖嬈的體態讓人恍然明白昭紀想為她做牛做馬也是沒辦法的事。
她把透心涼的可爾必思交給昭紀後,說:
「剛好,我有件事想拜託你。」
「什麼事?」
我語帶警戒地回答。我因為租房子而認識房東,但是與多美倒沒有過多交情。反而因為從鄰居口中聽到一些不好的傳言,除非必要不想與她扯上任何關係。
有人說她嫁給大自己二十歲以上的丈夫是為了財產。有人說丈夫之所以心臟病發作是因為多美水性楊花。有人說丈夫死了以後,她就把繼子趕出去。有人說她現在一個人住在那棟豪宅裡,每天晚上都帶不同男人回家過夜。諸如此類……族繁不及備載。要是被左鄰右舍撞見我們站一起說話,說不定連我也會變成他們口中圍著她轉的火山孝子之一。天氣已經這麼熱了,誰要當火山孝子啊。
「是琢磨的事。」
多美才不管我的困惑,瞥了已經變得冷冰冰的純白秋田犬一眼,把化著精緻妝容的臉湊過來說。
「美袋先生,聽說你認識偵探對吧,混血的……」
「對呀。」我點點頭。她指的大概是麥卡托吧。「可是,我不確定他是不是混血。」
「這樣啊。因為他的輪廓很深,我還以為他是混血兒。眞的不是嗎?」
她以不願意老實承認錯誤的態度向我解釋。肯定是聽到名字就以為麥卡托是混血兒吧。我也懶得說明,催她進入正題。
「我也不知道。所以呢,妳找偵探有什麼事?」
只見多美以迷濛的眼眸隨時都要浮現淚光的表情說:
「不瞞你說,我懷疑琢磨是不是被殺死的。」
「琢磨嗎?」
意料之外的答案令我忍不住再問一遍。
「多美姊,」昭紀從旁出言勸戒。「妳怎麼還在說這種話。」
「因為牠明明直到前天都還活蹦亂跳啊。」
多美以撒嬌的聲音說道,鬧彆扭地望向昭紀。
「一出門就開始撒野,飯也吃得很香。而且牠才五歲,根本還不到要死掉的年紀。」
昭紀也不敢表現出太強硬的態度,只好不滿地小聲咕噥:「妳想太多了啦。」
「妳為什麼會覺得琢磨是被殺死的?」
聽不出他們想表達什麼,我只好硬著頭皮打斷兩人愈來愈旁若無人的私密對話。多美以一種「你身為推理小說作家未免也太遲鈍」的口吻說道:
「推理小說不是經常有這種橋段嗎。為了不讓養的狗發出叫聲,先把狗殺掉。」
「呃,有是有……」我姑且理解她想說什麼了。「妳是說有人要殺妳嗎?」
「正是。」
多美斬釘截鐵地回答,一臉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選擇的篤定。
「誰想殺妳?」
「這還用說嗎,當然是徹啊。」
多美的表情意味著光是說出這個名字都會髒了自己的嘴。
徹是街坊口中被多美趕出家門的繼子。是八尾前妻的兒子,直到兩年前離開這個家以前,我們還算是談得來。雖然也有粗暴的一面,然而徹在我的印象中是個誠實的好靑年。跟只差三歲的繼母合不來,八尾一死就離家出走。聽說現在住在堺一帶。去年我們碰巧在車站遇到,當時他告訴我,他已經在半年前結婚了。
「那小子的目的是我老公留給我的財產喔!」
多美以威尼斯商人般的眼神尖叫。
「絕不會錯。」
「怎麼可能是徹。」
我壓根兒也不相信多美說的話。這對沒有血緣關係的母子感情不好是眞的,徹被繼母趕出家門大概也是事實,但充滿男子氣概的徹不是那種貪財的人,就連多美為了霸占八尾的遺產鬧得不可開交時,他也很乾脆地淨身出戶:「我不需要那些東西,一個人也能活下去。」這麼無欲無求的人近年來算是相當少見了,我不認為他事到如今還想要奪回財產。
「因為除了他以外,沒有人會這麼做。」
多美動氣地說,嘴角微微顫抖,枉費她那張標緻的臉。她顯然已經認定琢磨死於他殺了。
「所以呢?」
感覺就像是芙蓉蟹蓋飯配著起司蛋糕一起吃,我愈來愈提不起勁來,但還是請她繼續說下去。
「所以我想請你認識的偵探調查一下徹那傢伙,不然我會擔心得睡不著覺。」
說是這麼說,但多美連一個黑眼圈也沒有。
「我想想看喔……」
我抱著胳膊,表現出思索的模樣。因為我很淸楚麥卡托才不會接這種案子。
『居然來找我幫這種忙,你也眞糊塗啊。還是你也被未亡人的女人香迷住了。』
他大概會嗤之以鼻地一笑置之吧。我應該直接告訴多美嗎,可以的話我實在不想與她對立。
不僅因為她是房東,再加上多美在這一帶的風評不好,還喜歡把事情鬧大,萬一惹她不高興,可能連我都會傳出奇怪的流言蜚語。對街有個很適合踢足球的高中生,去年夏天不曉得為什麼被傳成偷了多美的內衣,從此徹底變成一個陰沉的傢伙。
「可是他的收費很高喔。」
我打算兜著圈子讓她知難而退。我可不想明知會被當成笑話還去找麥卡托。
「不能請他賣你一個面子嗎?」
多美一臉理所當然地向我撒嬌。
「他把錢看得很重,不可能賣我面子。」
「求求你了。說不定我今晚就會被殺掉。你就當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只是幫我問問他也好,希望他能給我一點建議。」
這才不只是幫妳問問看好嗎。心裡雖然這麼想,無奈我也敵不過她渾身上下散發的風情,最後還是點頭答應。
「好吧,我跟他商量看看。」
我偷偷地瞥了昭紀一眼,只見他眼角流露同情的表情,心照不宣地表示「我們都不容易呢」。我心領神會地朝他聳聳肩,走出庭院。再待下去,多美可能要我幫忙挖洞了。
「拜託你了。」
蟬聲唧唧,背後傳來未亡人潑辣中帶著煩惱的音色。
傍晚,我走到麥卡托掛著偌大招牌的事務所,向他說了這件事。儘管千百個不情願也無可奈何。冷氣開得很強的辦公室裡,麥卡托坐在皮革扶手椅上,指尖轉動絲質禮帽,饒富興味地問我:
「我該向你道謝,感謝你告訴我這麼一件無聊透頂的事嗎。」
「總之,我完成她的託付了。」
感覺責任已了,心情稍微爽快了點。
「你當然不會接受委託吧。」我窺探他的臉色說。
「那當然。」麥卡托點點頭。「不過,你居然來找我幫這種忙,你果然是隻糊塗蟲呢。還是你也被未亡人的女人香迷住了。」
如我所料,他果然嗤之以鼻地笑了。所以我才不想蹚這趟渾水嘛。麥卡托還繼續打落水狗:
「不過,依你的個性,光是用發嗲的聲音向你撒個嬌,你大概就沒法拒絕了。」
「我也是迫於無奈。」
我想為自己辯白,但終究還是放棄,默默地承受屈辱。對這種不知鄰里關係為何物的傢伙解釋再多,他也無法理解那種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拘束感吧。沒辦法,總之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這樣就好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麥卡托狩獵惡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中文書 |
$ 316 |
日本推理/犯罪小說 |
$ 316 |
日本懸疑/推理小說 |
$ 316 |
文學作品 |
$ 360 |
推理/驚悚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麥卡托狩獵惡人
看推理鬼才玩轉本格,看麥卡托戲弄讀者
不是神卻料事如神
到底是推理引來的殺機,還是有了殺機才有推理?
「我是銘偵探,所以經常成為眾人口中的傳說。
可能是神,也可能是無法用常理解釋的東西。」
★繼震驚推理界的《有翼之闇:麥卡托鮎最後的事件》後闊別多年,麥卡托的世界在此展開全新篇章!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理事、百萬書評部落客——喬齊安專文解說!
【劇情簡介】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縱有天大的苦衷,
殺人者人恆殺之。
天知地知麥卡托知。
揭穿惡人在黑暗中蠢動的罪行,
以慰死者在天之靈的任務
捨麥卡托其誰。
——麻耶雄嵩
總是以食指轉動著那頂浮誇的絲質禮帽,穿著一身令人過目難忘的燕尾服,性格傲慢又毒舌,他就是大阪地區大名鼎鼎的惡德偵探,麥卡托鮎。
雖然脾氣難以捉摸,卻是無數委託者爭相炫耀的話題人物。
不時收到各種邀請函的他,這次又將和作家助手美袋三条,一同前往什麼樣的地方,解決怎麼樣古怪的案件?
為了解開謎團,麥卡托甚至以自創的邏輯推翻不可思議的命案。
然而——
「很遺憾,我乃不適合長篇小說的偵探喔。」
由新本格推理鬼才麻耶雄嵩筆下最神秘的角色,為您呈上結局令人瞠目結舌的短篇連作——若要了解麥卡托鮎,必不能錯過!
★愛護精神:鄰居的狗離奇死亡,美麗的未亡人懷疑有人要謀殺她,愛把事情鬧大又謠言傳身的她,盯上了像是混血兒的銘偵探麥卡托,希望他能揪出兇手。這起案件真的如她所料,是為了殺害她所以先殺死狗嗎?
☆討厭週三和週五:美袋前往偏遠的修驗古道寺,因為手機不幸泡水報廢,走投無路下被大栗博士家的女僕收留。獲得照顧的他,看見了傳說中的「足不出戶」四重奏。不過,還未來得及沉浸在優雅的旋律之中,已經死去的大栗博士居然出現在洋房之中?接連而起的命案,找不到屍體也對不上血跡的現場,包裹在詭譎的氛圍之中,要解開謎題,只能向麥卡托求救了……
★不必要非緊急:新冠疫情襲來!偵探們紛紛躲在家中,然而謀殺案件卻暴增中,惡德銘偵探麥卡托又將怎麼度過疫情呢!?
☆名偵探的手寫筆錄:怎麼樣的犯罪才是完美犯罪?麥卡托為你戳破豪宅最適合發生兇案的真相!
★傳說之物:受到邀請前往豪宅的麥卡托,和巧遇的美袋一同前往,儘管男主人沒有現身,氣氛仍舊和樂。不過,命案依然悄悄找上門來,究竟豪宅之中隱藏著怎麼樣的秘密!?
☆麥卡托騎士:「好像有人要我的命。」知名作家委託惡德銘偵探麥卡托鮎展開調查。每天都會收到彷彿意味著「殺人倒數計時」的撲克牌,究竟有何用意?結局翻轉絕對出乎你的意料!
★天女五衰:前往劇團排練合宿地的美袋邂逅了漂亮的天女,然而天女卻成為一具屍骸,當地的天女傳說究竟和這起案件有什麼樣的關係?
☆麥卡托式搜查法:毒舌又傲慢的麥卡托竟然病倒了!為了休養,美袋帶著他一同前往朋友的別墅。在充斥著亡者照片和氣味的大房子裡,一群圍繞著亡者而活的朋友們散發著不尋常著樂觀,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又將會引發什麼事件?麥卡托期望的命案如願發生!
◆特別收錄◆
【解說】銘偵探麥卡托鮎:異端信仰的邪神化身,驚世駭俗的邏輯宇宙。
————台灣犯罪作家聯會理事•書評家/喬齊安
作者簡介:
麻耶雄嵩(Maya Yutaka)
一九六九年出生。京都大學工學部畢業。大學時代隸屬於推理小說研究社。一九九一年以《有翼之闇:麥卡托鮎最後的事件》一書正式出道。二○一一年以《獨眼少女》榮獲第六十四屆推理作家協會賞(長篇及連作短篇部門)與第十一屆本格推理大賞雙料冠軍。二○一五年以《再見神明》榮獲第十五屆本格推理大賞。
譯者簡介:
緋華璃
不知不覺,在全職日文翻譯這條路上踽踽獨行已十年,未能譯作等身,但求無愧於心,不負有幸相遇的每一個文字。曾翻譯麻耶雄嵩的《再見神明》、《夏與冬的奏鳴曲》等作品。
歡迎來【緋華璃的一期一會】坐坐:
www.facebook.com/tsukihikari022
章節試閱
1
「我正在埋葬琢磨。」
曬成小麥色的額頭浮現豆大的汗珠,昭紀靑年停下手中的鏟子說道。
「這傢伙死掉了,明明前天還活蹦亂跳的。」
「所以是昨天去世的?」
「突然就癱軟下來,才說要帶去給醫生看,在那之前就走了。」
寬敞的庭院裡長滿了杜鵑花和桃花樹,未經修剪的枝葉恣意伸展。春天呈現七彩斑斕的艷麗光景,如今已是盛夏,翠綠的葉片反射著陽光,貢獻滿眼綠意。此刻的溫度是三十五度。之前的氣象報告還預測今年夏天不會太炎熱,如今已被酷暑蒸發到一點影子都不剩,原本應該風和日麗的庭院如今只剩下悶熱的感覺。
庭院四周長滿...
「我正在埋葬琢磨。」
曬成小麥色的額頭浮現豆大的汗珠,昭紀靑年停下手中的鏟子說道。
「這傢伙死掉了,明明前天還活蹦亂跳的。」
「所以是昨天去世的?」
「突然就癱軟下來,才說要帶去給醫生看,在那之前就走了。」
寬敞的庭院裡長滿了杜鵑花和桃花樹,未經修剪的枝葉恣意伸展。春天呈現七彩斑斕的艷麗光景,如今已是盛夏,翠綠的葉片反射著陽光,貢獻滿眼綠意。此刻的溫度是三十五度。之前的氣象報告還預測今年夏天不會太炎熱,如今已被酷暑蒸發到一點影子都不剩,原本應該風和日麗的庭院如今只剩下悶熱的感覺。
庭院四周長滿...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解說】銘偵探麥卡托鮎:異端信仰的邪神化身,驚世駭俗的邏輯宇宙。 (節選)
文/喬齊安
「沒有人比名偵探更適合承擔這種思考實驗了。獨自抵達極北盡頭的麻耶,向讀者展示了一片前所未見的荒涼景象。」
──市川尚吾(推理評論家,寫小說的筆名為乾胡桃)
任憑季節更替,總是身著一襲燕尾服與高筒禮帽、頂著混血兒般的臉孔、黑白兩道通吃的硬背景,姓名不知是真是假的麥卡托鮎,是推理大師麻耶雄嵩執筆以來創造出的第一位名偵探,也是他設計的角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奇妙的是,即使麥卡托已經活躍了三十年,我們讀者對於他的了解卻...
文/喬齊安
「沒有人比名偵探更適合承擔這種思考實驗了。獨自抵達極北盡頭的麻耶,向讀者展示了一片前所未見的荒涼景象。」
──市川尚吾(推理評論家,寫小說的筆名為乾胡桃)
任憑季節更替,總是身著一襲燕尾服與高筒禮帽、頂著混血兒般的臉孔、黑白兩道通吃的硬背景,姓名不知是真是假的麥卡托鮎,是推理大師麻耶雄嵩執筆以來創造出的第一位名偵探,也是他設計的角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奇妙的是,即使麥卡托已經活躍了三十年,我們讀者對於他的了解卻...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003 愛護精神
027 討厭週三和週五
081 不必要非緊急
085 名偵探的手寫筆錄
091 傳說之物
141 麥卡托騎士
181 天女五衰
233 麥卡托式搜査法
303 解說
銘偵探麥卡托鮎:異端信仰的邪神化身, 驚世駭俗的邏輯宇宙。
027 討厭週三和週五
081 不必要非緊急
085 名偵探的手寫筆錄
091 傳說之物
141 麥卡托騎士
181 天女五衰
233 麥卡托式搜査法
303 解說
銘偵探麥卡托鮎:異端信仰的邪神化身, 驚世駭俗的邏輯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