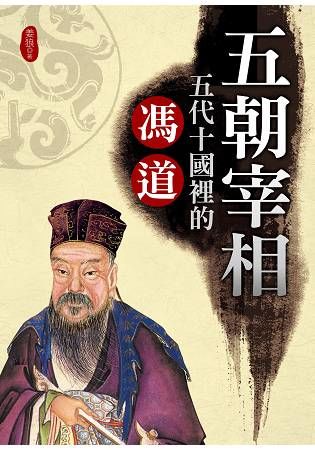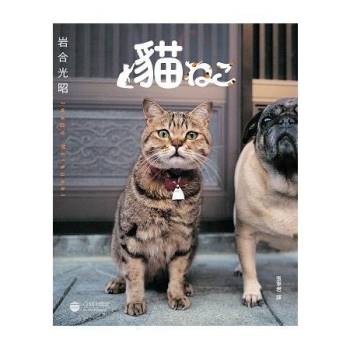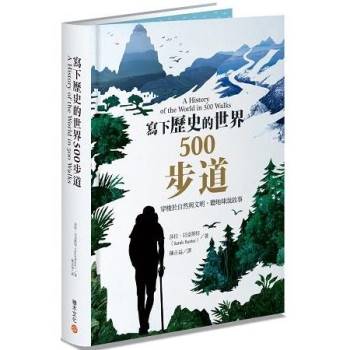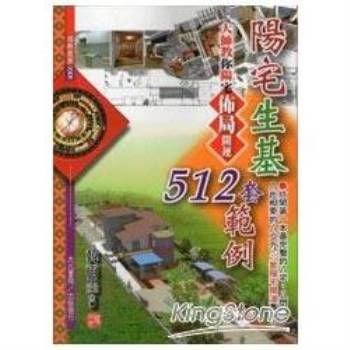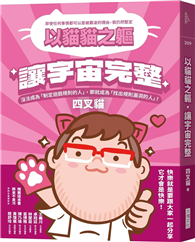前言
官場是什麼所在?從字面上解釋,就是當官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就像酒場、賭場、煙花場。
都說官場是個大染缸,把一塊白布扔到缸裡再撈出來,就成了五顏六色的花布。
也有例外的,比如明朝的海瑞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收納、不奉迎,堪稱官場聖人。海瑞為官如此,固然贏得生前身後名,可如果官場中人都要像海瑞那樣清白如水,那還做個什麼官?做官的樂趣何在?
為什麼要做官?不要講什麼治國平天下的空話,對大多數人來說,做官就是生前謀得富貴、死後蔭及子孫。如果能為民謀得幾件實事,賺得一把萬民傘,也好算作錦上添花,功德一件。
做官是一種生存手段,人活著總是要吃飯的,有人靠砍柴捕魚為生,有人就以做官謀生。做不做官,做大官與做小官,做內官還是做外官,都是一門大學問。怎麼才能做好官?為官之道如何?清道光朝的大學士曹振鏞先生留下了六字真經:「多磕頭,少說話。」
身在官場,要注意四點:
一、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時刻保持警惕,要懂得見機而進,識機而退。
二、多念別人的好,與人方便,與己方便,萬事給別人留條後路。
三、少說話,會說話,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四、要有真才實學,這是「10000」最重要的那個「1」,沒有這個「1」,一切都是空談。
歷史上名官如雲,位極人臣者更不在少數,但真正能將這四點為官之道做到爐火純青的並不多,有兩個人物特別值得一提。
一是東漢太尉胡廣。
胡廣歷經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做宰相三十年,在官場屹立不倒,成為東漢官場一大奇觀。胡廣為人中庸,不強出頭,所謂「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廣門生遍天下,他死後,皇帝悲痛,天下皆哭,備極榮哀,胡廣的學生蔡邕對座師的評價是「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耋袞老成,勳被萬方,與國始終,未有若公者焉。」
二是五代宰相馮道。
馮道的人生經歷比胡廣更為傳奇,為官之路更為艱難。胡廣生逢太平,天下興盛,無災無難到三公,而馮道所處的是天崩地裂的大亂世,皇帝輪流做,人命賤如土。
胡廣只入仕東漢一朝,馮道卻歷任後唐、後晉、遼、後漢、後周五個不同的政權而位居宰相,十代帝王師,皇帝禮敬,士林肅拜。馮道生前有重名於天下,死後同樣備極榮哀,周世宗柴榮追封馮道為瀛王。
讓人遺憾的是,像馮道這樣的文臣翹楚,士林班頭,五朝元老,在千年之後卻成了不忠不孝的反面典型被大加鞭撻。受歐陽修、司馬光、王夫之等人批判馮道的影響,現在提及馮道,一則曰貳臣,二則曰佞臣,三則曰奸臣,或譏為「騎牆孔老二」,冷嘲熱諷,以為常事。
我們從發黃的舊史書中所看到的馮道,並不是歷史上真實的馮道,而是被道德武器殺死的馮道屍體,歷經千年曝晒,已經嚴重變形發臭。
馮道最受後人詬病的地方是馮道的「不忠」,一身出仕五朝,騎牆觀風,迎來送往,喜新厭舊。《舊五代史》對馮道的評價非常具有代表性,「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在這些靠「忠孝」混飯吃的士大夫看來,為人臣者,要從一而終,馮道已失大節,雖有小善,亦不足取。
忠誠的標準是什麼?很簡單,標準是愛民與不愛民。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既然趙匡胤有負柴榮託孤,發動兵變建宋是為了天下蒼生逆取順守,為什麼對同樣愛護天下蒼生而忍辱負重的馮道窮追猛打?
一個人的人品即使再惡劣,他的身上也會有閃光點,馮道也不例外。馮道固然有明哲保身的庸猾,但馮道品性仁厚,性情中庸,與人為善。不能只看到馮道在官場上呼風喚雨,吃香喝辣,卻忽視了馮道所處的險惡歷史環境。
忠與不忠,看的不是對一家一姓的小忠,而是天下黎庶公器的大忠。馮道雖然歷仕五朝十帝,但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勸皇帝體諒民生之艱難,不與民爭利,這才是真正的忠貞。
馮道為相二十七年,從來沒有拿公家的一分錢,對外人送的貴重禮物一律拒之門外。許多士大夫都以養小妾為榮,馮道家裡卻空空如也,僕人都沒幾個。馮道身為宰相,俸祿優厚,可以享受人上人的生活,但馮道卻居茅舍、與僕人同食,睡覺則以草當床。有些人滿嘴仁義道德,私下卻妻妾成群、花天酒地,和馮道相比,何其渺小。
對馮道評價最高的是北宋官場的獨行者王安石,也只有王安石讀懂了馮道,王安石說馮道委屈自己,幫助別人,是當代的大佛菩薩。為了維護馮道的尊嚴,王安石不惜當著皇帝的面和同朝宰相唐介打嘴仗,把馮道比成商朝名相伊尹。
有些人天生就是做藝術家的,比如李白和李煜;有些人天生就是做皇帝的,比如劉邦和朱元璋;而有些人天生就是做官的,比如胡廣和馮道。為官者,多是糊塗而來,糊塗而去,一生贏得是淒涼。只有馮道把做官當成了一種藝術,上升到理論高度,還寫了兩本官經《仕經》、《榮枯鑒》,講述他做官的心得體會。
宦海沉浮,冷暖自知。要從小溪行舟奔大海,要繞過多少暗礁,多少滔天巨浪?稍不留神,便會葬身水底。沉舟側畔千帆過,還在船上的前行者依然鬥志昂揚地朝著大海的方向絕水而去,沒有人會同情失敗者。馮道很幸運,他從小溪上行舟一路東來,躲過暗礁,躲過巨浪,最終看到了大海。
與其說馮道做官成功,不如說馮道做人成功,會不會做官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會不會做人。官場名利多,是非也多,要拿得起放得下,捨即是得。老子說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馮道在這一點做得非常好,馮道喜歡做官,會做官,但他從來沒有貪戀這一切,該放手時毫不猶豫。
通過馮道看五代,跟著馮道混官場,下面開始這場奇妙的穿越旅行。
被時間殺死的馮道
周顯德元年(九五四)四月十七日,一個還算風和日麗的日子。
東京開封府,大周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中原最繁華的城市。
每天一大早,從東城的望春門到西城的闔閭門,人來人往,摩肩接踵,非常熱鬧。許多官員坐著轎子來到宮裡辦公,沿街還有許多小販在叫賣自己的商品。偶爾還會看到穿著奇異服裝的西域商人騎著駱駝穿行於街市,引來許多小孩子的圍觀。
皇帝柴榮此時並不在東京,而是親自率軍北上,與南犯的北漢軍隊大戰於高平。高平之戰,周朝軍隊幾乎全殲北漢軍,起初被所有人懷疑的柴榮在這場戰役中出盡了鋒頭,從此萬眾矚目。前方大捷的消息傳到東京,街頭巷尾都在傳頌皇帝臨陣殺敵的英雄事蹟,人人臉上都掛著笑容。
並非人人如此,在一座不甚起眼的宅院裡,就隱隱傳出來陣陣的抽泣聲。
楊柳深深的臥室裡,一個蒼老的身軀沉沉地躺在榻上,身上鋪著一床錦被。
在老者的榻邊,站著幾個臉上寫滿感傷的家人。
陽光斜灑進房間裡,卻讓人感覺不到一絲溫暖,反而能嗅到越來越重的死亡氣息。榻上老者的鬍鬚早已花白,散亂地伏在胸前,偶爾有一絲起伏。
這位老者身分貴重,地位顯赫,他就是周朝官場最德高望重的大臣--太師、中書令馮道。
這一年,馮道七十三歲。
五代最為傳奇的官場不倒翁,號稱「騎牆孔子」,與孔子同壽的馮道終於要倒了。不過他不是倒在政敵的手上,而是被時間殺死。
有心人會記得,當朝皇帝柴榮是馮道所侍奉過的第十二個君主,這是馮道從政的第五十二個年頭。也許會有好事者在私下猜測馮道還會「剋死」多少個皇帝,但讓這些人失算了,馮道即將走進發黃的歷史書中。
劉守光、李存勗、李嗣源、李從厚、李從珂、石敬瑭、石重貴、耶律德光、劉知遠、劉承祐、郭威、柴榮。
這是馮道所效力過的十二個君主的名字。
後唐明宗李嗣源天成二年(九二七),馮道被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末五代宰相)開始,就穩穩坐在宰相的位置上,再也沒有下來過。這一坐,就是二十七年。做太平宰相幾十年,自古大有人在,而馮道卻在政權更迭的刀與火之間歷經艱難,每走一步都是拿生命在和命運賭博。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有兩個敢於兜出「自己家底」的奇人。一個是白居易,他喜歡在自己的詩裡曬做官時的薪水,《白樂天詩集》更像是一本會計專用帳簿;另一個就是馮道,白居易只是曬曬工資,而馮道乾脆把自己從政以來所做過的所有官銜都裝進了寫給自己的墓誌銘《長樂老自敘》中。
有人說馮道這麼做是在炫耀,但他至少有炫耀的資本。他寫《長樂老自敘》的時候,已經六十九歲了,人生的戲劇就要謝幕。馮道在下車前,需要回憶一下自己都在車上做了些什麼,人之常情,不足責怪。
自古做人難,做官更難,做大官更是難上加難。官場險惡,機關算盡,在官場中,微笑是一把殺人的刀,幾乎人人都是笑面虎。何況馮道混得還不只是官場,更是江湖,一個歐陽修痛斥為「天地閉、賢人隱」的亂世江湖。
那是一個屬於粗暴武夫的江湖,那是一個酷烈的血腥殺場。
無藥可救的亂世
「天可汗」李世民創建的大唐帝國,早已經成為晚唐人心中苦澀的回憶,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天崩地陷的黑暗末世。
中和二年(八八二),這是年輕的僖宗皇帝李儇在位的第九個年頭。不過皇帝此時並不在帝都長安,而是在距離長安以南八百多公里的成都。
早在一年半以前,私鹽販子出身的落第秀才黃巢率領他的軍隊攻陷了東都洛陽,李儇為了避免和黃巢發生親密接觸,效仿他的八世祖唐玄宗李隆基,帶著王公大臣們逃出長安,逃到成都避難。
黃巢在長安城中吟誦著他的著名詩篇:「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
駐在成都府衙的僖宗卻在忙著寫號召天下藩鎮勤王的詔書,僖宗希望各鎮諸侯能體王業之艱難,火速派出大軍撲滅「反賊」黃巢。
僖宗不斷得到從關中傳來的好消息,諸侯軍已經雲集長安城外,已經對黃巢發起總攻。
此時的黃巢雖然實力不如以前,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諸侯軍在長安和黃巢的交手依然非常吃力。在這個時候,行營都統王鐸接受了大太監楊復光的建議,派人去代北,請李克用發兵南下,助諸侯一臂之力。
李克用帶著四萬黑鴉軍浩浩蕩蕩地殺向了長安,實力剽悍的沙陀軍果然打出了威風,在長安附近的成店打敗了黃巢大將尚讓,幾乎全殲了黃巢主力。已經做了大齊皇帝的黃巢不得不逃離長安,強奪藍田關逃出生天,諸侯軍順利地收復長安,時間是中和三年的三月。
逃到關東的黃巢依然沒有擺脫沙陀軍的追殺,被李克用追得滿街亂竄。最終在中和四年的六月,逼得走投無路的大齊皇帝在山東萊蕪的狼虎谷自殺。已經回到長安的僖宗皇帝激動地登上大玄樓,觀賞武寧軍節度使時溥送來的黃巢人頭。
轟轟烈烈的唐末農民大起義雖然以失敗告終,但等僖宗在黃巢被殺的興奮勁頭過後,才發現他面臨的是比黃巢起義更加不可收拾的局面。
割據各地的節度使在撲滅黃巢起義的過程中不斷壯大自己的實力,沒有一個把自己的地盤和兵權交給皇帝,他們表面上歸順朝廷,實際上沒有人理睬僖宗發出的每一道指令,政令不出承天門。
長安城中有一個唐朝皇帝,而在地方上,卻有無數個「皇帝」。
僖宗此時的處境還不如他的祖宗們,至少代宗之後的唐朝皇帝們還控制著大半國土,那時的藩鎮諸侯對皇帝還有三分敬畏。
而黃巢之亂後,勝利的果實被諸侯們竊走,僖宗什麼都沒有得到,甚至他的人身自由也被大太監、他的「義父」田令孜所控制。僖宗在官場的角色更像是聯合國秘書長,他無權干涉任何一個諸侯的內政。落架的鳳凰不如雞。對官場中人來說,最悲哀的事情不是人走茶涼,而是人還沒走,茶就已經涼了。
做人難,做皇帝難,做一個無權無勢的皇帝,更是難上加難。
眼前這個混亂局面,不要說唐太宗再世,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僖宗唯一能做的,就是得過且過,每天飽受被輕視的煎熬。好在僖宗命短,文德元年(八八八)三月初六,二十七歲的僖宗駕崩於淒風苦雨中的靈符殿,繼位的是僖宗的弟弟李曄,就是命運比僖宗更加悲劇的唐昭宗。
與其說昭宗是皇帝,不如說昭宗和他哥哥僖宗一樣,是個看客,站在城頭觀山景。帝國名義上的疆域內所發生的一切,都與昭宗無關。
軍閥們之間的火拼依然進行著,昭宗已經注意到了,無賴出身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就在昭宗剛改元的第二年,朱溫已經打敗了盤踞在河南的吃人大魔頭秦宗權,並把秦宗權押解到長安,由昭宗發落。
對於這樣一個自立於朝廷法統之外的反賊,昭宗自然要按國法行事,斬秦宗權於城郊大柳樹下。
朱溫逐步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區,而朱溫的仇人李克用則在河北用兵,他的對手是盤踞在洺州的昭義軍留後孟方立。孟方立不是李克用的對手,昭義軍的地盤很快就被李克用劃進自己的帳戶裡。
河北是自安史之亂後出現的藩鎮割據的重災區,軍閥橫行已有一百多年。得河北者得天下,朱溫自然不會讓李克用獨吞這塊美味的蛋糕,也把手伸了過來。
除了李克用和朱溫,河北有四股割據勢力,分別是統治魏州的魏博節度使羅弘信、統治鎮州的成德軍節度使王鎔、統治定州的義武節度使王郜、統治幽滄二州的盧龍節度使劉仁恭。
在這六個軍閥中,羅弘信、王鎔、王郜相對較弱,夾在李克用、朱溫、劉仁恭三大強藩之間苦苦掙扎。
劉仁恭實力強大到了什麼程度?截至光化元年(八九八),劉仁恭手下有步騎兵十多萬,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劉仁恭的野心非常大,他並不滿足於現有的地盤,他早就對富饒的河北諸鎮垂涎三尺,這年頭沒人嫌錢多咬手。劉仁恭第一個要吃掉的對手是魏博羅弘信,在光化二年,劉仁恭帶著十萬大軍南下進攻魏博。
魏博是宣武軍的北線戰略屏障,如果讓劉仁恭得到了魏州,會對朱溫產生極大的生存壓力。
朱溫不會讓任何人染指河北,他派出最精銳的部隊北上救援魏博,在內黃吃掉了五萬燕軍,成功打殘了劉仁恭反撲的能力。
劉仁恭為了能在朱溫的刀尖下活下來,不得不厚著臉皮去央求他曾經的敵人李克用出兵牽制朱溫。不過朱溫並不在乎李克用的搗亂,汴軍繼續北上,在同年(八九八)的十月,攻下瀛州,就是現在的河北省河間市。
瀛州自古以來就是河北重要的地級行政單位,漢朝時設為河間郡,一直到唐武德四年(六二一),唐朝消滅了河北王竇建德,才改為瀛州。
在瀛州轄下的幾個縣中,有一個景城縣,現在已經沒有景城縣這個行政區劃,大致位置在現在的河間市與滄州市的中間。景城的建縣史終止於宋神宗熙寧六年(一○七三年)。
之所以要單獨介紹已經從行政區劃史中消失的景城縣,因為這裡是馮道的家鄉。
唐中和二年(八八二),馮道生於此。
馮道的家世
關於馮道的家世,根據《舊五代史‧周書‧馮道傳》的記載,馮道出身於瀛州景城縣農村的知識份子家庭。
現有史料找不到馮道父祖幾代生平的任何記載,甚至不清楚馮道在家是獨子,還是有兄弟姐妹。
查了一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良吏傳》,發現在唐武則天執政時期,有一個專和武則天過不去的直臣,官拜尚書左丞,名叫馮元常。因為馮元常曾經密諫唐高宗李治要限制皇后武則天的權力,從而得罪了武則天,最後被酷吏周興下獄害死。
馮元常的籍貫是相州安陽,也就是現在的河南安陽,但馮元常卻是從長樂郡遷到安陽的,《新唐書‧馮元常傳》明確記載馮元常祖先的籍貫是長樂郡。長樂郡就在今天的河北省冀州市,漢朝時稱為信都郡,西晉時改為長樂國,北魏也稱為長樂郡。
馮元常的曾祖父馮子悰是北齊胡太后的妹夫,官居高位,而馮子悰的祖上是十六國之一的北燕開國君主馮跋,馮跋就是長樂人。
說到馮跋,人們不太熟悉,但北燕馮氏的子孫非常出色,馮跋有兩個著名後裔,一是力行漢化的北魏馮太后(孝文帝元宏祖母),一是唐朝第一大太監高力士(原姓馮)。而南北朝後期嶺南著名的女領袖冼夫人的丈夫,是北燕皇族馮寶。
在隋朝初年州改郡的行政區劃調整後,長樂郡不復存在,但人們還是習慣把後來的冀州稱為長樂。我們再來看看馮道給自己的墓誌銘叫什麼,就叫《長樂老自敘》,在文中馮道也明明白白地說自己就是長樂人。
雖然沒有史料證明馮道就是馮元常的後人,但馮元常是當時有名的學者型官員,熟讀經書,被稱為儒者。而馮道家族又世傳儒學,很難相信馮道和馮元常之間沒有血脈傳承關係。
馮道祖上的情況基本上摸清楚了,如果排除馮道有意抬高自己家世的可能性的話,馮道就是北燕太祖文成皇帝馮跋的後人。
馮元常在武周政權被推翻後,因為他曾經反對過武則天,所以馮元常在死後得到了平反。唐中宗李顯為了表彰馮元常,親賜名匾,上書四個大字「忠臣之門」,天下人皆傳頌馮元常的忠直不阿。
雖然長樂馮氏在唐朝不算是名門望族,但當時的一流士族都願意與馮家通婚,並以此為榮,可見在唐朝中葉以前,長樂馮氏的社會地位還是很高的。
不過馮道以前的幾代祖上都沒有在官場上留下痕跡,而是世代務農或講學。一個合理的邏輯推斷,就是馮元常的子孫曾經敗過家,或者因為其他什麼原因導致家道中落,淪為平民。
祖上吃香喝辣,子孫啃窩頭鹹菜的悲喜劇,很容易讓人們想起那位賣草鞋的大漢皇叔劉玄德。
馮道比劉備強一點的是,他家還有幾畝薄地,而劉備則是典型的城市貧民階層,無地可種,不打工就得餓肚子。
不過古代的農業完全是靠天吃飯,生產水準低下,收不了多少糧食,再加上官府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農民辛苦一年,都不一定能吃上一頓飽飯。
中晚唐以後,朝廷吏治敗壞,軍閥橫徵暴斂,惡吏橫行鄉里。不管百姓家裡有沒有收成,各級官府派來的惡吏們都要上門要錢徵糧,沒錢也要交,不然就扒屋牽牛。
從馮道家的情況來看,馮家雖然世代務農,但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放棄種地,而是在鄉里教書為業。說明馮家的祖上也承受不了多如牛毛的稅收,或者被地主強行兼併了土地,淪為「農民工」。
馮家雖然是北燕皇族後裔,但那都是幾百年前的老皇曆了。
馮道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落魄的貴族家庭,他的祖先們只留給馮道兩樣東西。
一、虛無縹緲的貴族頭銜。這個東西不能當飯吃,看看劉備的遭遇就知道了。
二、大量的書籍。這個東西可以當飯吃。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五朝宰相:五代十國裡的馮道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五朝宰相:五代十國裡的馮道
五代十國的風流人物眾多,但能稱為其中翹楚者,帝王中的柴榮,文藝中的李煜,大臣中則有馮道。馮道不算是著名的歷史人物,但其一生充滿特色與傳奇。
馮道在走馬燈式的歷代官場中浮沉周旋,進退自如,身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中間還夾著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相二十多年,始終屹立不倒,被稱為官場「不倒翁」。在武人當道、帝王更迭頻繁的五代十國,一位文人如何做到從政五十二年,效力十二位君主,馮道憑藉的「道」是什麼?
本書由五代史作家姜狼先生執筆,娓娓道來,述事以鑒古,繪人而明理,足令讀者了解真正的馮道。
作者簡介:
姜狼,男,生於七十年代,現為自由職業者。酷愛歷史文學。對亂世歷史的研究和寫作有濃厚的興趣,如三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曾出版過多部反映亂世精彩歷史的作品。希望能用自己獨特的視角,精練的筆觸,為讀者還原一個個精彩、撼人心魄的時代。
TOP
章節試閱
前言
官場是什麼所在?從字面上解釋,就是當官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就像酒場、賭場、煙花場。
都說官場是個大染缸,把一塊白布扔到缸裡再撈出來,就成了五顏六色的花布。
也有例外的,比如明朝的海瑞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收納、不奉迎,堪稱官場聖人。海瑞為官如此,固然贏得生前身後名,可如果官場中人都要像海瑞那樣清白如水,那還做個什麼官?做官的樂趣何在?
為什麼要做官?不要講什麼治國平天下的空話,對大多數人來說,做官就是生前謀得富貴、死後蔭及子孫。如果能為民謀得幾件實事,賺得一把萬民傘,也好算作錦上添花,功德...
官場是什麼所在?從字面上解釋,就是當官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就像酒場、賭場、煙花場。
都說官場是個大染缸,把一塊白布扔到缸裡再撈出來,就成了五顏六色的花布。
也有例外的,比如明朝的海瑞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收納、不奉迎,堪稱官場聖人。海瑞為官如此,固然贏得生前身後名,可如果官場中人都要像海瑞那樣清白如水,那還做個什麼官?做官的樂趣何在?
為什麼要做官?不要講什麼治國平天下的空話,對大多數人來說,做官就是生前謀得富貴、死後蔭及子孫。如果能為民謀得幾件實事,賺得一把萬民傘,也好算作錦上添花,功德...
»看全部
TOP
目錄
被時間殺死的馮道 013
無藥可救的亂世 016
馮道的家世 020
知識改變命運 023
馮道的選擇 027
死諫 032
拯救馮道 036
選擇新老闆的學問 040
張承業、周玄豹、盧質 042
李存勗重用馮道的竅門 048
宴會的主角 052
河東第一文膽--馮道 060
馮道的官場生存法則 062
拯救大兵郭崇韜 069
要有敢與老闆拍桌子的膽量 078
大唐中興,馮道賜紫 080
李存勗選宰相 083
歸鄉守喪 087
契丹人的密謀 094
天翻地覆同光朝 098
馮道為什麼選擇李嗣源 103
李嗣源其人 108
馮書記何在? 110
關於用馮道為相的一場幕後政治交易 114
馮...
無藥可救的亂世 016
馮道的家世 020
知識改變命運 023
馮道的選擇 027
死諫 032
拯救馮道 036
選擇新老闆的學問 040
張承業、周玄豹、盧質 042
李存勗重用馮道的竅門 048
宴會的主角 052
河東第一文膽--馮道 060
馮道的官場生存法則 062
拯救大兵郭崇韜 069
要有敢與老闆拍桌子的膽量 078
大唐中興,馮道賜紫 080
李存勗選宰相 083
歸鄉守喪 087
契丹人的密謀 094
天翻地覆同光朝 098
馮道為什麼選擇李嗣源 103
李嗣源其人 108
馮書記何在? 110
關於用馮道為相的一場幕後政治交易 114
馮...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姜狼
- 出版社: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11-14 ISBN/ISSN:978986402194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80頁 開數:寬 15 cm × 長 21 cm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歷史人物
|